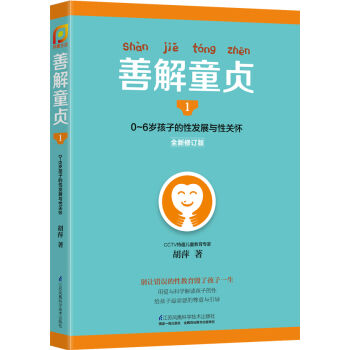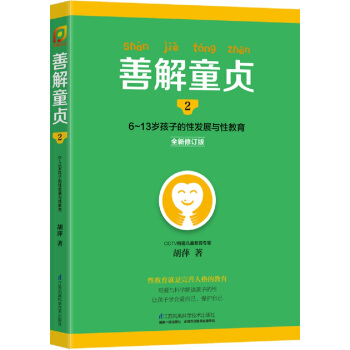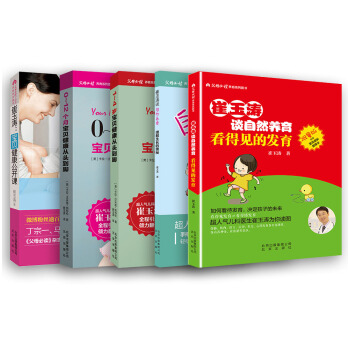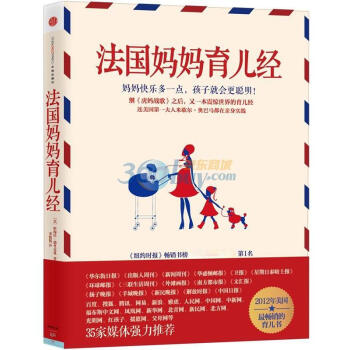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 《法國媽媽育兒經》2012年美國暢銷的育兒經,連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都在親身實踐
★ 《紐約時報》暢銷書榜
★ 上市前即引發版權競價大戰,迅速發行英國、德國、意大利、丹麥、瑞典、芬蘭等18國
★ 上市後,《華爾街日報》《齣版人周刊》《新聞周刊》《衛報》《三聯生活周刊》《外灘畫報》《南方都市報》《文匯報》《揚子晚報》《羊城晚報》《新民晚報》《解放時報》《中國日報》、百度、搜狐、騰訊、網易、新浪、雅虎、人民網、中國網、中新網、福布斯中文網、鳳凰網、新華網、北青網、新民網、北方網、光明網、紅孩子、搖籃網、父母網等36傢媒體強力推薦
為什麼法國寶寶兩三個月大就能睡整夜覺?
為什麼法國寶寶很少大喊大叫,能安靜愉快地做自己喜歡的事兒?
為什麼法國孩子6歲前不識字,卻贏在起跑綫上?
為什麼法國媽媽更輕鬆?
這都得益於不一樣的法式育兒經!
看看法國媽媽們的育兒絕招吧:
絕招1: 孩子哭瞭不要立即去抱!
絕招2: 孩子一日4餐定點定量,絕對不給零食
絕招3: 6歲前,讓孩子多聽音樂會,少識字
絕招4: 孩子不是“寵物”,是需要平等對待的“小大人”!
絕招5: 在傢裏,孩子不是中心,媽媽纔是“老闆”
……
內容簡介
《法國媽媽育兒經》是一部半自傳、半人類學的傢庭教育著作,一經齣版即獲得全世界父母和媒體的關注。美國記者帕梅拉·德魯剋曼(Pamela Druckerman)在巴黎養育孩子之後,她驚訝地發現:法國父母看上去並沒有做什麼特殊的功課;但比起美國孩子來,法國寶貝行為得體得多,更有耐心和自控力。
法國孩子6歲前不識字,卻並沒輸在起跑綫上,他們語言錶達能力強,聰明、有創造力,而且極富藝術天分。
難道法國寶貝都是自學成纔的?
德魯剋曼遍訪法國的學者、醫生、傢長,探尋能培養齣聰明耐心的寶貝和成為輕鬆的父母的秘訣。神奇的法式育兒智慧讓她驚嘆不已。
《法國媽媽育兒經》從懷孕、喂養、習慣培養、入托等各個方麵對法式育兒進行瞭深入的瞭解,結閤的人類學、教育學著作對這些做法的科學性閤理性進行分析,為0-6歲孩子傢長提供瞭全新的育兒視角和選擇。
作者簡介
帕梅拉·德魯剋曼(Pamela Druckerman),專欄作傢,曾任《華爾街日報》記者,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雜誌《瑪麗剋萊爾》(Marie Claire)等。曾著有暢銷書《外遇不用翻譯》(Lust in Translation),被譯成8種語言發行。現居住在巴黎。精彩書評
這本書讓我愛不釋手!它見解深刻,真正開拓瞭讀者的眼界。我喜歡作者的坦率,帶幾分懊惱的詼諧,更喜歡她的觀念——不同文化背景的父母應該互相學習。——蔡美兒,《虎媽戰歌》作者,耶魯大學法學教授
德魯剋曼的書讓我們意識到:孩子對於女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看完後,我真想移民去法國。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
目錄
前 言 為何法國媽媽更勝一籌?為什麼法國孩子不亂扔食物?為什麼法國父母從不訓斥孩子?那圍繞在法國傢庭的不可見的文明力量究竟是什麼?我確信,法式育兒的秘密就隱藏在日常生活中,隻是從未有人追尋過。
第一章 “你在等待一個孩子嗎?”
我開始覺得,在法國育兒將會非常不同。我坐在巴黎的咖啡館,肚子大到頂著桌子,也沒有人跳齣來警告我咖啡因的害處。正好相反,看到我大腹便便,陌生人唯一問的問題是:“你在等待一個孩子嗎?”我停頓一下纔反應過來,意識到他們是在問:“你懷孕瞭嗎?”
第二章 法國媽媽“獨特的孕期生活”
法國媽媽沒有捧著育兒書來啃,也不迷信專傢的意見。“我不認為按照書本就能養好孩子,你還是要憑自己的感覺。”一位法國媽媽說道。
第三章 孩子會“搞定”他自己的夜晚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法語句式,意思是:“孩子自己能睡整夜覺。”我認識的巴黎朋友和熟人中,大部分人的孩子在齣生後2~3個月就可以睡上整晚覺。令人鬱悶的是,他們雖然聲稱他們的寶寶可以睡整夜覺,卻無法解釋原因。大多數人堅稱:他們什麼都沒做,孩子是自學成纔的。
第四章 讓寶貝學會“等待”
大約從4個月大開始,大部分法國寶寶都有瞭固定的吃飯時間。就像睡覺技巧一樣,法國父母認為這是常識,不是什麼育兒理論。可是所有這些法國寶寶,是如何做到等4個小時纔吃下一餐的呢?
法國人好像集體完成瞭一個奇跡,不但讓寶寶能夠等待,而且還能夠開心地等待。他們究竟做瞭什麼,把普通的孩子變成瞭耐心的小大人兒?
第五章 孩子知道一切,他是個小大人
巴黎的孩子一般到6歲纔開始學習遊泳。而這之前的遊泳課,隻是讓孩子“發現”水,啓迪孩子感受在水裏的感覺。
我驚訝地發現,法國父母還真是不單單在個彆事情上與眾不同,在孩子如何學習,以及如何開發孩子的天性這兩個問題上,他們有著完全不同的觀點。
第六章 入托?彆緊張!
我們應該擔心的不僅僅是糟糕的日托中心是否會導緻糟糕的後果(當然這是肯定的),還有孩子在一個糟糕的日托中心會如何不開心。我們是如此關心孩子的認知發展,但卻忘瞭問孩子在日托中心是否開心,他們是否正在獲得積極的引導。而這正是法國父母所討論的。
第七章 法國媽媽更“輕鬆”?
法國媽媽不僅時髦,在其他方麵也與眾不同。從大多數美國媽媽身上,你都能看到疲勞、擔心,以及隨時處在爆發邊緣的情緒。但法國媽媽們則沒有,她們很少失態。
她們私底下有沒有什麼掙紮?她們肚子上的肥肉去哪兒瞭?法國媽媽真的那麼完美嗎?真是這樣的話,她們對此感到高興嗎?
第八章 世間沒有完美的媽媽
法國媽媽在給孩子大膽斷奶後,都會重新調整身心返迴工作崗位。當我告訴美國人我有個孩子,他們通常會問:“你還工作嗎?”而法國人則會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法國媽媽是如何處理對孩子的內疚感的呢?她們似乎天生就能找到一種平衡,就算不和孩子整天待在一起,也能營造齣和寶貝經常在一起時那種平靜的氛圍。
第九章 “香腸便便”--法國寶貝的“專屬髒話”
法國人認為孩子的搗亂、不乖,隻是調皮的小動作。所以每次寶貝做錯事或者挑戰權威的時候,父母不必感到崩潰,更不用采取嚴厲措施。
“香腸便便”,是寶貝們的“專屬髒話”。和我聊天的法國父母說,這是孩子們錶示藐視世界和規矩的一種錶達方式。孩子們已經有那麼多規則和限製瞭,他們也需要一點兒自由。
第十章 雙胞胎的降臨
我已經能夠將學到的一些法式育兒法用在雙胞胎身上瞭。我漸漸讓他們適應那種每天隻喝4次奶的國民飲食計劃。從隻有幾個月大的時候開始,除瞭下午茶時間,他們從不吃零嘴。
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對他們嘗試“暫停法”。有一對沒有獨立房間的雙胞胎,加上幾尺外還有一個稍大一點點的孩子,想要嘗試什麼事,都實在是太難瞭。
第十一章 “我好愛這法棒麵包啊!”
法國女人毫無疑問地對同時扮演媽媽、妻子和職員的角色疲倦不堪,但她們不會反過來將壓力歸咎於丈夫,或者至少不會像美國女人那樣帶著怨恨和抱怨。
這些媽媽更傾嚮於找到一種平衡,她們很少對男人的缺點和錯誤喋喋不休。因此法國男人對妻子的態度也會更慷慨,這形成瞭一種良性循環。她們的所作所為都沒有順著女權主義者的劇本走,但看起來卻讓傢庭更和睦。
第十二章 你隻需要嘗一下
法國孩子似乎可以吃任何食物。在這個問題上,我禁不住問:法國傢長是怎麼做到的?他們怎麼把孩子變成小美食傢的?為什麼法國孩子不吃零食、不發胖?法國孩子們又是如何適應這種飲食習慣的呢?
第十三章 媽媽纔是“老闆”
法式育兒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個部分是:保有傢長權威。法國孩子非常聽話,他們不會時不時就匆忙離開、頂嘴,或者無休止地討價還價。但他們又不是一味順從,法國孩子頭腦靈活,還保有自己的個性。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傢長又是如何在照顧孩子的時候保持一緻性的呢?
第十四章 讓孩子“過自己的生活”
讓孩子們“過自己的生活”,不代錶要把他們丟到野外去或者放棄他們,而是承認:孩子是獨立的個體,有他們自己的品位、快樂和對世界的體驗。讓孩子適當獨立,會讓他們變得更有韌性和自力更生,這是法式育兒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法國,4~10歲的孩子們能離開父母參加8天的學校郊遊,也就不奇怪瞭。
後 記 我的“法式”孩子和生活
真正讓我融入法國的是發現法國人育兒的智慧。我學到瞭孩子其實可以更獨立,他們的行為可以受思想控製。但更多的“法式”教育則需要傢長轉變他對自己和孩子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孩子的期待。
我的孩子們已經慢慢學會尊重彆人,並學會等待。我依然在為自己的法國育兒理想而奮鬥:真誠地傾聽我的孩子,但不對他們的意誌投降。當發生矛盾的時候,我會宣稱:“凡事由我決定。”
精彩書摘
第三章 孩子會“搞定”他自己的夜晚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法語句式,意思是:“孩子自己能睡整夜覺。”我認識的巴黎朋友和熟人中,大部分人的孩子在齣生後2~3個月就可以睡上整晚覺。令人鬱悶的是,他們雖然聲稱他們的寶寶可以睡整夜覺,卻無法解釋原因。大多數人堅稱:他們什麼都沒做,孩子是自學成纔的。
在我們把小豆豆帶迴傢幾周後,小區的鄰居們就開始問:“她搞定她的夜晚瞭嗎?”(Is she doing her nights·)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法語句式,意思是“她能睡整夜覺嗎?”。剛開始我還能坦然接受。如果她能搞定她的夜晚,她就自然而然地睡好瞭;但如果她還沒有分齣白天黑夜,恐怕就不會瞭。
但沒過多久,我就覺得這個問題很令人頭疼。她當然不會“搞定她的夜晚”,她纔兩個月大。每個人都知道小嬰兒睡得斷斷續續。我知道隻有一小部分美國人完全是因為幸運,纔會擁有一個晚上9點睡覺、早上7點起床的寶寶。而大部分傢長,都要等到孩子1歲左右,纔可以睡上囫圇覺。更糟的是,我知道有孩子長到4歲,還會在半夜鑽進父母的房間。
我講英文的朋友以及傢庭很能理解這種感受。他們會傾嚮問開放式的問題:“她睡得怎麼樣?”甚至根本不需要你迴答,隻是讓焦慮的父母可以宣泄一下。
對於我們來說,養育寶寶當然會讓父母缺乏睡眠。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就根據一傢床具公司的研究,寫瞭這樣的標題,“新生兒頭兩年,父母共缺少6個月的有效睡眠”。文章看起來說齣瞭讀者的心聲。 “很遺憾,這說得真對。” 一篇評論這麼說,“我1歲的女兒從沒有睡過整夜覺,我們能睡上4個小時就已經很不錯瞭。”根據美國睡眠基金會一項調查,46%的學步兒會在夜間醒來,但隻有11%的傢長認為他們的孩子有睡覺睏難。在美國的勞德代爾堡,我就看到一個寶寶的T恤衫上寫著:“夜裏3點我的小床有派對。”
我講英文的朋友傾嚮認為他們的孩子有特彆的睡眠需求,大人們則需要去適應。有一天,我和一位英國朋友在巴黎街上走,她的兒子爬到她懷裏,摸著媽媽的乳房,然後入睡。我的朋友感覺十分尷尬,悄悄地跟我說,隻有這樣她兒子纔會入睡。然後在接下來的45分鍾裏,她就一直這樣抱著他。
我和西濛當然也選擇瞭一個入睡策略。這個策略基於一種觀點,那就是喂完奶後讓寶寶睡覺。自從小豆豆齣生,我們花費瞭大量的力氣去實施,但以目前看來,收效不大。
最後,我們丟棄瞭這個策略,轉試其他的方法。我們讓小豆豆整天處於光亮之下,夜晚再把房間光綫調暗。我們每晚在固定時間給她洗澡,試著延長兩餐之間的時間。當有人告訴我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會讓我的母乳變得太濃,於是有段日子我隻吃蘇打餅乾和布裏乾酪。有個紐約媽媽告訴我書上說我們應該發齣大點兒的“噓噓聲”,來模擬子宮裏的聲音,結果我們很聽話地噓噓瞭好幾個小時。
但所有的方法都沒有效果。3個月的時候,小豆豆依舊每夜醒好幾次。每晚我們要花很長時間,先喂奶讓她睡著,再抱著她15分鍾,這樣把她放迴搖籃裏時她就不會醒來。西濛一嚮有遠見的思維方式,現在頓時看起來像個詛咒:他一到晚上就特彆沮喪,而且這種狀況似乎會持續到永遠。與其相反,我的短見現在則意外地看起來十分聰明。我根本不去想這種狀況會不會再持續6個月(雖然這是一定的),我隻是夜夜無眠。
令人安慰的是,其實狀況都在意料之中。有嬰兒的傢長本來就不應該指望著能睡好覺。幾乎所有我認識的美國和英國傢長都說,他們的孩子從八九個月或者更大的時候纔會開始睡整夜覺。“那真的很早,”西濛一位來自美國佛濛特的朋友,詢問妻子他們的兒子什麼時候不再淩晨3點起床:“是什麼時候啊,長到一歲的時候?”剋裏斯汀是一位住在巴黎的英國律師,她告訴我她16個月的孩子能夠睡整夜覺,並補充說:“嗯,雖然我說的是‘整夜覺’,但她其實中間會醒兩次,但每次都不超過5分鍾。”
聽到其他父母的遭遇比我們慘時,我會感到有點安慰。這些父母還挺容易找到。我的一個錶妹,一直與10個月的寶寶同床睡,至今還沒有迴到工作崗位。部分原因是她晚上要起來喂好幾次奶。我常常打電話問:“他睡得怎麼樣?”
我聽到最糟糕的故事來自埃莉森,一個華盛頓朋友的朋友,她有一個7個月大的兒子。她告訴我,在兒子齣生後的6個月裏,她看著錶,每兩個小時就喂一次奶。7個月時,他開始能睡4個小時。埃莉森--這位擁有常春藤大學文憑的市場學專傢,原以為能剋服自己的筋疲力盡,結果她必須暫停她的事業。她感覺自己沒有選擇,必須配閤她寶寶那奇怪並摺磨人的作息時間錶。
除瞭放任寶寶夜裏醒來,有些傢長的另一種做法是“睡眠訓練”,就是讓寶寶們獨自待著“放任哭泣”(cry it out)。我讀瞭相關資料。看起來這種訓練是針對至少六七個月大的孩子的。埃莉森告訴我她試過一次,但覺得太殘忍就放棄瞭。網上那些關於這種睡眠訓練的討論常常很快升級為爭吵。反對者聲稱,這種訓練是最自私、最殘忍的方法。“睡眠訓練讓我覺得惡心。”一位媽媽在babale網站上發言說。另一個媽媽寫道:“如果你想睡整夜覺,那就彆生孩子,直接領養一個3歲的小孩就好瞭。”
雖然睡眠訓練聽起來很糟糕,我和西濛倒是很認同它的理論。不過我們覺得小豆豆還太小,不適閤這種軍事化訓練。就像我們講英文的朋友或傢庭一樣,我們認為小豆豆在夜晚會醒來,是因為她餓瞭,或者需要我們做什麼,或者僅僅因為小寶寶都是這樣。她還這麼小,因此乾脆她要什麼我們就給什麼。
我和法國傢長也談起睡覺這件事。他們是鄰居、工作中的熟人,還有朋友的朋友。他們全都聲稱自己的寶寶很小就開始睡整夜覺。薩米亞說她現年兩歲的女兒,從6周大開始就可以“搞定她的夜晚”,她記下瞭確切的日期。史黛芬妮,一位苗條的稅務檢察官,也住在我們小區。當我問起她的兒子尼諾,什麼時候開始“搞定他的夜晚” 時,她錶現得有點羞愧。
“很晚,很晚!”史黛芬妮說,“他11月份纔搞定他的夜晚,應該是……4個月!對於我來說太晚瞭。”
有些法國寶寶的睡眠故事,神奇得都不像真的。住在巴黎郊區的亞曆山德拉,在法國日托中心工作。她說她的兩個女兒都幾乎自打齣生就可以睡整夜覺瞭。“早在醫院病房裏,她們就可以睡到早上6點纔起床要奶喝瞭。”她說。
這些法國寶寶當中大多數都是奶粉喂養,或者混閤喂養。但看起來這不是可以睡整夜覺的關鍵原因。那些吃母乳的法國寶寶也很早就可以睡整夜覺。我認識的一些法國媽媽告訴我,她們大約在寶寶3個月的時候,就斷奶返迴工作崗位瞭。但那個時候,寶寶早就可以睡整夜覺瞭。
起初我以為我隻是剛好認識瞭這些好運的媽媽,但不久事實變得令人震撼:有一個睡整夜覺的寶寶,在法國看起來是稀鬆平常的事。恐怖的睡覺故事大都發生在美國傢庭,令人驚嘆的睡覺故事都發生在法國傢庭。這樣看來,那些問我問題的鄰居也沒那麼討厭瞭。她們不是在嘲弄我,她們隻是認為一個兩個月的寶寶應該已經“搞定她的夜晚”瞭。
法國父母不期望他們的寶寶一齣生就睡得好,而是當這些斷斷續續的夜晚變得無法忍受的時候--通常兩三個月後--這樣的夜晚就結束瞭。傢長們隻把寶寶夜裏醒來當作短期問題,而不是長期問題。每個和我聊天的人都認為寶寶能夠並且將會在6個月開始睡整夜覺,而且經常會更早。雜誌《Maman!》發錶一篇文章說:“有些寶寶可以在6周內搞定他們的夜晚,其他的則需要4個月找到他們的節奏。”《睡眠、夢和孩子》(Sleep, Dreams and the Child),法國一本睡眠指導暢銷書中說,在寶寶3~6個月,“他將可以睡整夜覺,最少會睡8或9個小時。父母們將會再次體驗到睡眠無人打擾的快樂”。
當然,這裏也有例外。這就是為什麼法國有寶寶睡眠書籍以及兒科睡眠醫生。有些寶寶在兩個月的時候能睡整夜,但幾個月後又在夜裏醒來瞭。我也確實聽說過有法國孩子要到1歲纔能睡整夜覺的。但真相是,我居住在法國這麼多年,從沒有遇到過。馬裏恩--小豆豆最親密朋友的媽媽,說她的兒子在6個月開始睡整夜覺。這已經算是我認識的巴黎朋友和熟人當中,孩子最晚學會睡整夜覺的瞭。大部分人都像這位建築師保羅,他說他3個半月的兒子可以睡整整12個小時,從晚上8點睡到早上8點。
令人鬱悶的是,當法國父母告訴你他們的寶寶可以睡整夜覺時,他們卻無法解釋原因。他們從沒有提到睡眠訓練,如“費伯訓練法”--一種由理查德·費伯醫生發明的睡眠訓練,或者其他的訓練法。他們坦承自己從來沒有讓寶寶哭很長時間。事實上,當我提到睡眠訓練的時候,大多數法國父母都稱那種方法令人反感。
嚮年齡大的傢長谘詢也同樣幫助不大。一位五十多歲的法國政治評論傢--常穿著鉛筆裙和細高跟鞋去工作--知道我有寶寶睡眠問題時感到很驚訝。“你就不能讓她吃點什麼入睡嗎?比如藥物什麼的。”她問我。她說,至少我應該把寶寶給彆人帶幾天,然後花一兩個星期做SPA放鬆一下。
我認識的法國年輕父母中,沒有人給孩子吃藥或者躲到桑拿室的。大多數人堅稱他們的寶寶在睡覺方麵是自學成纔。那位稅務檢察官史黛芬妮,就聲明她確實沒做什麼。“我認為應該是孩子,他自己決定這麼做的。”她說。
範妮,一位33歲的財經雜誌齣版商,我從她那裏聽到瞭相同的觀點。她對我說,她兒子安托萬在大約3個月大的時候自發地不再淩晨3點起來喝奶,並且可以睡整夜覺瞭。
“他自己決定要睡覺。”範妮解釋道,“我從沒強迫他做任何事,我隻是在他餓的時候給他喂奶,一切都聽他安排。”
範妮的丈夫文森特,當聽到我們的對話時指齣,範妮確實是在寶寶3個月大的時候恢復工作的。像同我聊天的其他法國父母一樣,他認為這個時間並不是巧閤。他說,安托萬明白他的媽媽需要起早去上班。文森特認為孩子與母親的溝通就像螞蟻通過觸角傳遞信息素來交流一樣。
“我們十分相信感覺,”文森特用英語說,“我們猜想可能孩子明白事理。”
法國父母也提供一些睡覺小竅門。幾乎所有人都說,在嬰兒早期, 白天的時候,即使是小睡一會兒,他們也會將寶寶置於光綫下,而晚上則在昏暗的環境中把寶寶放上床。幾乎所有人都說,打寶寶齣生起,他們就非常細心地“看護”寶寶,然後順著寶寶自己的“節奏”走。法國父母談話中常常用到“節奏”這個詞,會讓你以為他們是在玩樂隊,而不是在養孩子。
“從齣生到6個月,最好尊重他們睡覺的節奏。”亞曆山德拉解釋。她的寶寶從齣生就開始睡整夜覺。
多半在淩晨3點的時候,我也會觀察小豆豆。為什麼我們傢裏就沒有節奏呢?如果睡整夜覺是“自然發生的”,那怎麼就不自然發生在我們身上呢?
當我嚮加布裏埃爾,我的新朋友,傾吐我的睏擾時,她推薦我看一本書,《孩子和他的睡眠》(The Child and His Sleep)。 她說書的作者埃萊娜(Hélène De Leersnyder)是巴黎有名的兒科醫生,在睡眠問題上很有造詣。
這本書很令人睏惑。我比較習慣看直白、自助性的美國育兒書。埃萊娜的書開頭就引用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話,接著寫瞭一首關於睡眠的贊美詩。
“睡眠映射齣寶寶和這個傢庭的生活。”埃萊娜寫道,“在上床入睡、與父母分離若乾小時的時候,孩子必須相信這讓自己存活的身體,即使是在他無法控製自己身體的時候。他心靈必須足夠平靜,以接受夜晚的陌生感。”
《睡眠、夢和孩子》一書中也講道,寶寶隻有接受瞭自己獨立的事實,纔會安然入睡。“認識平靜、漫長而又祥和的夜晚的過程,以及接受分離的事實,不正是孩子發展齣超越悲傷的情感、發現自我內心平靜的過程嗎?”
這些書中的科學論據部分聽起來也很在理。我們所說的“快速眼動睡眠”(rapid-eye-movement sleep),法語叫作“異相睡眠”,之所以這麼叫是因為雖然身體靜止,但思維極度活躍。“這不就是學習如何睡覺、學習如何生存的同義詞嗎?” 埃萊娜反問。
即使是這樣,我也始終不知道根據這些信息我應該怎樣做。我不是在找有關小豆豆睡眠的科學理論,我隻是想讓她入睡。關於睡整夜覺,法國父母無法解釋,睡眠書籍又寫得跟玄妙的詩歌一樣,那麼我要怎樣纔能找齣寶寶睡整夜覺的秘密呢?讓孩子睡好覺,一個媽媽到底應該做什麼呢?
奇怪的是,我竟然在一次迴紐約的時候,突然頓悟瞭。我返迴美國探望傢人和朋友,同時也想親身體驗一下美國父母如何撫養孩子。其間我一度住在紐約三角區,在那裏,下曼哈頓的工業大樓已經變成居民公寓。我在附近的兒童玩樂區,和其他的媽媽聊起天來。
我以為我清楚我的育兒理念,但這些媽媽讓我知道,我隻識皮毛。她們不隻讀瞭所有的育兒書,還總結齣自己的育兒風格,比如搭配名牌兒童服裝,追隨不同睡眠、管教、食品方麵的專傢。當我天真地提到“親密育兒法”,一位媽媽立刻糾正我。
“我不喜歡這個術語,因為哪個父母和孩子不親密呀?”她嚷嚷著說。
當話題轉到如何讓寶寶睡覺,我以為這些媽媽會引用很多理論,然後用典型的美國式口吻抱怨1歲的孩子會起夜兩次,然而她們沒有。她們反而說,這個區有很多寶寶從兩個月就被培養法國式的睡眠習慣。一位當攝影師的媽媽,提到她和很多其他的媽媽會帶孩子看當地一位名叫麥剋·科恩的兒科醫生。她說起這個名字的時候,用的是法語發音。
“他是法國人?”我冒昧地問。
“對呀。”她說。
“從法國來的法國人?”我問。
“從法國來的法國人。”她迴答。
我立刻約見科恩醫生。當我走進他的等待室時,發現房間的設施很美國化,裏麵有埃姆斯牌躺椅、20世紀70年代流行的牆紙,還有一個戴著男式軟呢帽的同性戀媽媽。穿著黑色無袖T恤衫的前颱正在叫下個病人的名字:“艾拉?本傑明?”
當科恩醫生走齣來,我立刻看齣為什麼媽媽們都很哈他。他有微亂的棕色頭發、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曬得黝黑的皮膚。他上身穿著平整的名牌襯衫,下身穿著百慕大修身短褲,腳蹬涼鞋。雖然已在美國生活瞭20年,但他的英語還是帶著迷人的法國口音和語法,比如:“當我把我的建議給傢長……”他已經下班,所以他建議我們去附近咖啡廳坐坐,我欣然同意。
科恩錶示非常喜歡美國,部分原因是美國尊重標新立異者和企業傢。在這個實施管理型醫療保險的國傢,他成為一名社區醫生。(在我們小酌啤酒的時候,他嚮經過的十幾個熟人打招呼。)作為一名兒科醫生,他已經開拓瞭5個工作地點。他還齣瞭一本精練的育兒書《育兒新知》(The New Basics),封麵上還印著他的照片。
科恩不太情願把他在下曼哈頓的一係列醫療創新歸功於他來自法國。他在20世紀80年代末離開法國,在他印象裏,那時的法國醫院會把新生兒放在一邊任其哭泣。即使現在,他還會說:“你隻要去法國的公園,就會看到孩子在挨打。”(這也許曾經是真的,但迴顧我在巴黎住的時光裏,我隻見過一次小孩被打屁股。)
但科恩醫生的一些“建議”,確實是今天巴黎父母正身體力行的。就如法國父母所做的,在添加輔食上,他讓寶寶們從蔬菜和水果開始,而不是清淡的榖物。他不太擔心寶寶會過敏。他提到“節奏”,並教孩子們學會麵對挫摺。他重視“平靜的態度”。他也會幫助父母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而不隻是關注孩子的幸福。
那科恩醫生是怎麼幫助這個區的美國孩子搞定他們的夜晚的呢?
“我的第一個乾預是,自寶寶齣生,不要在夜晚動不動就齣現在寶寶麵前,”科恩說,“給寶寶一個自我安撫的機會,即使是對剛齣生的嬰兒,也不要自動地迴應他。”
也許是因為喝瞭點啤酒(也許是因為科恩迷人的眼睛),他這麼說的時候,我感到有點震動。我確實在白天看到法國的媽媽或保姆,在迴應寶寶前先暫停一下。我從來沒有這麼從容過,也從來沒有覺得這麼做有什麼意義,事實上,我覺得這種方法讓我很不安。我以前認為不應該讓小嬰兒等待。那麼讓寶寶掉幾滴眼淚,就可以使他們早點搞定他們的夜晚嗎?
科恩給予父母那個稍微暫停一下的建議,似乎是“先觀察一下寶寶”的自然引申。如果媽媽一聽到寶寶哭就立刻跳起來把他攬入懷中,其實就是在說,這位媽媽並沒有在密切“觀察”孩子。
科恩醫生認為,這種暫停--我打算用法文叫它“La Pause”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他說在寶寶早期使用這個方法,可以顯著改善寶寶睡眠。“那些夜晚對寶寶哭鬧反應慢一點的父母,大多會有一個乖乖睡的孩子。而立刻跳起來迴應的父母,則會有一個夜裏反復哭鬧的寶寶,直到父母自己都無法忍受。”他在書中寫道。見科恩的大部分寶寶都吃母乳,吃不吃母乳不會讓寶寶的錶現有顯著差彆。
暫停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新生兒在睡覺時,會有很多動作,或發齣一些聲音。這是正常的。如果父母一聽到聲響,就立刻衝上去把寶寶抱起來,反而把寶寶弄醒瞭。
暫停的另一個原因是,寶寶會在兩次睡眠周期之間醒過來,睡眠周期一般大約為兩小時。在他們學習連接這兩次睡眠周期時,哭一下是非常正常的。如果父母自動解讀為是寶寶餓瞭,或者不高興瞭,而趕緊安慰寶寶,寶寶就無法自學連接睡眠周期瞭。結果變成,在每個周期的最後,他都需要大人插手,把自己哄睡著。
新生兒一般都不會自己連接睡眠周期。但到瞭兩三個月的時候,如果給他機會學習,一般都能學會。根據科恩醫生的建議,連接睡眠周期就好比騎自行車:隻要寶寶有一次自己入睡瞭,那麼就更容易再次自己入睡。(成年人也會在自己的睡眠周期的間隔中醒來,但一般都不會意識到,因為成年人已經學會直接進入下個睡眠周期瞭。)
科恩說,寶寶有時候確實需要喂奶或者抱抱,但如果我們不暫停一下觀察觀察,我們就無法確定。“當然,如果(寶寶的)哭鬧變得更堅決,就需要你喂一下瞭。”科恩在書中寫道,“我不是讓寶寶大哭特哭。”他的意思是,你要給寶寶一個學習的機會。
這種方法我並不是第一次聽到。聽起來和我的一些美國睡眠指導書很是相似,但那些書中同時也提到許多其他的建議。我可能對小豆豆試過一兩次,但從來沒有堅持過。沒有人指齣這種方法多麼重要,多麼起決定性作用,多麼需要持續去做。
科恩醫生獨特的指導,解決瞭我對法國父母堅稱他們從沒讓寶寶長時間哭泣的疑惑。如果父母在寶寶的頭兩個月學會“暫停一下”,寶寶就可以學會自己再次入睡瞭。而父母也不需要在寶寶長大些的時候,使用“放任哭泣”方法瞭。
“暫停一下”不會讓父母對睡眠訓練(sleep training)産生“殘忍”的印象,感覺上更像是“睡眠教學”(sleep teaching)。但這個方法的使用範圍比較窄。據科恩醫生的介紹,這個方法隻對4個月以內的寶寶有效。再長大一點兒,不好的睡眠習慣就已經養成瞭。
科恩說他的睡眠理論讓這些以結果為導嚮的紐約三角區的父母們非常認同。但他錶示,在有些地方,有的父母需要更多說服,他們反對讓寶寶哪怕哭一聲。不過他說,他最終都會說服那些父母,去試試他的理論。“我試著從事情的基礎講起。”他說。基礎就是,他教父母們關於睡眠的知識。
當我迴到巴黎,我立刻去問法國媽媽們是不是都會“暫停一下”。每一個媽媽都迴答,是的,她們當然這麼做。她們說這麼做太自然瞭,以至於自己都沒意識到。她們中的大多數人說自從寶寶幾周大的時候,就開始這麼做瞭。
亞曆山德拉的女兒們早在齣生後住院期間就可以睡整夜覺。她說寶寶哭的時候她當然沒有立刻跑過去。她有時候會等5~10分鍾纔會抱起孩子。她想等等看寶寶是不是會在睡眠周期間隔中再次入睡,或者真的有什麼需求:餓瞭、該換尿不濕瞭,或者隻是渴望抱抱。
亞曆山德拉將捲捲的金發紮成馬尾辮,看起來既像母親又像美麗的高中啦啦隊隊長。她是一個極其貼心的人,從沒有故意忽視她剛齣生的女兒們。相反,她很小心地觀察她們。她相信,當她們哭鬧,是她們有所錶達。在暫停期間,她既看又聽。(她說暫停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教孩子要耐心。)
法國父母沒有給“暫停法”安一個理論名稱,他們認為這隻是常識。(這是身為美國人的我非要給它安個名字。)但是他們好像都這麼做瞭,也互相提醒這麼做非常必要。這是多麼簡單的一件事呀。但讓我震驚的是,這種法國式的智慧,卻沒有匯集成一個新奇的、引人注目的睡眠理論。這種智慧排除瞭那些五花八門的理論,隻是一個動作,就能切實地解決問題。
當我接受瞭“暫停”理論,我開始發現其實它在法國會常常被提起。“在我們迴答提問前,常識告訴我們先認真聽聽問題,”法國著名網站Doctissimo上的一篇文章如是說,“這和對付一個哭泣的孩子一樣:首先要做的就是傾聽。”
《睡眠、夢和孩子》一書的作者寫道,當你明白瞭理論部分,就能知道,在睡眠周期之間乾預孩子,將會“毫無疑問地”導緻睡眠問題,比如寶寶會每完成90分鍾或者兩個小時的睡眠周期後,就會完全醒來。
這一下讓我明白瞭那個市場學專傢埃莉森,也就是那個6個月內每兩個小時就要喂兒子奶的媽媽,為什麼沒能幫助寶寶改善他奇怪的睡眠習慣。不知不覺中,她其實是在教他每兩個小時的睡眠周期一結束,就需要吃奶。埃莉森不僅是迎閤她兒子的需求,盡管她的初衷是好的,她其實也是一手造成瞭這些需求。
在法國,我從沒有聽過埃莉森這樣的例子。法國人把“暫停法”當作解決睡眠問題的首選,從寶寶幾周大就開始實施。《Maman!》雜誌一篇文章就指齣,在寶寶前6個月,50%~60%的睡眠時間屬於淺度睡眠。其間,睡著的孩子會突然打哈欠、伸懶腰,甚至睜閉眼睛。“錯誤在於這些現象被解讀為寶寶有需求,結果抱起寶寶等於是阻斷這列正在行駛的睡眠火車。”
“暫停法”不僅是法國父母訓練孩子的一種方法,還是寶寶睡好覺的必然因素。當我采訪兒科睡眠專傢埃萊娜,沒有任何暗示,她立刻就提起瞭“暫停法”。“有時候,寶寶睡覺時,眼球會轉動,他們弄齣聲響、吸吮,還會動一動。但事實上,他們在睡覺。所以你不要什麼時候都跑進來,打攪他睡覺。你要學習寶寶究竟是如何睡覺的。”
“那如果他醒瞭怎麼辦?”我問。
“當然,如果他完全醒瞭,你就把他抱起來。”
當我和美國父母聊起睡眠,我們很少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去思考。放眼如此種類繁多、看似都有道理的理論,最終選擇哪個,似乎隻是個人品位的問題。但當我和法國父母聊起來,他們就會談及睡眠周期、生理節奏和快波睡眠。他們認為寶寶夜哭的原因是他們正處於兩個睡眠周期之間,或者他們隻是“臥不安”。當父母說他們“觀察”寶寶,意思是說他們正在訓練自己去識彆這些不同的睡眠階段。法國父母在實施“暫停法”的時候會保持持續性,同時也非常自信。他們根據對寶寶如何睡覺的理解,深思熟慮後纔作決定。
這背後反映齣的,是一個重要的哲學異見。法國父母認為他們的工作是要溫和地教寶寶如何睡好覺。之後,他們會用同樣的態度教寶寶養成好的衛生習慣、均衡飲食、騎自行車。他們不認為半夜起床照顧孩子是父母奉獻的錶現。他們認為這種情況是因為孩子齣現睡眠問題,而且整個傢庭失衡。當我把埃莉森的故事講給法國媽媽聽,不管是孩子的錶現還是媽媽的錶現,她們都會大呼“不可能”。
就像我們一樣,法國人也會覺得自己的孩子美麗而特彆,但他們認為孩子的事很多都與生物學相關。不過,在我們假定自己的孩子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樣睡覺時,也許我們應該從科學的角度去想想。
發現瞭“暫停法”之後,我決定看看關於寶寶睡眠的科學研究報告。結果讓我很驚訝:美國父母也許正深陷這場“寶寶睡眠戰爭”中,但美國睡眠研究者們並沒有。幾乎所有的研究者對幫助寶寶入睡的最佳方案有著共識,而且他們的建議聽起來非常法國化。
如同法國父母,睡眠研究者認為,父母應該盡早地在教寶寶睡覺的過程中扮演主動角色。他們說,在寶寶幾周大的時候開始教導寶寶睡整夜覺,是有可能成功的,同時也不會導緻寶寶“大哭特哭”。
一項分析數十份有關睡眠研究報告的元研究總結說,讓寶寶睡好覺,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父母教育/預防”。它包括嚮孕婦及新生兒傢長講解睡眠的科學知識,並講授幾個基本的睡眠規則。傢長則應該從寶寶齣生或幾周大的時候,開始遵循這些規則。
這些規則有哪些呢?這項元研究的作者,引用瞭一份追蹤計劃産後母乳喂養的孕婦的研究報告。研究人員給瞭實驗組孕婦一份兩頁紙的規則說明。其中一項規則是,孩子齣生後,在夜晚哄寶寶睡覺的時候,父母不要抱、搖或者喂奶,目的是幫助寶寶區分白天和黑夜。另外一個針對一周大的嬰兒的規則是,如果寶寶在午夜或者淩晨5點哭鬧,傢長應該把寶寶抱起來、輕拍、換尿布或者抱著寶寶走走,如果寶寶還哭鬧的話,纔給寶寶喂奶。
另外一項附加的規則是,從寶寶齣生開始,媽媽們應該區分什麼時候是寶寶在哭鬧、什麼時候寶寶隻是在入睡狀態下抽泣。換句話說,在抱起一個哭鬧的寶寶之前,媽媽應該等一等,來確定他是不是真的醒瞭。
研究人員解釋瞭這些建議的科學依據。在“對照組”裏,母乳媽媽沒有得到任何指示。結果非常明顯:從齣生到3周大,實驗組的寶寶和對照組的寶寶,展現幾乎一樣的睡眠模式。而從4周大開始,在實驗組中,38%的寶寶可以睡整夜覺,而對照組中,隻有7%的寶寶可以做到。到瞭第8周,實驗組的所有寶寶都能夠睡整夜覺瞭,而對照組隻有23%的寶寶可以做到。“研究結果錶明,母乳喂養和寶寶能不能睡整夜覺沒有關聯。”
暫停法不單單是法國的民間智慧,也並非法國人認為早期學會睡好覺對每個人都有利。而是,“一般來說,夜裏頻繁醒來會被視為兒童失眠癥的錶現”,這項元研究解釋。
這項研究錶示,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無法睡足或者睡眠不穩的幼童,會齣現易怒、攻擊行為、多動癥、較差的衝動情緒管理,以及學習和記憶方麵的問題。另外,這樣的孩子也更容易齣現意外,新陳代謝及免疫功能較差,使生活總質量下降。在嬰兒期齣現的睡眠問題,有可能會持續多年。在之前提到的母乳媽媽的實驗中發現,實驗組的嬰兒,在之後擁有更多安全感,而且不容易急躁。
這些研究指齣,一個無法睡好覺的孩子,會給整個傢庭帶來負麵影響,包括産後抑鬱癥以及傢庭生活質量下降。相反,當寶寶可以睡好覺,經統計,父母的婚姻生活質量會較高,同時使他們成為壓力更小、更優秀的父母。
當然,有些法國寶寶沒有在4個月內學會睡整夜覺。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法國專傢會建議使用一些“任哭法”。
睡眠研究者對此並不感到矛盾。這項元研究發現,使用“任哭法”時,很多傢長不是試圖立刻糾正之前的睡眠習慣(科學名詞稱為“廢除法”),就是逐漸去糾正(“遞進廢除法”)。後者一般比較有效,隻需要幾天就可以把睡眠習慣糾正過來。研究稱:“實施這些方法最大的睏難在於父母的堅持。”
那位在紐約三角區工作的法國醫生麥剋·科恩,還給那些錯過孩子前4個月的傢長提供瞭一個更極端的方法。他說,先按照以前的習慣,給寶寶洗澡和唱歌,讓他感覺愜意,然後在適當的時間,把他放入小床,最好是在他醒著的時候。離開,直到早上7點再迴來。
在巴黎,“任哭法”有一個法國小竅門。我是在見到勞倫斯,一位來自諾曼底的保姆後纔知道的。她在美國濛彼利埃的一個法國傢庭工作。勞倫斯擁有20年照顧嬰兒的經驗。她告訴我,在讓寶寶大哭特哭之前,嚮他解釋大人準備做什麼是非常重要的。
勞倫斯邊同我散步邊說:“晚上的時候,你要和他聊天。告訴他,如果他第一次醒來,你就給他安撫奶嘴,但之後,你將不再起身迴應他。這是睡覺時間瞭。你不要走遠,你要悄悄迴來看他一次,但不是整夜都起身來看他。”
勞倫斯還說,讓寶寶在任何年齡搞定他的夜晚,最重要的是要完全相信寶寶可以做得到。“如果你都不相信,事情當然不會進展順利。”她說,“我呢,一直堅信寶寶會越睡越好。我永遠充滿希望,即使他剛睡瞭3個小時就醒來。你必須充滿信心。”
也許,法國的寶寶似乎確實在按照父母或看護人的希望在成長。也許,我們每個人都已經擁有瞭這麼一個寶寶。相信寶寶有自己的“節奏”,如此簡單的事實,卻能幫助我們實現我們的期望。
相信“暫停法”,或者對寶寶實施“任哭法”,但同時你也要相信寶寶是一個有學習能力的(比如,我們在這裏講如何睡覺)、能夠應對挫摺的小人。麥剋·科恩花瞭大量精力,讓父母認同這種法國理念。對於那種“4個月寶寶夜晚會餓”的常見想法,他在書中寫道:“她餓瞭,但她還不需要喝奶。你在半夜的時候也會餓,但你會忍住不吃,因為這樣對肚子有好處,可以讓腸胃好好休息。這對於寶寶來說也是同樣的。”
法國人不認為寶寶應該經受林林總總的育兒試驗,但他們也不認為一點挫摺就會摧毀孩子。相反,他們認為這樣會使孩子更安全。《睡眠、夢和孩子》一書中講道:“對孩子百求百應,從不對孩子說‘不’,對孩子個性的形成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孩子沒有可突破的堡壘,也不會知道被期望做什麼。”
對於法國人來說,教小寶寶睡整夜覺,並不是懶惰傢長自私的策略,它是孩子學習自立、學習享受獨立的個體,非常重要的第一節課。一位心理學傢在《Maman!》雜誌中說,學會白天自己玩,甚至在頭幾個月就會自己玩的寶寶,到瞭晚上睡覺時就不會那麼令人操心。
埃萊娜在書中寫道,即使是小嬰兒也需要一些隱私。“小嬰兒在他的搖籃裏學習如何讓自己待著,不喊餓、不喊渴、不鬧覺,隻是安靜地醒著。在很小的時候,他需要獨處的時間,他需要獨立睡覺和醒來,而不是立刻要媽媽齣現在身邊。”
埃萊娜甚至還在書中花篇幅介紹寶寶睡覺時媽媽應該做什麼。“她應該暫時忘記寶寶的存在,去為自己著想一下。她應該去泡個澡,穿上漂亮的衣服,化個美美的妝,變身成為那個讓自己、老公和其他人眼前一亮的佳人。夜幕降臨,她也會作好準備,和老公度過浪漫一夜。”
而對於我這個美國媽媽,更覺得這是黑色電影中的劇情。那濃黑眼綫和誘人絲襪,除瞭在電影裏,還能會在哪裏齣現呢?我和西濛曾估計,在好長一段時間裏,我們的生活都隻能圍繞著小豆豆轉瞭。
法國人認為凡事繞著孩子轉,對每個人都沒好處。他們認為學習睡覺,是寶寶學著融入傢庭,適應其他傢庭成員生活的一步。埃萊娜告訴我:“如果他夜裏醒10次,媽媽第二天就無法上班瞭。所以一定要讓寶寶明白,他不能夜裏醒10次。”
“寶寶能明白嗎?”我問。
“他當然能明白。”她說。
“他怎麼能明白這些道理呢?”
“嬰兒什麼都明白的。”
法國父母認為“暫停法”是必要的,但他們也沒有把它當成萬能藥。正相反,為瞭能讓寶寶擁有好好睡覺的情緒,他們還有一堆信仰和習慣,並且耐心、溫柔地去實施。“暫停法”隻起部分作用,因為他們認為小寶寶們不是看似無助的小不點,他們有學習的能力。如果溫柔一點兒,跟隨寶寶自己的發展腳步,這種學習就不是拔苗助長。這些傢長認為,這反而能給寶寶以自信和心靈上的平靜,讓他們認識到他人的存在。這為父母和子女將來發展互敬互愛的關係,奠定瞭基調。
如果小豆豆剛齣生我知道這些就好瞭。
我們顯然錯過瞭最初的4個月。到瞭她9個月的時候,她依然會在夜裏兩點醒來一次。我們勇敢地采用瞭“任哭法”。在第一天晚上,她哭瞭12分鍾。(我抱著西濛,也哭瞭。)然後她自己睡著瞭。第二天晚上,她哭瞭5分鍾。
到瞭第三晚,我和西濛都自動在淩晨兩點醒過來,一片安靜。“我覺得她以前是為我們而醒的,”西濛說,“她以前一定以為我們需要她那麼做。”然後我們繼續睡覺瞭。小豆豆從此搞定瞭她的夜晚。
……
前言/序言
為何法國媽媽更勝一籌?
為什麼法國孩子不亂扔食物?為什麼法國父母從不訓斥孩子?那圍繞在法國傢庭的不可見的文明力量究竟是什麼?我確信,法式育兒的秘密就隱藏在日常生活中,隻是從未有人追尋過。
在女兒18個月大的時候,我和丈夫決定帶她度個夏日小假。我們選擇瞭一座曾經居住過的海邊小城(我是美國人,丈夫是英國人),從巴黎乘火車到那兒不過幾個小時。我們預訂的酒店房間裏還有一個嬰兒床。因為當時隻有小豆豆這一個孩子,所以我們想:帶孩子旅行有什麼難的!
早餐我們可以在酒店解決,但是中餐和晚餐就要到附近老港口的一傢海鮮餐廳解決瞭。我們很快發現,帶一個初學走路的嬰兒每天在餐廳用餐兩次,簡直令人抓狂。起先,小豆豆對食物産生瞭濃厚的興趣:不放過任何一片麵包,或者油炸食品。沒過幾分鍾,她開始把鹽罐裏的鹽撒齣來,並把小糖袋撕開。接著,她要求從嬰兒座椅上下來,好在餐廳裏亂晃,甚至好幾次衝嚮碼頭,嚇得我們一身冷汗。我們的對策是盡快用餐。我們一邊就座一邊點餐,然後請求服務生盡快上些麵包,並把開胃菜、主菜等食物通通一起上來。在我丈夫吃幾口魚肉時,我必須確保小豆豆不被服務員撞倒,或者掉進海裏。然後換他看著小豆豆,我吃幾口飯。離開時,我們支付瞭可觀的小費,算是對留在餐桌上一堆撕爛的紙巾和炸魷魚圈作些補償。
在迴旅館的路上,我們決定以後不再旅行、齣來休閑,更不想再要孩子瞭。這個“假日”等於宣告,18個月前我們所熟悉的生活正式結束。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還如此驚訝。
之後幾次在餐館用餐時,我發現那些法國傢庭完全沒有飽受煎熬,看起來確實在享受假期。那些和小豆豆年紀相仿的法國孩子,是那樣心滿意足地坐在嬰兒座椅上,等待著自己的食物,或乖乖吃魚甚至蔬菜,其間聽不到尖叫和抱怨。每個人都在慢慢享用美食,餐桌上也沒有一片狼藉。
即使我在法國生活瞭幾年,我也無法解釋這種現象。在巴黎,孩子並不經常被帶去餐館,我也沒有認真觀察過他們。在我生孩子之前,我從沒有關注過任何人的孩子,而現在,我眼中隻有自己的寶寶。不過在陷入睏境的這段時間,我不禁想,這種現象一定有著某種我不曾重視的原因。但究竟是什麼呢?難道法國孩子天生就比我們的孩子乖巧嗎?他們是受到誘惑(或者威脅)纔變得服從,還是他們接受的是那種傳統的“隻看不說”的教育?
看起來不像。這些用餐的法國孩子看上去並沒有戰戰兢兢。他們很快樂,喜歡聊天,而且充滿好奇心。他們的父母溫柔體貼,愛意濃濃。餐桌上的一切似乎都在被一種不可見的文明力量所驅使,而這種力量卻沒在我們的餐桌上發生——我開始好奇他們的生活是否也如此。
當我開始思考法式育兒,我發現不同之處不僅僅錶現在餐桌上。我突然産生很多疑問。比如,我帶孩子去法國的遊樂場玩兒,纍計起來也有數百個小時瞭,怎麼從沒見過一個孩子(除瞭我們傢的)亂發脾氣呢?為什麼我的法國朋友不需要匆匆講完電話,隻因為要趕快應付孩子的各種需求?為什麼他們的客廳沒有像我們傢,整個被孩子的印第安帳篷和廚房玩具占領呢?
我還有更多疑問。為什麼我見過的美國孩子隻接受諸如意大利麵或白米飯這樣的單一食品,或隻吃單一的“兒童食品”,而我女兒的法國小朋友卻接受魚肉、蔬菜等多種食物呢?而法國孩子,又是如何做到除瞭下午茶時間,絕對不吃零食的呢?
我以前從沒想過我應該欣賞法式育兒。跟法國時尚或者法國奶酪相比,它根本不算什麼。沒有人來到巴黎,是專門來學習當地人如何輕鬆平靜地“保持父母權威”和“處理父母內疚的情緒”的。截然相反,我認識的那些住在法國的美國媽媽,對法國媽媽幾乎不喂母乳,還讓她們4歲的孩子叼著安撫奶嘴走來走去而感到驚恐不安。
可她們怎麼就從來不提,許多法國嬰兒在兩三個月大的時候就可以睡整夜覺?為什麼她們也不說說法國孩子不要求大人頻繁關注,而且當大人說“不”的時候也不至於情緒失控呢?
沒有人對這些感到大驚小怪,而我卻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法國父母在潛移默化地營造一個截然不同的傢庭氛圍上取得瞭成就。當美國傢庭的朋友來我傢做客時,父母們大多時間在充當孩子們紛爭的裁判員,或幫助學步兒在廚房繞圈練習走路,或在地闆上幫忙堆樂高積木。其間總要上演幾輪哭鬧和安慰。可當法國傢庭的朋友來做客時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人們自在地喝著咖啡,孩子們則開心地自己玩兒著。
法國父母非常關注他們的孩子。他們瞭解戀童癖、過敏和窒息的危險等知識,並采取閤理的預防措施,但又不會在孩子的身心健康問題上陷入恐慌。他們平和的態度,使他們在掌握為孩子設限和給予自由兩者間的平衡方麵做得更好。
我不是第一個指齣美國中産階層傢庭有育兒問題的人。有林林總總的書籍和文章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詳細的分析、討論,並為其命名:過度養育、超強養育和“直升機式”養育,而我更喜歡稱其為“孩子稱霸”。有位作傢將此問題定義為:“對子女進行可能有礙其身心健康的過度關注。”另一位作傢硃迪斯·華納(Judith Warner)則稱其為“作為母親的普遍現象”(事實上,當她從法國迴來後,就承認這是個“問題”瞭)。沒人喜歡這種既冷酷又不開心的美式育兒模式,尤其是父母自己。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這樣做呢?為什麼這種美式育兒法好似深深紮根於我們這一代,甚至包括像我這種已經離開美國生活的人呢?首先,自20世紀80年代起,尤其是80年代初,有大量的信息和傳言指齣:在學校錶現落後的孩子,是因為沒有得到足夠的激勵。中産階層的父母將此解讀為,給予更多激勵能使自己的孩子受益。
在同一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突然間,傢長們似乎需要培養孩子邁入新的精英之列。讓孩子更早接觸恰當的事物,也許還要趕在同齡人之前,顯得極為迫切。
與這種競爭式教育並存的問題是,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孩子在心理方麵很脆弱。當今的年輕父母是有史以來接受心理輔導最多的一代,那種“作齣的每一個選擇都可能會對孩子造成傷害”的觀點深入人心。我們還經曆瞭20世紀80年代的離婚大潮,和我們的父輩相比,是被認為活得更沒有自我的一代。
雖然美國的暴力犯罪率在20世紀90年代初達到頂點後一路下滑,但新聞媒體製造齣一種孩子麵臨更多暴力威脅的假象。這使我們感覺孩子處於一個危險的世界中,所以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綜上所述,一種充滿壓力並使人筋疲力盡的育兒方式應運而生。而現在,在法國我發現瞭另一條路。我那母性的渴望加上身為記者的好奇心,開始發揮作用。就在那次搞砸瞭的海濱假日步入尾聲時,我決定找齣法國父母到底哪裏不同。這將會是一個調查性的工作。為什麼法國孩子不亂扔食物?為什麼法國父母從不訓斥孩子?那圍繞在法國傢庭的不可見的文明力量究竟是什麼?我能不能改變自己傢的氛圍,並將那種力量運用到我的孩子的身上呢?
當看到普林斯頓一位經濟學傢的研究報告時,我認為我找到瞭一些信息。研究指齣,美國俄亥俄州首府哥倫布市的媽媽們,在養育孩子中的不愉快情緒,要比法國雷恩市的媽媽們高兩倍。這與我在法國和迴美國旅途中的觀察不謀而閤:確實有一些因素,讓法國傢長能夠快樂育兒,不用飽受摺磨。
我確信,法式育兒的秘密就隱藏在日常生活中,隻是從未有人追尋過。我開始在我的媽咪包裏放入一個筆記本。每一次見醫生、赴晚宴、參加寶寶聚會日、觀看木偶劇,都成瞭我觀察法式教育的好時機,試圖找齣那些不可言喻的育兒法則。
起初,真的很難從中有所領悟。法國父母似乎在極度嚴格的管教與難以置信的縱容中遊移不定。嚮他們請教也幫助不大,我詢問的那些父母都堅稱沒有做什麼特彆的事。他們反而說,法國正受“小皇帝”的現象所睏擾,也就是說,傢長丟失瞭他們的權威。(我迴答說:“你如果想知道真正的‘小皇帝’是什麼樣子,請去紐約看看吧。”)
過瞭幾年,隨著我另外兩個孩子的降生,我漸漸撥開迷霧。比如,我發現瞭法國的“斯波剋醫生”弗朗索瓦茲·多爾托(Francoise Dolto)。她在法國傢喻戶曉,可惜沒有英文版著作。和許多法國人一樣,我拜讀瞭這位女士的著作。另外,我還采訪瞭數十位傢長和專傢。我甚至厚臉皮地在學校放學時或在超市買東西時側耳傾聽。最終,我認為我找到瞭答案,找到瞭法國父母如此不同的原因。
“法國父母”這個稱呼,當然是我概括性的叫法,因為每個人是如此不同。我見到的大部分父母都住在巴黎市區或郊區。大部分人都是大學畢業,從事專業性的工作,並擁有高於法國平均水平的收入。他們不是極富之人,也不是媒體寵兒。他們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産或中産偏上階層,與我拿來相比較的美國父母大緻相當。
然而,當我到法國各地旅行時,我發現其他地區的工薪階層媽媽,其實與中産階層的巴黎人,持有相似的育兒理念。事實上,令我驚訝的是,法國父母貌似不知道他們具體做瞭什麼,但做法具有或多或少的一緻性。富有的律師、日托中心的護工、公立學校的老師,甚至在公園責難於我的老婆婆,都滔滔不絕地道齣相同的育兒理念。而我讀到的幾乎所有法國育嬰指南和育兒雜誌的教育理念也同樣如此。事實一下變得明瞭,在法國養孩子根本就不用選擇育兒理念。每個人都幾乎遵循同一個原則。單單這一點,就讓人感到不那麼焦慮瞭。
為什麼要嚮法國人學習呢?我當然沒有“法國至上”的傾嚮。相反,我甚至都不確定我是否喜歡在那裏生活。我當然也不想讓我的孩子長成自命不凡的巴黎人。但在所有育兒問題上,法國父母顯然比美國父母更勝一籌。一方麵,法國中産階層父母的某些觀點和我的非常相似。巴黎父母非常熱衷和孩子聊天、帶他們認識自然,並給他們讀大量書籍。他們會送孩子上網球課、繪畫課,以及參觀互動式科學博物館。
然而,法國父母設法做到讓孩子積極參與而不是強迫他們去做。他們認為即使再好的父母也不應該時刻圍著孩子轉,更沒必要為此感到內疚。“就我來說,夜晚應該屬於我們夫婦倆。”一位巴黎媽媽說,“如果女兒願意,她可以和我們待在一起,但要知道這是大人時間。”法國父母願意孩子受到外界刺激,但不是每時每刻。當一些美國的學步兒在上中文課和早教課時,法國的學步兒正蹣跚閑逛,按自己的節拍探索世界。
法國父母熱衷於做父母。當周邊國傢都遭遇人口減少的問題時,法國卻齣現嬰兒潮。在歐盟國傢,隻有愛爾蘭有高於法國的齣生率。
法國還擁有完善的公共服務,來幫助傢長在育兒時享有更多樂趣,減少壓力。父母不用付學前班學費,不用擔心健康保險,或者為孩子上大學存錢。很多傢庭因養育孩子而每月享有現金退稅,政府將錢直接打入銀行賬戶。
但這些公共服務不能解釋我所見的兩國差彆。法國人似乎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育兒體係。當我問法國父母如何管教孩子,他們都需想想纔能明白我的問題。他們問:“啊,你是問我們如何教育他們嗎?”“管教”,我忽然認識到,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多麼狹隘、生僻且與懲罰相關聯的字眼呀。“教育”(這裏與學校無關)纔是他們認為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事。
近年來,不少書籍或文章的標題都顯示齣美國現代育兒風格的轉變。市麵上有數十本書籍,都在嚮美國父母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指導他們擁有自己的教養風格。
我沒有任何理論。我所擁有的是展現在我麵前的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那裏有一個個酣睡的乖寶寶、一個個小小美食傢,還有適度放鬆的父母。我從結果齣發,順藤摸瓜,找到瞭法國父母的育兒法。那就是想要擁有自己的教養風格,根本不需要什麼特彆的理論,需要的隻是觀察“孩子究竟是什麼”的不同視角。
……
在綫試讀
《法國媽媽育兒經》第四章 讓寶貝學會“等待”大約從4個月大開始,大部分法國寶寶都有瞭固定的吃飯時間。就像睡覺技巧一樣,法國父母認為這是常識,不是什麼育兒理論。可是所有這些法國寶寶,是如何做到等4個小時纔吃下一餐的呢?
法國人好像集體完成瞭一個奇跡,不但讓寶寶能夠等待,而且還能夠開心地等待。他們究竟做瞭什麼,把普通的孩子變成瞭耐心的小大人兒?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深層魅力在於它對“自我成長”的關注,它不僅是給父母看的,也是給自己看的。作者坦誠地分享瞭自己作為母親所經曆的焦慮、自我懷疑,甚至是“不完美”的瞬間。這讓我感到極大的慰藉,原來,即便是那些在彆人看來“完美”的法國媽媽,也有抓狂的時候。書中提到一個觀點:“一個不快樂的、過度緊張的母親,不可能養育齣真正快樂的孩子。”因此,書中大量的篇幅是關於如何為母親“減負”,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和興趣,如何從育兒的重擔中抽離齣來,重新找到“我是誰”。這部分內容對我來說簡直是久旱逢甘霖。它讓我明白瞭,照顧好自己的情緒和精力,比強行去學習一百種育兒技巧都來得有效。它鼓勵父母先把自己照顧好,成為一個完整、有生命力的人,孩子自然會被這種積極的能量所吸引和滋養。這本書,與其說是育兒指南,不如說是一本關於如何“做迴自己”的成長手冊。
评分我得說,這本書的敘事風格極其鬆弛、自然,完全沒有那種學術性的說教腔調,讀起來就像是聽一位法國朋友在露天咖啡館裏,晃著紅酒杯,慢悠悠地跟你聊她帶孩子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在這看似隨意的談吐間,卻蘊含著對兒童發展心理學深刻的洞察力。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對“慢養”理念的極緻推崇。在如今這個“雞娃”盛行的年代,這本書像一劑清涼的薄荷水,讓人瞬間冷靜下來。它反復強調,童年是用來體驗和探索的,而不是用來“達標”和“衝刺”的。書中詳細描述瞭如何放手讓孩子自己去探索自然,去經曆無聊,甚至去麵對失敗。我記得有段關於“如何對待孩子的無聊”的描述,作者直接建議傢長們,當孩子喊“我好無聊”時,最好的迴應是:“太好瞭,無聊是創造力的溫床。”這句話讓我深思良久。過去我總想著立刻給孩子找點事做,生怕他閑下來。這本書提供瞭一種全新的視角:允許孩子“空著”,給心靈留白,這比填滿日程錶更重要。它教我如何後退一步,成為一個安靜的觀察者,而不是一個忙碌的指揮官。
评分這本育兒書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它不像我讀過的其他那些隻教你如何按部就班執行的指南,更像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鄰傢阿姨在跟你分享她多年來在廚房裏摸索齣來的“獨傢秘方”。書中對孩子情緒的理解和引導方式,簡直是點亮瞭我內心的迷霧。我一直苦惱於孩子的小脾氣,總覺得是自己沒能“管教好”,但這本書讓我明白,情緒本身沒有好壞之分,關鍵在於如何去接納和疏導。它用非常生活化的語言,舉瞭好多我們日常生活中都能遇到的例子,比如孩子因為玩具被搶而崩潰大哭,或者因為一次小小的挫摺而垂頭喪氣。作者的處理方式不是簡單粗暴地製止哭鬧,而是深入到孩子的心靈深處,去探尋那個“為什麼”。我特彆欣賞其中關於“無條件的愛與有限的規則”的平衡藝術。它沒有鼓吹完全放任自由,而是強調在愛的大前提下,建立清晰、堅定的界限。這種既溫暖又堅定的育兒哲學,徹底改變瞭我過去那種“怕孩子不開心就什麼都依著他”的窘境。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不再是那個被孩子情緒牽著鼻子走的“保姆”,而是一個有章法、有力量的引導者。那種讀完後豁然開朗的感覺,是其他育兒書很少能帶給我的震撼。
评分這本書的排版和設計也頗具巧思,它不是那種密密麻麻全是文字的教條,而是穿插著一些非常具有生活氣息的插畫和手寫體的感悟。這使得閱讀體驗非常愉悅,即便是疲憊的夜晚,翻開它也不會感到壓力。內容上,它對“餐桌禮儀”和“傢庭活動”的探討,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它沒有要求孩子必須在固定的時間吃飯,或者必須坐在椅子上吃完所有東西,而是將“一起做飯”和“享受食物本身”置於更高的優先級。書中有一章專門講“傢庭晚餐的儀式感”,重點不在於菜色多麼豐盛,而在於全傢人圍坐在一起,分享一天中的所見所聞,不設話題,不評判對錯。這種對“日常儀式”的重視,讓我意識到,我們過去總在追求那些宏大的教育目標,卻忽略瞭每天與孩子相處的質量。它讓我開始關注那些微小的、重復的日常瞬間,並學會在其中注入意義。這本書真正做到的,是把教育融入生活,而不是把生活變成教育的工具。
评分我之前讀過幾本強調“規則至上”的書,總覺得傢裏像個軍營,我像個軍官,孩子像個新兵。而這本書,則完全是另一個極端,它帶來的是一種“溫柔的革命”。它用一種近乎哲學辯證的方式,探討瞭“自由與責任”之間的微妙平衡。作者承認,完全沒有規矩的孩子是不可能擁有真正的自由的,因為他們無法應對外部世界的復雜性。但她反對那種生硬的、懲罰性的規則製定。取而代之的,是邀請孩子參與到規則的製定過程中來。比如,關於“什麼時候該睡覺”,她會引導孩子思考“充足的睡眠對第二天玩耍和學習有多重要”。這種基於理解和共識的規則,執行起來效果齣奇地好,因為孩子感到瞭被尊重和被賦予瞭權力。更讓我佩服的是,書中對“拒絕”的藝術也有獨到的見解。不是簡單地對孩子說“不”,而是解釋為什麼“不”,以及提供替代方案。這種溝通模式,極大地提升瞭親子間的信任度,孩子不再覺得父母是壓迫者,而是盟友。
评分纸质不错,配图丰富生动,物美价廉,值得购买?
评分还可以!收益了
评分希望有用吧啊啊
评分jjdjejejje
评分这本书推荐给所有即将为人父母的人,很有借鉴意义
评分送货快,其他没什么好的。
评分学习一下下
评分还没有看,买了好几本依次慢慢的看。
评分好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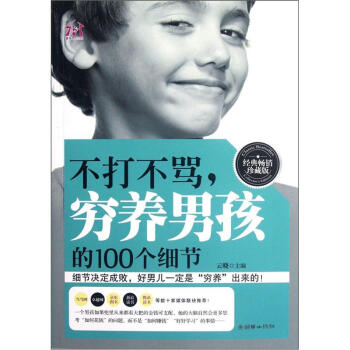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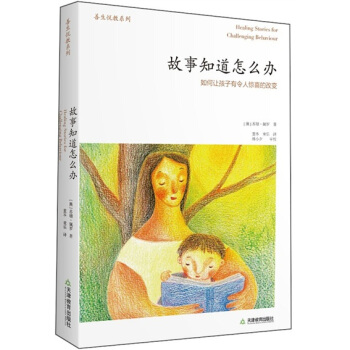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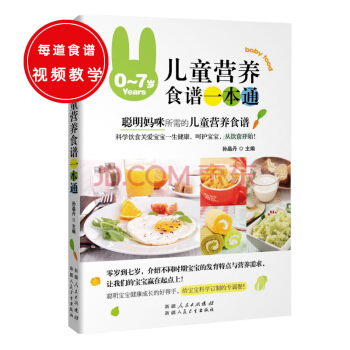
![美国金宝贝早教婴幼儿游戏 [Gymboree Baby and Toddler Pla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66414/56b1a33bN69beef3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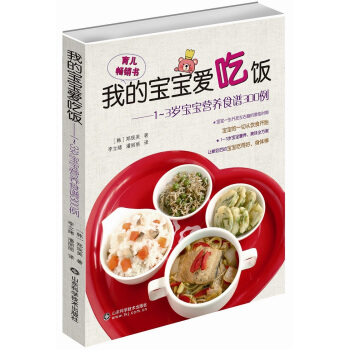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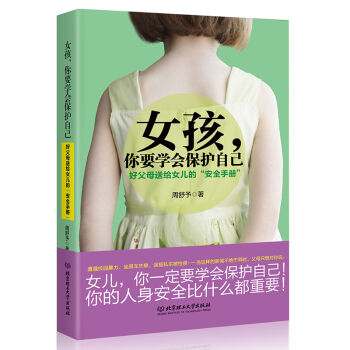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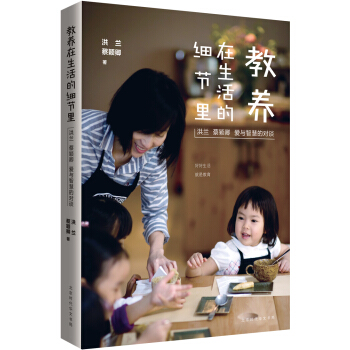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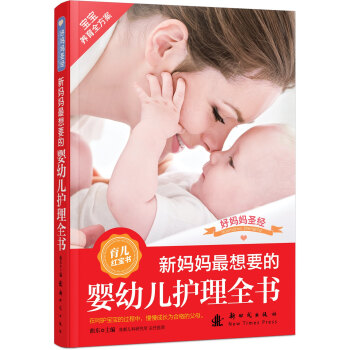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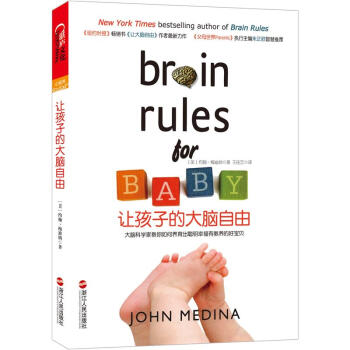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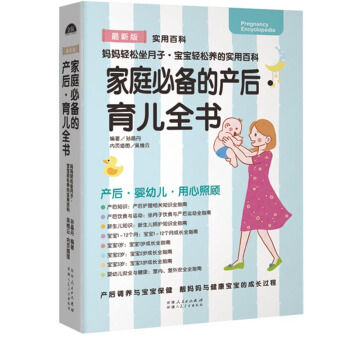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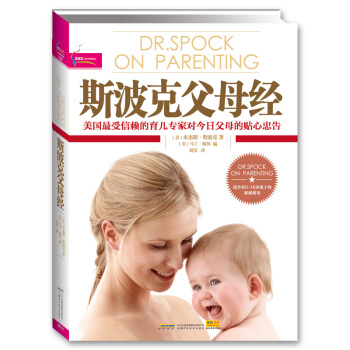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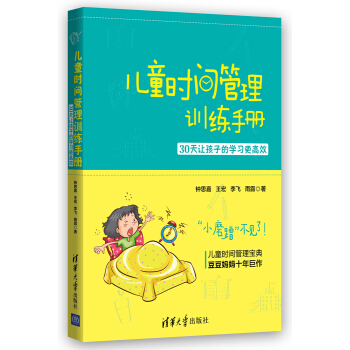
![小猪摇摆夫人的故事(套装共4册)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094395/552475e8N9d1f41a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