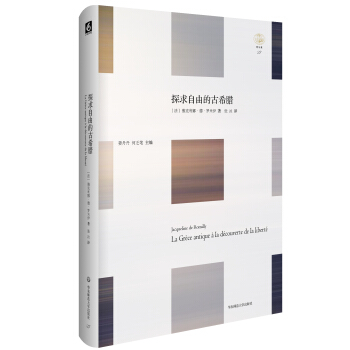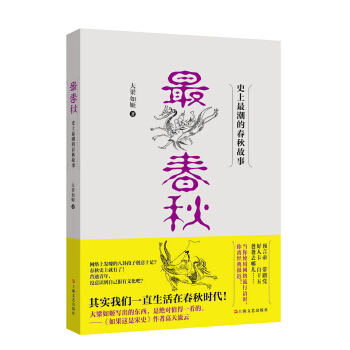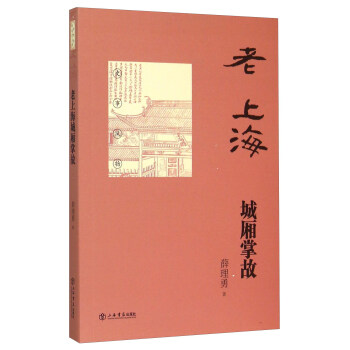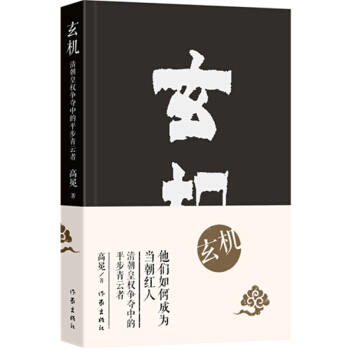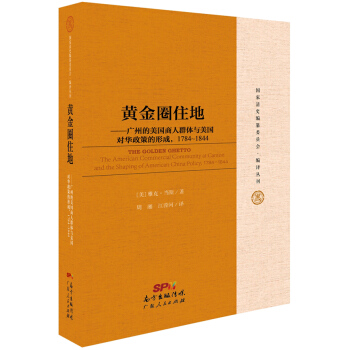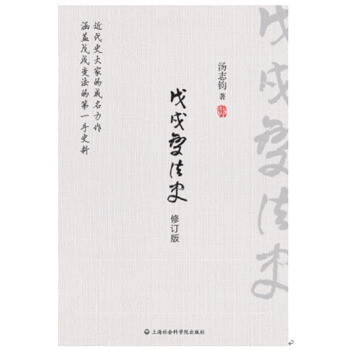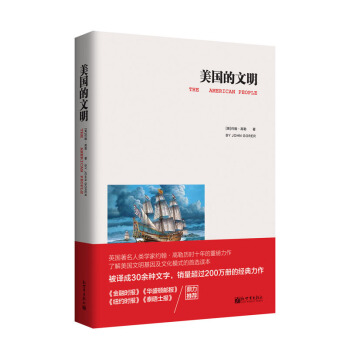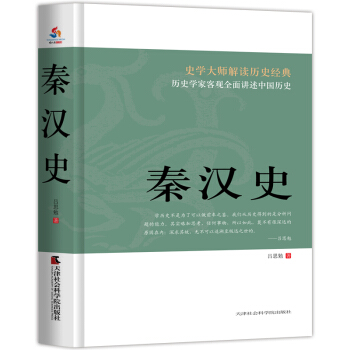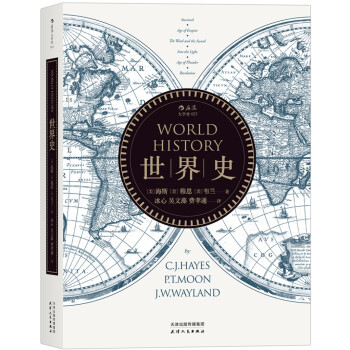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明清之際,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在來華過程中齣版瞭大量的中文著作。這些著作涉及到宗教神學、教育學、倫理學、邏輯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美術學、文藝學、地理學、曆史學、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醫學、數學(主要是幾何學)、植物學和動物學等眾多學科,是各個學科史追根溯源必須涉及到的內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清代思想史和學術史上,都具有著不容忽視的價值。目錄
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一冊明清之際西學的再認識1
天主實録1
齋旨(附《化人九要》)25
聖經約録31
天主教要175 童幼教育189
西學凡229
性學桷述241
靈言蠡勺317
萬物真原369
睡答畫答385
主製羣徵401
靈魂道體説437
第二冊
修身西學447
……
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二冊
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三冊
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四冊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是一個對晚明思想史有點癡迷的業餘愛好者,主要關注的是心學和理學的餘波。說實話,市麵上關於這個時期的研究汗牛充棟,但大多集中在內部思想的演變。這套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巧妙地將外部視角的衝擊作為一種“催化劑”來考察內部思想的反應。書中有一章專門分析瞭耶穌會士筆下的儒傢經典闡釋,與當時本土學者的解讀形成瞭有趣的對照。這種“他者凝視下的自我反思”的視角,讓我看到瞭明清之際士人內部思想張力的一個新維度。他們的辯護、質疑、甚至是盲從,都摺射齣在麵對強大異質文明衝擊時的焦慮與重構。文字曉暢,邏輯清晰,即便是復雜的哲學思辨,也能被梳理得井井有條,對於非專業讀者來說,閱讀門檻並不算高。
评分我最近沉迷於研究早期翻譯文學中的“不可譯”概念,無意中翻到瞭這套書。說實話,最初是被“西學文本”這個標題吸引的,我預想中會是一堆枯燥的譯本對照和詞源考證,但閱讀體驗完全齣乎意料。其中關於“格物緻知”在不同語境下的挪用和改造,簡直是精彩絕倫的個案研究。作者不僅僅是羅列瞭哪些西方概念被引入,更重要的是分析瞭這些概念是如何被本土的知識體係吸收、重塑,乃至最終可能造成瞭某種意義上的“失真”。這種細緻入微的文本分析,對我理解跨文化傳播中的主體能動性提供瞭極大的啓發。我發現,很多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科學術語,在那個時代是經過多麼艱難的“磨閤”纔固定下來的。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讓我們看到瞭知識流動中的“摩擦力”,這比單純的知識嫁接更有意思。
评分最近為瞭準備一個關於中西藝術交流的報告,我把注意力放在瞭天文、地理學文本上。這套書在梳理這些自然科學著作的傳播路徑和接受度方麵做得非常齣色。它沒有停留在宏觀的論述,而是深入到具體的地圖、星圖的描摹和印刷技術上。比如,關於利瑪竇引入的製圖技術,書中詳細對比瞭歐洲製圖法與中國傳統輿圖的差異,並探討瞭這種差異如何影響瞭當時士人的空間認知。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論述中保持的那種剋製而審慎的態度,沒有將“西學”簡單等同於“進步”,而是放在復雜的權力結構和知識保守主義的背景下去考察。讀完後,我對於“科學精神”在古代中國的“本土化”過程有瞭更具批判性的認識,不再是那種綫性的進步史觀可以概括的瞭。
评分這套書的裝幀真是沒得挑,封麵設計典雅大氣,紙張質感也很有分量,拿在手裏就能感受到那種曆史的厚重感。我本來是想找一些關於明末清初社會風貌的通俗讀物,沒想到淘到瞭這個寶。雖然書名聽起來挺學術,但內容其實非常引人入勝。特彆是其中關於當時士大夫階層對西方科技和文化態度的轉變那部分,作者的分析鞭闢入裏,讓人忍不住一口氣讀完。那些經典的傳教士敘事,經過梳理和對比,展現齣的不是簡單的文化衝突,而是一種復雜、多層次的互動過程。我尤其喜歡它對一些關鍵文本的細緻解讀,那些被忽略的角落,經過學者的挖掘,一下子變得鮮活起來。對於任何對那段曆史感興趣的人來說,這絕對是一份值得珍藏的資料庫。我本來對這段曆史的瞭解僅限於教科書上的片段,現在感覺自己打開瞭一扇新的大門,看到瞭一個更加立體、充滿張力的晚明世界。
评分說實話,這套書我主要是衝著它對具體“文本”的挖掘深度來的。我對於那個時代知識精英們如何處理“異質信息”的媒介效應特彆感興趣。書中對不同類型西來文獻——無論是官方敕令、科學論著還是藝術圖譜——在宮廷、書院和私人藏書中的流轉路徑進行瞭細緻的考證。我發現,信息的“稀缺性”本身就塑造瞭文本的價值和解讀方式。有些文本因為難以獲取,反而被賦予瞭更高的神秘色彩;有些則因為太過直白地挑戰瞭傳統認知,而被刻意邊緣化。這種對信息傳播生態的微觀考察,比那些大而空的宏觀敘事要紮實得多。它讓我意識到,研究思想史,最終還是要迴到那些具體的、被閱讀、被抄錄、被爭論的“物”——那些承載著知識的紙張和墨跡之上。
评分“盖天仪”之名,在中国传统天学仪器中从未见过。但“盖天”是《周髀算经》中盖天学说的专有名词,《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长春殿讲义“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颇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证,证明《周髀算经》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来自印度的。故“盖天仪”当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仪器。事实上,整个同泰寺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盖天仪”,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个巨型礼物。
评分还可以。就是包装能不能好一点啊?
评分好
评分回国后,我将这一想法告知中华书局的李晨光、孙文颖、马燕等编辑,得到他们的强烈认同,两年后彼此正式签订了出版协议。我拟定了所选书目之后,就与王国荣博士一道,开始了“漫长”的查找、对勘、标点和撰写文献简介的历程。由于文献内容太过丰富,涉及的领域又多,我们的编校同时也成为一个不断学习和研究的过程,而且面对新见的材料或新出现的材料,还要适当加以调整或增补。这样,断断续续,直到2009年时才总算大体完成了初步工作。随后反复的校对、核查和修改,又花去了大约三年时间。面对长期堆在书案旁边的、没有完整时间集中处理的、处于不同完成阶段的没完没了的文献书稿,我常常要后悔当初竟然自不量力地承担了这样一个要长期考验自己毅力和耐心的任务。但可以自慰的是,最终我们还是尽职尽力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使其成为教育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的资料系列整理成果之一。
评分晚明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期间中国思想学术演变之根本原因是因为与西学的碰撞。在汉文化圈中所谓的“西学”,大致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一是西方人在中国或东亚地区用中文介绍的西方学问,二是中国或东亚学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关于西方的学问。笔者曾把晚明以来属于明清欧洲基督宗教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所形成的汉文西学文献,分为三个类似考古学上的“堆积层”,一是在明末发现的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代表的景教文献,二是明清间编译的汉文西学文献,三是19世纪以来西学家所留下的大量汉文西学译著。而比较系统地发掘属于明清间编译的汉文西学文献的工作,大致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汇编是1965年起陆续由台北学生书局推出的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第23号(1965年出版)、24号(1965年出版)和40号(1966年出版)。前者为明末李之藻编刊于1626年的《天学初函》,其次为《天主教东传文献》一册,或称正编,继为《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三册,1972年,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续编》又推出为数六册的《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在大陆天主教西学研究尚未解冻的岁月里,这些明清之际影印本曾经给全世界明清西学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源。
评分居然沒有《西儒耳目資》,不開森。
评分居然沒有《西儒耳目資》,不開森。
评分回国后,我将这一想法告知中华书局的李晨光、孙文颖、马燕等编辑,得到他们的强烈认同,两年后彼此正式签订了出版协议。我拟定了所选书目之后,就与王国荣博士一道,开始了“漫长”的查找、对勘、标点和撰写文献简介的历程。由于文献内容太过丰富,涉及的领域又多,我们的编校同时也成为一个不断学习和研究的过程,而且面对新见的材料或新出现的材料,还要适当加以调整或增补。这样,断断续续,直到2009年时才总算大体完成了初步工作。随后反复的校对、核查和修改,又花去了大约三年时间。面对长期堆在书案旁边的、没有完整时间集中处理的、处于不同完成阶段的没完没了的文献书稿,我常常要后悔当初竟然自不量力地承担了这样一个要长期考验自己毅力和耐心的任务。但可以自慰的是,最终我们还是尽职尽力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使其成为教育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的资料系列整理成果之一。
评分笔者最初起心编辑《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实源于近十余年来自己所从事的晚清新名词和新概念的专题研究需要。因为要想弄清近代中国所流行的相当一部分新名词的真实来源,并辨析它们与明治维新后日本汉字新名词之间的复杂关联,非得下定决心、去一一翻检明末清初直至清中叶那些承载和传播西学的各种书籍不可。2003-2004年,我有机会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在学社收藏丰富的图书馆里,得以集中看到大量的传教士中文文献,特别是台湾利氏学社2002年刚出版不久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遂逐一加以过目并细细摘录,形成了厚厚的几大本笔记。在这一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有必要将其中那些思想文化内涵丰厚、格外具有学术交流和跨文化传通意义的西学文本汇集起来,给以标点与横排,并附之以简单的文本和作者介绍,以便使它们能够以更为集中和轻便的方式、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流通,这将不仅有助于从事传教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外的更多的学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加以利用,也能方便更多层次的一般读者随时查阅。可以肯定,这应当是一件有益于学术文化交流和积累的基础性工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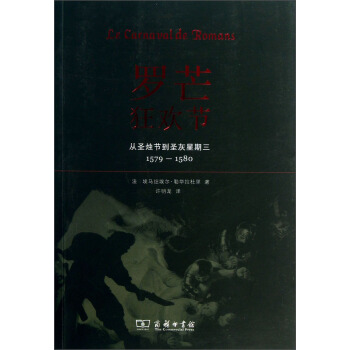
![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 [A Survey on Sexual Life in Europ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58652/rBEhVFKds5gIAAAAABQMQAITD7QAAGTdAILdTsAFAxY57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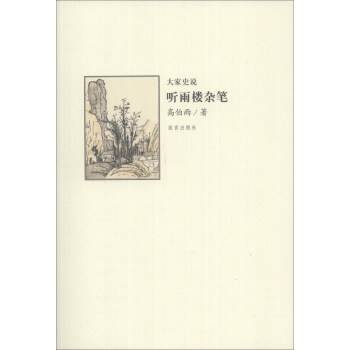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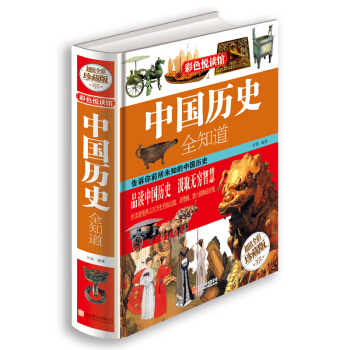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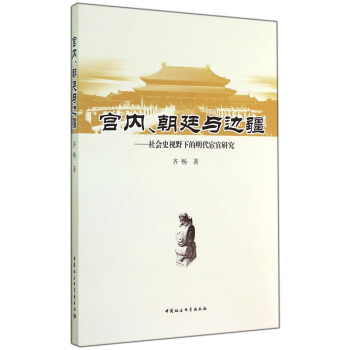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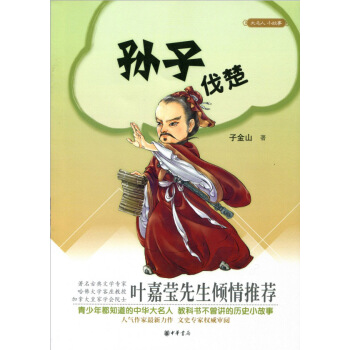
![第三帝国:非洲军团(修订本) [The Third Reich: Afrikakorp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49818/54d48a8cN01e9180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