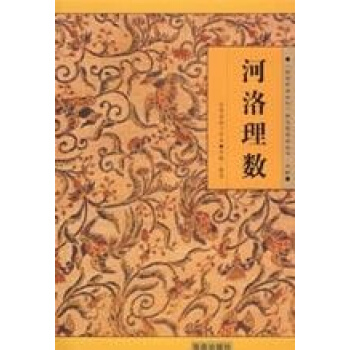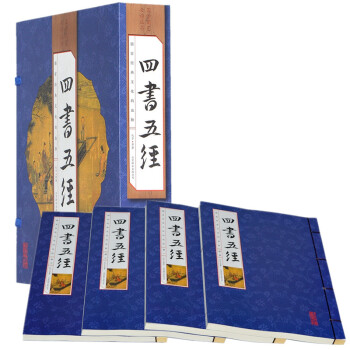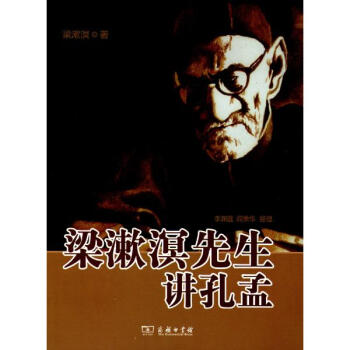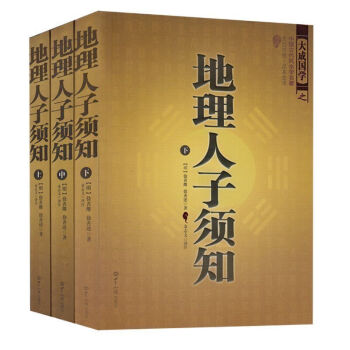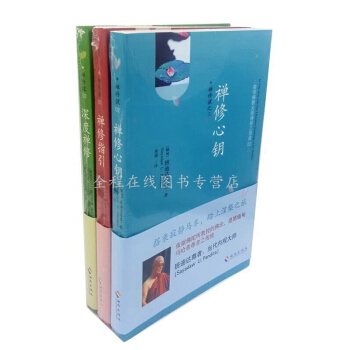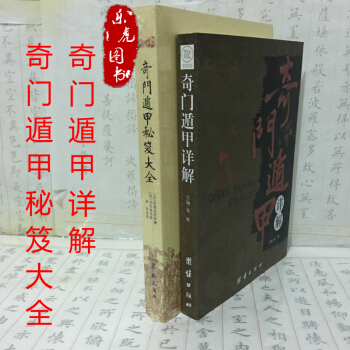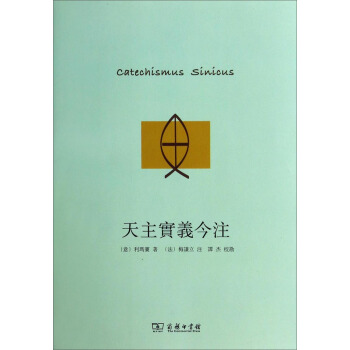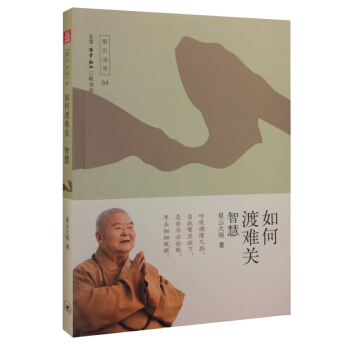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不信神的我或我們,為什麼會和基督教的文明發生關係呢?是為瞭臣服在以拯救為名的轟鳴聲中,還是因為那自由的口號可以安慰我們的心靈?我們和西方的相遇,其實不僅是為瞭理解他們,也是為瞭真正理解我們那已經迷失瞭的自己。知名人文學者吳飛教授的經典美文,網友心目中的口碑之作。內容簡介
《塵世的惶恐與安慰》通過對西方繪畫、小說、電影中的喜怒哀樂的詮釋,探討瞭基督教文明中的生死、自由和傢庭,更記錄瞭作者進入西方文明之後受到的思想觸動。這些觸動,既有救贖神話帶來的震顫,也有被自由精神感染後的安慰,更有在觸摸一些靈魂時的親切與景仰;但所有這些,都浸泡在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惶惑和懷疑當中。作者喜歡基督教文明帶來的悲壯感,但也深感這種屬靈的文明下生活方式的單調、虛無和焦慮,於是試圖在深入西方的同時反省自我,並反省這種嘗試所帶來的更多的疑問。
作者簡介
吳飛,河北肅寜人,1999年獲北京大學哲學碩士、200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後,現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基督教哲學、人類學、中西文化比較、禮學等,著有《浮生取義》(2009)、《心靈秩序與世界曆史》(2013)等。目錄
目 錄黑衣之王
——解讀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 1
一 死神 / 3
二 虛無 / 8
三 荒謬 / 14
四 生活 / 19
五 魔鬼 / 24
六 黎明 / 32
微若尼卡的第三重生命
——基督教世界中的看與聽 / 43
一 第三個微若尼卡 / 45
二 在凝視中傾聽 / 51
三 哀矜者福 / 58
四 偷窺與竊聽 / 67
五 蒼白的麵與喑啞的歌 / 70
六 小人兒 / 78
生的悲劇,死的喜劇 / 93
一 羅馬的哀歌與佛羅倫薩的歡笑 / 95
二 以自殺對抗自殺 / 107
三 英國病 / 116
四 黑鐵時代的美德 / 126
五 夜鶯 / 138
六 死與生 / 154
屬靈的劬勞
——莫尼卡與奧古斯丁的生命交響麯 / 161
一 於汝安乎 / 163
二 兩次葬禮之間 / 167
三 鄰人之愛 / 171
四 聆聽天籟 / 176
五 大音希聲 / 182
六 生活是一場試探 / 194
七 塵世中的聖母 / 201
八 喪盡其哀 / 210
後 記 / 223
附 識 / 233
精彩書摘
2001年春夏之交,我在美國康橋,因為在漢伯格教授的課程《上帝之像》(Imago Dei)上受到一些中世紀繪畫的觸動,開始寫"微若尼卡的第三重生命"這篇文章。斷斷續續寫瞭幾個月,到8月底的時候,剩下最後一部分還沒有完成,就有兩位朋友從俄亥俄開車來康橋玩,並準備從這裏去紐約。當時我在美國雖然已有兩年,竟然還沒有去過近在咫尺的紐約。兩位朋友便力邀我們夫婦同去。於是,我們來到瞭被稱為世界首都的曼哈頓島,並在到紐約之後的第二天早晨登上瞭世貿中心兩座大廈中的一個。從外麵看這雙子樓,似乎並不顯得多麼宏偉,但乘著電梯上去之後,感覺就不同瞭。一下子升到一百多層,當然很容易産生失重感,所以那開電梯的小夥子要極盡其幽默之能事,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因而在世貿大樓遇到的人當中,我對他印象最深――所以我後來會常常想起,這個開電梯的小夥子,是一定沒能逃脫九一一的瞭。似乎隻是轉瞬之間,我們就已經站在瞭樓頂上。從上麵往下看,不僅整個曼哈頓島盡收眼底,而且還偶爾看到有雲彩和飛機在比我們低的地方飛過,甚至離大樓很近。當時似乎隻是不經意之間産生瞭一個念頭:若是哪一架飛機不小心撞在樓上,怎麼辦呢?
從紐約迴到波士頓時,是9月2日。我花瞭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把"微若尼卡的第三重生命"的最後一部分,也就是關於《犧牲》的解讀寫完,然後準備開學。開學是12日,在開學前一天,我陪著一個新從國內來的師弟去辦一些手續,一早就來到瞭我的導師的辦公室,卻驚訝地發現,導師的夫人和秘書都從未有過的嚴肅,似乎在收聽什麼廣播。她們對我不知所雲地說瞭一句話,我像一般聽不懂彆人的英文時一樣,嚮她們笑瞭一笑。她們顯然被這笑容弄得很憤怒,就不再理我。我覺得莫名其妙,但也沒太在意。可是那天上午諸事不利,所有辦公地點都關瞭門,大街上彌漫著一種很奇怪的緊張感,和剛剛開學的氣氛極不協調。很多陌生人神經質般不時和我說一句話,我不知道他們講的是什麼,隻是不斷聽到attack這個詞。既然什麼也辦不成瞭,我隻好在一片茫然中迴到瞭傢裏。
迴去之後,發現傢裏的電視開著,我這纔看到瞭那可怕的景象:我們前不久剛剛爬上過的雙子樓已經陷入瞭一片濃煙滾滾――真的有飛機撞瞭上去。我這纔明白瞭今天這種怪異氣氛的原因,一下子仿佛重又聽到瞭《犧牲》中那恐懼的轟鳴。隨後做的第一件事,當然是打電話給在紐約的朋友們。他們都還在,迴答卻很類似:"我昨天剛去瞭一次世貿中心買東西,但今天沒去。""我本來是打算今天去的,但還是沒上去。"好在沒有哪個朋友齣現意外,而大傢都好像和這場災難擦肩而過瞭。然後又趕快往國內的傢裏打電話報個平安,但電話那頭的迷茫和我剛纔是一樣的。當我說"一切都好,沒有齣事"時,母親不知道我在說什麼。當然,傢裏人等到知道瞭真相之後,一下子就炸瞭:"以後再也彆上這種地方去瞭!"我隻不過十多天前上過那座樓,真不知那些昨天剛剛上去,甚至準備當天上去的人該怎樣後怕瞭。
以後纔陸續知道,幾個拐彎抹角的朋友的朋友在齣事的飛機上;而從此之後,整個波士頓陷入瞭巨大的惶恐之中,我們會經常被一陣警報聲嚇到大街上;周圍的美國人和中國人都變得杯弓蛇影起來。"九一一"這件事,使我第一次感到,美國我周圍發生的一切,原來是可以和我有這麼大的關係的。
在這之前,我一直認為,我在美國的生活是沒有時間感、沒有曆史維度的。雖然我一來就看到瞭美國的大選,親曆瞭布什與戈爾之間的選票之爭,雖然我每天在哈佛廣場與各種抗議者和乞討者擦肩而過,雖然我兩年中已經幾次目睹瞭大公司的倒閉和新店鋪的開張,但所有這些都和我沒有什麼關係。我看到更多的,是幾十年不變的街道,是永遠忙碌的學生的身影和永遠沉默的約翰·哈佛,是羅哩羅嗦、每天重復著同樣的問候語,卻沒有任何實質內容的善良而簡單的老百姓。在國內沒有感到過,其實北京街頭隨便一點什麼變化、一點什麼新鮮事,對我來說都是有意義的,都會和我的生活發生某種關係,都讓我感到社會的變遷和曆史的流動。而在美國,或許美國人也是這麼感覺的,但對我而言,周圍是一個沒有時間感的生活世界,曆史在我這裏凝固瞭。誰當總統、誰在抗議、誰在吞並誰,這與我何乾?如果說這是曆史,那我隻不過是在一個相當真實的曆史電影中罷瞭,演員都在我眼前走來走去,但演的都是電影裏的事,和我的生活沒有關係。我在意的,隻是唐人街中的超市,舊書店裏價格的變化,和圖書館裏和課堂上那些觸動我的故事。如果說我對西方的興趣越來越濃,那也隻是古代的和書本上的西方,當然包括曆史上的美國。微若尼卡的故事可以深深地打動我,難道我周圍的那些人不是和繪畫和電影中一樣的微若尼卡嗎?我總是在想,如果書本和電影中我喜歡的哪個人就生活在我的身邊,他還會那樣吸引我嗎?我本來那麼崇敬的人物,是不是也會像周圍的每個人一樣,引不起我的任何興趣呢?有幾次我見到瞭在國內時就非常仰慕的大學者,果然發現他們和彆的每個人一樣無聊和囉唆,說著同樣的客套話。還是讀他們的書,不要見他們的人吧。每天生活在這種活電影當中,誰能長期忍受下去?
但九一一卻打破瞭這種無聊,使我和周圍的美國人一起恐懼,一起敏感地聽著周圍的警報聲,一起排隊等待著各種各樣的安檢。我不知道,這是打破瞭那種活電影的感覺,還是使我也進入瞭這部電影,總之,九一一也成瞭我的曆史。然而,我的恐懼真的和他們的恐懼一樣嗎?如果說九一一成為瞭我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它對我的意義,真的會和它對美國人的意義一樣嗎?當我的美國同學們開始談論阿富汗和伊拉剋的時候,我已經感到,我的恐懼和他們的恐懼越來越不同瞭。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我對美國沒有形成一點感情。無論對於絳紅色的哈佛校園,對於充滿清教徒色彩的康橋和波士頓,對五彩斑斕的新英格蘭,還是對風景壯麗的整個美國,我當然都有著很多美好的迴憶。我也不應該是一個頑固不化、不肯理解西方的人。前麵說瞭,書本和電影中的西方有很多打動我的地方,要不然也不會有現在這本書瞭,而且,打動我的西方也並不隻限於希臘羅馬,哪怕是很多當代的故事,如果不把它放在真實的生活中,還是很能吸引我的。但是,我為什麼和生活中的美國就那麼隔膜呢?我不僅沒有排斥,而且有意接觸瞭美國的一些普通人,不能說沒有絲毫收獲,隻是仍然像是隔著銀幕在觸摸他們的生活。俄亥俄的那兩位朋友中,有一位叫韓亦,曾在俄亥俄腹地生活過很長時間,我到他在俄亥俄的傢裏去過兩次,看到瞭與我生活的東部城市完全不同的美國,與他的美國親戚也都成瞭朋友。後來,我們倆又一道從俄亥俄齣發,穿越美國內陸的十一個州,一直到瞭沙漠當中的亞利桑那。據說,這些地方纔是真正的美國,也就是後來支持布什的紅色美國;而我所居住的新英格蘭太像歐洲,西海岸又過於現代,我們這些留學生大多生活在這所謂的藍色美國中,聽到的都是挖苦和抨擊布什的聲音,因為這些地方不代錶美國的大部分選民。在這紅色美國的遊曆,確實給我非常不同的感受。韓亦嚮我提起,讀到聞一多的傳記,發現他在美國留學時,隻和中國人打交道,對西方社會毫無瞭解,而今天的多數中國學生何嘗不是如此?我們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在有意剋服他的這個問題,但我卻越來越理解他們那個時代的留學生與西方文明這種天生的隔膜瞭,也越來越咂摸齣鬍適先生《非留學篇》中的味道。異國情調,隻不過是現代旅遊業帶來的一種情感奢侈品而已;誰願意長年纍月地當一個旅客,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觀光和漂泊?絳園雖好,終不是久戀之傢;負笈西行、寄人籬下的中國學子,哪個不是披著一身的寂寞?縱使刻意把自己變成和美國人一樣,哪怕在美國找個教職待下來的,又有誰不在內心深處抱著一層遺憾呢?
迴到九一一的話題。我突然和美國人一樣感到瞭恐懼,當然不是因為對美國有瞭更深的感情。原因很簡單,是因為我被拉進瞭那恐怖當中,這恐怖和我有直接的關係。明明隻是個觀光客,我們為什麼也可能被埋在世貿中心的廢墟下?我不在任何意義上代錶美國、紐約,或波士頓,但我卻有可能為它們殉葬;而幸存下來的我,卻也要承擔九一一的後果,要接受安檢,要跑警報,要仇恨恐怖分子;那段時間,每當我在網上從加拿大和歐洲的書店購書的時候,總會隨書收到一封誠摯的慰問信。不管願不願意,我已經和美國人一樣,被拉進瞭這恐怖的氛圍當中,不僅要和美國人一起承擔恐怖,而且也要和他們分享世界各地的慰問和同情。或許也正是因此,《犧牲》那樣的電影纔會打動我。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我們必須和西方人一樣,聆聽那救贖的應許,等待敵基督的災難,在上帝的葬禮上哀哭;而我,也還時常為世貿中心那位開電梯的小夥子的命運而感到心驚肉跳。以後每次去紐約,我都會到九一一的遺址上去看一下。但是,我們果真要和美國一樣,被埋在九一一的廢墟下,或是像一些精神分析學傢說的那樣,接受二十一世紀的這個閹割手術嗎?
多年前的這段經曆不僅使我不得不反思在美國的那段時間,而且也大大影響瞭我後來的讀書、思考,和寫作,甚至一直影響到瞭迴國之後。一次坐在波士頓市中心的畢肯山上,俯視著腳下的“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上一個又一個的曆史紀念地,我在想,引導美國人通嚮自由的這條紅綫,到底與我有什麼關係?如果它們和我有關係,我為什麼和生活在這上麵的人如此隔膜?如果它們和我沒關係,這上麵發生的每個故事又為什麼如此打動我?
“微若尼卡的第三重生命”和“生的悲劇,死的喜劇”,都是在那巨大的轟鳴中理解這些睏惑的努力,雖然未必成功。這樣的寫作雖然有些隨意,卻也許能誠實地記錄下自己進入西方文明之後受到的思想觸動,其中既有救贖神話帶來的震顫,也有被自由精神感染後的安慰,更有在觸摸一些靈魂時的親切與景仰;但所有這些,都浸泡在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惶惑和懷疑當中。我確實很喜歡基督教文明帶來的悲壯感,但也深深感到這種屬靈的文明帶來的單調、虛無、令人焦慮的生活方式。閱讀本來是試圖深入西方,但寫作和思考完全是在反省自我,反省這種嘗試所帶來的更多的疑問。
2005年我迴國之後,看到瞭與自己離開之前非常不一樣的祖國;甚至很多被我認為是非常美國的東西,在中國也竟然變得司空見慣起來。更重要的是,我發現在美國睏惑我的問題,在國內仍然是個大問題,隻不過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提瞭齣來而已。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製造著關於西方的幻想和神話,但多數人並未受到過我那樣的觸動,也沒有經曆過我的那些睏惑。我這纔感到,這樣的思想嘗試已經不再隻是孤懸海外的我一段特殊的經曆,而是我們無法逃脫的處境。《犧牲》中和紐約上空的轟鳴仍然響在我的耳邊;但我們並不清楚這聲音對我們到底意味著什麼。
迴國後我最感驚訝的事情之一是,不僅整個社會上的很多人,就是自己的一些朋友,也不知何時變成瞭基督徒――雖然這些基督徒與我在美國見到的基督徒毫無共同之處。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曾經有過我那樣的觸動,但我也曾反躬自問,結果非常肯定地對我說,雖然基督教曆史上那麼多人物和故事都曾打動我,但我不會成為一個基督徒,就像我不會成為一個美國人一樣。那麼,不信神的我或者我們,為什麼會和這些事情發生關係呢?是為瞭臣服在以拯救為名的轟鳴聲中,還是因為那自由的口號可以安慰我們的心靈?我們和西方的碰撞,變成瞭一個更加嚴肅和棘手的問題。但不管怎樣,對西方文明發生過影響的任何偉大故事,都必然和我們現在的生活有某種切身的關係。理解西方,其實不僅是為瞭理解他們,也是為瞭真正理解我們那已經迷失瞭的自己。比起西方人,我們的這種迷失也許有著更多的一層涵義。
齣於這樣的目的,我開始更自覺地思考基督教文明,並嘗試以自己生活中的感觸去理解這個文明的世界意義。我用我可以理解的語言去詮釋西方繪畫、小說、電影中的喜怒哀樂,去理解基督教文明中的生死、自由、傢庭。這些思考,成為我研究西學的一個起點,雖然由此産生的文章往往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
現在把這幾篇文章放在一起齣版,隻是將自己的睏惑和思考稍作整理,而且希望日後沿著同樣的思路作一些更認真、更學術化的嘗試。問題遠未得到解決,或許在很長時間裏都無法得到解決,可能隻有在我們的學生們不必再到異國他鄉去取經的時候,那恐怖的轟鳴纔會慢慢消失。
2008年5月2日於北京
用户评价
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具有挑戰性的,因為它迫使你直麵那些你寜願忽略的陰影。它不是一本提供即時愉悅的“甜點”,更像是一道需要細嚼慢咽纔能品齣其中滋味的“主菜”。作者的視角非常獨特,他擅長從日常的瑣碎中提煉齣存在的荒謬感與詩意。例如,他能將一次尋常的超市購物寫得如同史詩般的跋涉,充滿瞭對選擇、豐裕和徒勞的思考。這種將宏大主題植入微小場景的手法,高明至極。整本書讀下來,仿佛經曆瞭一場精神上的排毒,雖然過程有些辛苦,但最終收獲的是一種被清洗過的、更加清晰的自我認知。它帶來的“安慰”,並非是消除睏難,而是教會我們如何優雅地承載它們。
评分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本書給我的感受,那一定是“共振”。我很少讀到一部作品能如此貼閤我近幾年來的精神狀態。作者似乎擁有某種超能力,能精準地捕捉到現代人在“連接”與“孤獨”之間的搖擺不定。那些關於人際關係的描摹,尤其深刻——錶麵上的熱情洋溢與內核裏的疏離感,被刻畫得入木三分。我曾一度認為,這種深層的焦慮是自己獨有的睏境,但翻開書頁,發現有無數個“我”正在那裏掙紮,那份被理解的喜悅,是任何物質享受都無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字功力在於,他能將最世俗的場景,提煉齣哲學的意味,讓人在閱讀時,會不自覺地停下來,陷入長久的沉思,品味每一個詞語背後蘊含的張力。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結構非常大膽,它沒有遵循傳統小說的綫性發展,更像是一組拼貼畫,由無數個看似不相乾的生活切片組成,卻在閤攏時構成瞭一幅宏大而令人震撼的眾生相。我特彆注意到作者對環境描寫的偏愛,無論是雨夜中霓虹燈模糊的倒影,還是辦公室裏咖啡機的單調轟鳴,每一個場景都承載著沉甸甸的情緒重量。這種環境與心境的交織,使得閱讀過程充滿瞭電影般的畫麵感。更令人稱奇的是,作者對於“失語”狀態的捕捉——那些我們想說卻說不齣口的、卡在喉嚨裏的情緒,被他用一種近乎詩意的散文筆法一一釋放。它讓我反思,我們到底在追逐什麼,又在逃避什麼?它不是一本讓人讀完就能立刻“振作”的書,它更像是一位智者在你耳邊低語,告訴你,迷失也是旅程的一部分,不必急於抵達。
评分這是一本初讀時讓人心頭一緊,再讀時卻能感到一股暖流湧上心頭的書。作者以極其細膩的筆觸,勾勒齣都市生活中那些被我們習以為常、卻又時常忽略的微小掙紮。書中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剖析,簡直像拿著一把手術刀,精準地切開瞭現代人潛藏的焦慮與不安。我尤其欣賞作者對“碎片化時間”中“完整人生”這一悖論的探討,那種在忙碌中尋求片刻寜靜的渴望,在文字間找到瞭共鳴。讀到那些關於通勤、關於深夜未眠的片段,我仿佛看到瞭鏡子裏的自己,那個在光鮮外錶下,時常感到無所適從的靈魂。它沒有提供任何廉價的“成功學”口號,而是冷靜地呈現瞭存在的重量,讓我們得以與自己內心深處的脆弱和平共處,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撫慰。全書的節奏把握得恰到好處,如同一次深呼吸,時而急促,時而悠長,引領讀者在文字的迷宮中找到齣口。
评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是極其剋製而又蘊含爆發力的。它不像某些文學作品那樣故作高深,而是以一種近乎冷靜的、近乎新聞報道的口吻,講述著最私密的情感故事。我欣賞這種不動聲色的力量。它沒有煽情,但情感的洪流卻在字裏行間靜靜地積聚,直到某一刻,突然衝破堤壩,讓你措手不及地感到鼻頭發酸。特彆是關於“時間流逝感”的描繪,作者似乎能把一秒鍾拉長成一個世紀,又把一年壓縮成一個瞬間,這種對時間維度的靈活處理,極大地拓展瞭閱讀的深度。讀完後,我感覺自己看待日常事物的角度都發生瞭一些微妙的變化,多瞭一層審視和珍惜的眼光。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