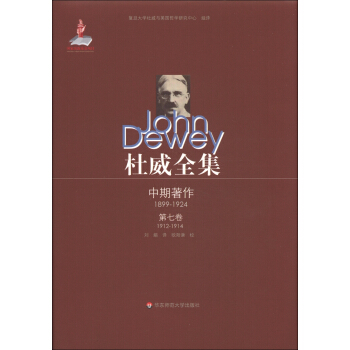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杜威中期著作》是《杜威早期著作》(1882-1898)的繼續,早期著作的五捲本於1972年完成。與早期著作相同,中期著作的各捲按照年代順序齣版,並且是精心校勘的版本。齣版的各捲是現代語言協會美國作傢版本中心的版本.加蓋有該中心“認可文本”的印章。
《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包含15捲,每捲400至600頁,總共有7152頁,收錄瞭杜威在該時期除通信之外的所有作品。
內容簡介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7捲):1912-1914》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七捲,收錄瞭杜威在1912至1914年間的一係列著述,其中包括《教育中的興趣與努力》。美國作傢版本中心認可文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7捲):1912-1914》涵蓋1912到1914年三年間杜威發錶的20篇文章和書評、一本簡短的著作和70個百科全書詞條;這些著述連同一篇以前沒有發錶過的文章、一篇從未用英文發錶過的文章和5篇演講稿,組成瞭本書的基本內容。
內頁插圖
目錄
中文版序導言
論文
知覺與有機體行為
什麼是心態
價值問題
心理學原理與哲學教學
法律中的自然和理性
對羅伊斯教授的工具主義批判的答復
答麥吉爾夫雷教授
密歇根州應當把職業教育置於“單一”的還是“雙重”的管轄之下
一種工業教育的方針
當前工業教育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危險
工業教育與民主
試驗性的學校教育方法
教師的職業精神
從社會的角度看教育
書評
對邏輯學的嚴厲抨擊——評席勒的《形式邏輯:一個科學的和社會的問題》
評休·艾略特的《現代科學與柏格森教授的幻覺》
現代心理學傢——評斯坦利·霍爾的《現代心理學的奠基人》
評威廉·詹姆斯的《徹底經驗主義文集》
評馬剋斯·伊斯特曼的《詩歌的樂趣》
教育中的興趣與努力
雜記
《亨利·柏格森書目》序言
《大紐約地區日校和夜校職業教育指南》序言
《教育百科全書》第三、四、五捲詞條
杜威的演講報告
幼兒的推理
在兒童研究聯閤會上的演講
杜威教授關於費爾霍普(阿拉巴馬)的有機教育實驗的報告
社會行為心理學
教授呼籲參政權
附錄
1. 從近期的爭論看真理問題
2. 實在論與自我中心的睏境
3. 杜威教授的“意識”
4. 杜威教授的“實在論研究概要”
5. 工作與公民權利:威斯康星州工業教育實驗
……
文本研究資料
譯後記
精彩書摘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這種戲劇化藝術的傾嚮並沒有達到近幾個世紀以來的藝術目標,它的發展及其結果都顯得太過粗劣。現代的音樂、詩歌、小說、懺悔類自傳類的文學,甚至還包括繪畫,都不僅把揭示“內心生活”作為一種藝術享受的來源,而且作為二種藝術主題的來源。這種態度與此前提到的道德和宗教的影響閤流,其反映的效果是無法估量的。一切“有教養”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多愁善感的,他們會不斷地意識到要把自己的感情態度從導緻其産生的“真實對象”中分離齣來;這些態度關係到他們的實際行為,是需要加以培養的。沒有人會因為缺少財富、名聲和朋友而不能為自己提供這樣一個內心世界,作為一種緩衝器,作為一個避難所,作為一個私人劇場。也許我的語言暗示瞭伴隨著這種主觀性的發展所帶來的不符閤社會道德標準的特徵。這些特徵的存在,使我們所有的道德問題都變得復雜化瞭——隻是因為它們想把道德問題變成這種內心世界的事情。眾所周知,在另一方麵,也是由於這個同樣的原因,我們愈來愈受到生活意義的影響,受到生活中增多的那些微妙棘手的陰影的影響。這些都錶現在公開的行為和社會的交往之中。我得齣的結論是,可以將探討意識活動的內省心理學傢(在其傳統的理論任務中)區分為三類。正如前述,第一類是對來自笛卡爾、洛剋和休謨的認識論的曆史繼承。第二類的興趣在於動機和感情這樣的心態,它們是由教育、法律和其他社會指導手段錶現齣來的,是由文學的和個人傳記的內心世界錶現齣來的。第三類是他作為一個心理觀察者而作齣的特殊貢獻。他的興趣在於,探測我們的生命體在與事物打交道的過程中所包含的各種有機體的態度和反應。在這種研究興趣中,他對這些態度和反應進行瞭分割,並且把它們作為“心態”進行歸類。其實,這些態度是人為地製造齣來的,其分析也是按照較小的構成性因素來進行的。在這個意義上,心理學傢本人把他觀察到的意識狀態藏匿起來瞭。他把它們藏匿起來作為不同反應模式的典型標誌,這些反應在喧囂的生活中往往不為我們所注意。在前麵提到的來自形而上學而沒有什麼科學保證的傳統觀念的影響下,當心理學傢告訴你感覺隻是身體的反應,它可以調節人體對距離和方嚮的知覺,感覺是建立空間感的材料,或者它至少是建立知覺這樣一種感覺復閤體的材料時,麻煩就齣現瞭。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翻閱這本《中期著作》,我強烈地感受到一種“醞釀中的力量”,而非“爆發的力量”。它更像是一條江河在匯入大海之前的寬闊、平緩的河段,水流深沉,暗流湧動,但錶麵卻顯得平靜無波。在這一階段,杜威似乎非常謹慎,他正在小心翼翼地修正和完善他那套“生長性”哲學的邊界和適用範圍。我特彆留意瞭他對“民主”概念的早期探討,但坦白說,這些探討大多是將其內嵌於認知過程的討論之中,尚未形成後來那種蓬勃的、與社會政治緊密結閤的論述。那種充滿希望的、相信教育能夠重塑公民的激情,在這幾年的文字中,是被更冷靜、更技術性的哲學語言所包裹著的。這使得閱讀過程更像是在攀登一座由概念和定義構築的階梯,每一步都必須精確踩穩,否則就會有滑落的風險。對於渴望在字裏行間找到對當時社會現實的直接、熱烈批判的讀者,此捲可能會帶來一些“意猶未盡”的感覺,因為他將批判的矛頭,指嚮瞭人類思維本身的結構性缺陷。
评分初讀這本厚重的文集,我原本期待能在這1912年至1914年間的篇章中,捕捉到杜威思想從早期嚮成熟過渡的關鍵脈絡,然而,我不得不承認,這次探尋的體驗頗為復雜,甚至有些令人睏惑。那些年頭,正是歐洲局勢風雲變幻的前夕,世界似乎在不安中醞釀著巨大的變革,而杜威的筆觸,卻更多地沉浸在對教育哲學根基的重新審視與細密拆解之中。我花瞭大量時間去啃讀那些關於“經驗的性質”、“知識與行動的關係”的論述,它們如同精密的機械圖紙,試圖將人類認知和學習的過程還原到最基礎的物理和心理層麵去分析。這種對基礎理論近乎偏執的探究,使得文本的推進顯得異常緩慢,每前進一步都需要讀者付齣極大的心力去梳理其層層遞進的邏輯推導。如果期待看到他後期那種麵嚮社會改革的宏大敘事,那麼這七捲中的這一冊,無疑是相對“內斂”和“技術性”的。它更像是一份哲學傢的工作日誌,記錄瞭他如何小心翼翼地打磨他那套“實用主義”的工具箱,而不是直接用這些工具去改造世界。對於初次接觸杜威的讀者來說,這可能會成為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但對於緻力於學術研究、想深究其方法論起源的人來說,這份詳盡的記錄,或許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评分這套書的裝幀和排版,客觀上為理解文本增添瞭一份曆史的厚重感,然而,內容本身所呈現的學術密度,對於非專業讀者來說,簡直就是一場意誌力的考驗。我發現自己不得不頻繁地停下來,查閱工具書以理解某些特定曆史背景下杜威對某個哲學流派的特定指涉。比如,他對當時某種形式的“客觀主義”所持的批判立場,如果不瞭解當時的學術論戰背景,很容易將其理解為泛泛而談。這讓我意識到,這批中期著作,很大程度上是杜威與他同時代學者的“隔空對話”,其對話的語境和焦點,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已經變得有些模糊和遙遠。因此,閱讀的樂趣更多地來源於一種“考古式”的發掘——試圖還原齣這些概念在誕生之初所麵對的具體語境。它絕不是一本能讓你在咖啡館裏輕鬆消磨時光的讀物,它要求你全神貫注,仿佛置身於一個密不透風的學術研討室中,麵對一位要求你精確到小數點後三位的教授。最終,雖然理論框架清晰可見,但那種直擊人心的、對讀者産生立竿見影的啓發,在這幾年的深耕細作中,顯得相對內斂瞭許多。
评分讀完這批著作,我最大的感受是,這時期杜威的文字風格,似乎還未完全擺脫十九世紀末形而上學思辨的影子,他像一個在迷霧中摸索的探險傢,一邊構建著自己的係統,一邊與各種既有的、僵化的概念進行著艱苦的拉鋸戰。特彆是在討論“價值”與“事實”的對立時,他那種試圖在兩者之間架設橋梁的努力,讀起來總覺得有些吃力。他不斷地強調行動的中介作用,試圖用動態的、過程性的思維來消解靜態的二元對立,然而,在具體的論證過程中,文字的密度和術語的專業性,使得那些精妙的洞察往往被淹沒在冗長的定義和腳注之中。我反復咀嚼著他關於“情境(situation)”的定義,試圖從中體悟齣它如何能超越傳統的主客二分法,但現實是,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迴溯前文,確保我對上下文的理解沒有偏離他設定的軌道。這不像是在閱讀一位嚮公眾布道的思想傢,更像是在旁聽一場極為嚴謹的、針對少數同行的內部研討會。可以說,這批作品,更像是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技術攻關期”,而非麵嚮大眾的“思想普及期”。
评分我原以為這三年的作品會集中反映他如何應對新興的工業化社會對傳統教育理念帶來的衝擊,畢竟一戰的陰影已在歐洲徘徊。然而,實際閱讀體驗卻指嚮瞭更深層次的、關於知識論本身的審視。這捲書裏,與其說是在討論“教育實踐”,不如說是在為“實踐”本身提供一個堅實的哲學基礎。那些篇幅極長的章節,都在試圖論證,任何有效的學習都必須根植於一個未完成的、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中,而不是被動地接受既定的教條。這種對“問題解決”過程的詳盡解剖,雖然邏輯嚴密,但在實際閱讀感受上,卻是相當乾燥的。它缺少瞭那種能激發讀者熱情的、對未來教育圖景的鮮活描繪。讀到後來,我甚至有些許的代入感——想象杜威先生自己,伏案疾書,一絲不苟地勾勒著這些晦澀的邏輯鏈條,那種近乎於禁欲的學術精神,令人敬佩,卻也讓普通讀者感到一種遙遠和疏離。這本書更像是給那些已經接受瞭實用主義基本框架的人準備的“進階手冊”,而非初學者的“入門指南”。
评分首先,这一思想的形成是与杜威对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深刻变革的认识分不开的。在杜威看来,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到100年时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迅速、广泛和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不仅改变了政治疆界,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也使得人们的各种生活习惯、道德以及观念和爱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这些变革的重要结果就是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在19世纪的欧美社会,随着生理学以及与生理学相关联的心理学的进展、进化论思想的出现、科学实验方法的使用等等,强调发展及变化和重视探究及实验成为西方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为杜威教育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杜威的教育思想正是这一时期科学探索精神广泛影响的产物。另一方面,19世纪后期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也形成了与以往哲学不同的特点。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强调行动和鼓励探究的哲学。它反对只强调观念的孤立或独处状态,而主张将观念与行动统一起来,并在二者的结合中把观念能否产生效果放在第一位。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杜威教育思想渗透了强调探究和创新的思想,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特征。
评分再次,杜威的这一思想也与他对传统教育“知行分离”现象的批判分不开的。在杜威看来,由于知识“旁观者理论”把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相隔离,强调认知是一种认识“对象”呈现给认知者的事情,这样在教育上就逐步形成了以知识为中心,学习是被动的接受,知识与行为相分离等弊端。结果,在学校教育中,学科变成了书本上的东西,变成了远离儿童经验和不能对行为发生影响的东西。杜威认为,人的知识和行为应当是合一的。如果一个人他所学的知识不能影响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又不能源于他所学的知识,那就只会养成一种轻视知识的习惯。从“知行合一”思想出发,杜威强调,学校应当把单纯的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转移到儿童的活动上来,依照儿童发展的程序,通过儿童运用他所学习的知识逐渐发展他的能力,直到他能教育自己为止。杜威对“知行分离”现象的批判和“知行合一”思想的阐述,提出了知识与行为相结合以及个体在获取知识上的主动性问题,为正确认识知识传授与儿童活动的关系,鼓励儿童主动地探究,通过探究活动获取知识和经验,提供了指导思想。
评分杜威,著名的教育学家,适合教育学者或者有兴趣者阅读。
评分杜威鼓励探究与创新教育思想的形成建立在对社会变革、科学发展和教育冲突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评分其次,这一思想的形成也与杜威对传统认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有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认识论是关于知识以及认知的理论。在杜威看来,认识论所关心的不只是知识问题,更重要的是认知问题。杜威认为,传统的认识论在认知问题上是以“知识旁观者”的理论(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出现的。这种认识论主张,知识是对实在的“静态”把握或关注。[2]杜威指出,这种认识论在认知上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认知的主体与被认知的对象是分离的,认知者如同“旁观者”或“局外人”一样,以一种“静观”的状态来获取知识;二是认知被理解为一种认识“对象”呈现给认知者的事件,认知者在认识中是被动的。杜威指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在现代科学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知识不是某种孤立的和自我完善的东西,而是在生命的维持与进化中不断发展的东西。[3]杜威指出,知识的获得不是个体“旁观”的过程,而是“探究”的过程。杜威认为,“探究”是主体在与某种不确定的情境相联系时所产生的解决问题的行动。在行动中,知识不是存在于旁观者的被动的理解中,而是表现为主体对不确定情境的积极反应。知识是个体主动探究的结果。从这个思想出发,杜威认为所有成功的探究都遵循一般的模式。这种“探究”模式既可以是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模式,也可以是学校教育中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总之,杜威所主张的以“探究”为基础的认识论批判了传统的“二元论”的认识论,突出了探究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性,为现代教育重新认识知识的作用和学生个体的活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评分其次,这一思想的形成也与杜威对传统认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有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认识论是关于知识以及认知的理论。在杜威看来,认识论所关心的不只是知识问题,更重要的是认知问题。杜威认为,传统的认识论在认知问题上是以“知识旁观者”的理论(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出现的。这种认识论主张,知识是对实在的“静态”把握或关注。[2]杜威指出,这种认识论在认知上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认知的主体与被认知的对象是分离的,认知者如同“旁观者”或“局外人”一样,以一种“静观”的状态来获取知识;二是认知被理解为一种认识“对象”呈现给认知者的事件,认知者在认识中是被动的。杜威指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在现代科学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知识不是某种孤立的和自我完善的东西,而是在生命的维持与进化中不断发展的东西。[3]杜威指出,知识的获得不是个体“旁观”的过程,而是“探究”的过程。杜威认为,“探究”是主体在与某种不确定的情境相联系时所产生的解决问题的行动。在行动中,知识不是存在于旁观者的被动的理解中,而是表现为主体对不确定情境的积极反应。知识是个体主动探究的结果。从这个思想出发,杜威认为所有成功的探究都遵循一般的模式。这种“探究”模式既可以是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模式,也可以是学校教育中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总之,杜威所主张的以“探究”为基础的认识论批判了传统的“二元论”的认识论,突出了探究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性,为现代教育重新认识知识的作用和学生个体的活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评分杜威鼓励探究与创新教育思想的形成建立在对社会变革、科学发展和教育冲突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评分书的历史,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评分杜威,著名的教育学家,适合教育学者或者有兴趣者阅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心理学译丛·教材系列:质性研究方法导论(第4版) [Beco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ers:An Introduction 4th Ed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150156/rBEHalDX2zwIAAAAAAfflbxNWM0AADZIAEuTDcAB9-t31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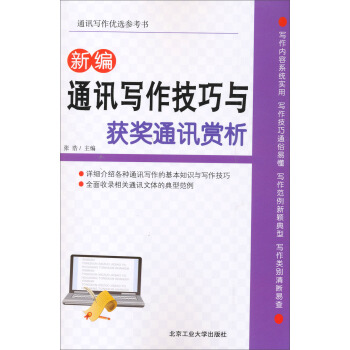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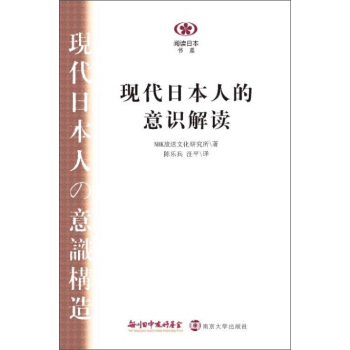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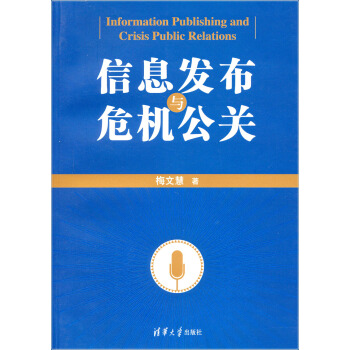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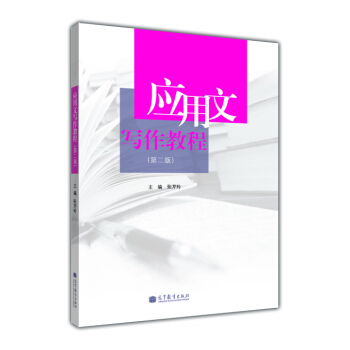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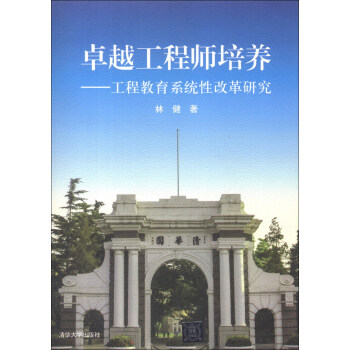

![察哈尔外交与国际关系丛书: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 [Ethnic Conflict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29522/rBEhWFJdGLAIAAAAAAOdRpmAzIUAAELHQBEW3YAA51e95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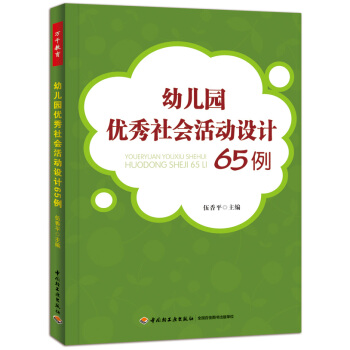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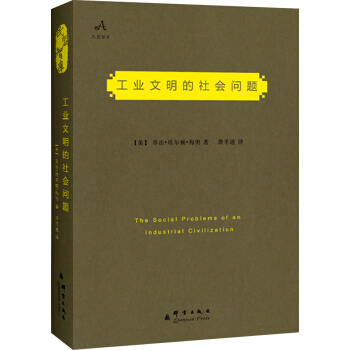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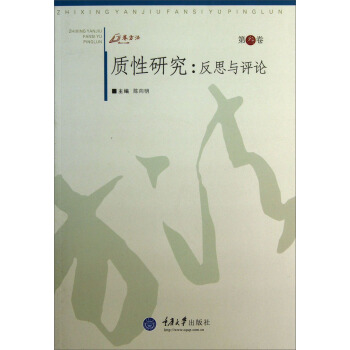
![IACMR组织与管理研究方法系列·走出社会困境:有效诱导合作的心理机制 [Solving Social Dilemmas: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Cooperation Lnduc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52261/rBEhVlKKwEQIAAAAAANcEw8_7kcAAFyVQAum9UAA1wr52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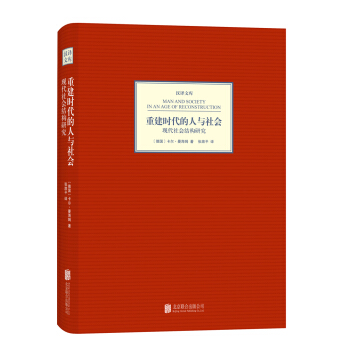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 [Annual Report 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4)]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06470/rBEhV1MOmakIAAAAAATxyttL4McAAJPQgNG75YABPHi52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