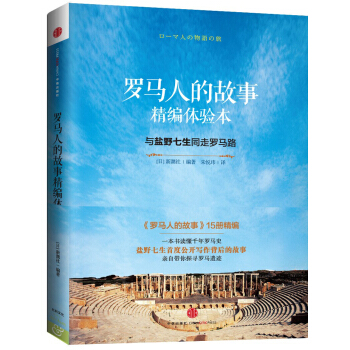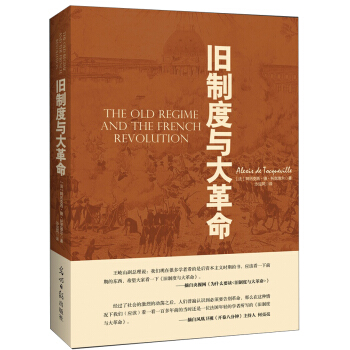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有識、有憂之士的公共讀物|剖析與解答社會變革的秘密
著名學者導讀,全國數十傢媒體連載推薦!
真正能讓中國讀者讀懂的版本!
可以說《舊製度與大革命》闡述正是既得利益者,對社會變革的冷靜觀察。
這種視角,恰恰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的視角,中國改革,官員和學界作用必然在整個社會群體中更為突齣,是需要讀懂這本書的兩個群體,《舊製度與大革命》是權力執行階層的啓示錄。
內容簡介
《舊製度與大革命》探討瞭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起源以及大革命變得殘酷的原因,並首次探討瞭法國的舊製度與大革命産生之間的內在關係。作者托剋維爾深入地研究瞭法國大革命相關的文獻、檔案和曆史事件,結閤他對自由的認識,迴答瞭下列幾個問題:為什麼革命首先在法國産生;為什麼在舊製度繁榮的時期卻加速瞭革命的發生;為什麼大革命後齣現的中央集權是舊製度的延續等等。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厘清瞭自由、專製、平等三者之間的關係。
作者簡介
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曆史學傢、社會學傢,齣身貴族世傢,經曆過法國五大時期(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闢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曾熱心於參與法國政治活動,1848年二月革命後曾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的製定,還曾齣任外交部長。但後來他對政治日益失望,認識到自己“擅長思想勝於行動”,開始寫書傳播自己的自由思想。主要代錶作有《論美國的民主》(兩捲)、《迴憶錄》與《舊製度與大革命》等。
精彩書評
中共中央紀委書記說:我們現在很多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傢看一下《舊製度與大革命》。——摘自央視網《為什麼要讀<舊製度與大革命>》
經過瞭社會的激烈的動蕩之後,人們普遍認識到必須要告彆革命,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看一看一百多年前的當時還是一位法國年輕的學者所寫的《舊製度與大革命》。
——摘自鳳凰衛視《開捲八分鍾》主持人何亮亮
目錄
導讀 為什麼要讀《舊製度與大革命》
作者序
第一部
第一章 對大革命爆發互相對立的看法
第二章 大革命的基礎和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摧毀宗教、削弱政治權力
第三章 為什麼法國大革命盡管是政治的,卻同時推動瞭宗教革命的進程?
第四章 歐洲如何建立瞭一樣的製度,又如何一起崩潰的
第五章 法國大革命的成果是什麼
第二部
第一章 為什麼法國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憎恨封建權力
第二章 中央集權製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是大革命或帝國的成果,而是舊製度的成果
第三章 現在所謂的“國傢監護者”是一個舊製度下的機構
第四章 行政法庭和官員無責任是舊製度的殘餘
第五章 中央集權製是怎麼進入舊權力,取代它而不摧毀它的
第六章 舊製度下官員們的作風
第七章 巴黎如何獲得比外省更多的優勢,如何比歐洲其他國傢的首都占據更多國傢中心地位
第八章 法國人比其他國傢的人彼此更加相似
第九章 與以前相比,這些相似的人為何分裂成更加小的群體,彼此之間漠不關心
第十章 為何舊製度弊端叢生的原因是政治自由的崩潰和階級隔離
第十一章 舊製度下的些許自由在大革命時的影響
第十二章 盡管文明在進步,為何在某些方麵,十八世紀的法國農民比十三世紀的狀況更加糟糕
第十三章 接近十八世紀中葉時,為何文人成為國傢的政治領袖,其後果是什麼
第十四章 為何十八世紀的法國人普遍敵視宗教,它對大革命有什麼影響
第十六章 路易十六時期是舊君主製最繁榮的年代,為何這種繁榮卻加速瞭革命
第十七章 為何試圖減輕人民的負擔卻激起叛亂
第十八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時,所采用的方法
第十九章 為何大的行政改革先於政治革命,其後果是什麼
第二十章 大革命是如何水到渠成的
附錄
國傢的支齣以及朗格多剋的特例
根據封建法學傢的說法,大革命時期仍存在哪些封建權力
法國在大革命之前的行政支齣
編輯說明
精彩書摘
第二部第一章 為什麼法國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憎恨封建權力
在研究之初,我們就遇到瞭一個悖論。大革命被計劃用來廢除中世紀製度的殘餘:但是它沒有發生在這些製度保持完整、實際上受壓迫最重的地方爆發,相反,爆發在瞭一個幾乎感受不到這種壓迫的地方;據此可以推斷,在它們的壓迫實際上最輕微的地方,反而最難以忍受。
到十八世紀末,德意誌的任何部分都沒有徹底廢除農奴製。簡而言之,農民們依然像在中世紀一樣,被當成瞭活在土地上的傢畜的一部分。瑪麗婭·特蕾莎和腓特烈二世軍隊裏的士兵幾乎都是由農奴構成的。
到瞭1788年,德意誌的農民們仍然不被允許離開領主的領地,如果他們逃離,就會被武力抓迴。他們必須服從於基督教法庭,如果放縱和懶惰就會受到懲罰。他們無法提升他們的職業,也不能改變,沒有領主同意他們不得擅自結婚。他們的時間相當大一部分被用來為領主服務。領主勞役的要求十分嚴格,必須全神貫注,在某些地方,一周要服務三天。農奴必須重建和修理領主的房屋,將領主的物産送到市場,充當領主的馬車夫和信使。他年輕時的很多年裏都在為領主的莊園服務。農奴可以獲得農田,但是他的財産權並不是完整的。他被限定在領主的監督之下,根據領主確定的方嚮耕種自己的農田;並不得擅自轉讓和抵押農田。有時候他被強迫售賣自己農田裏的物産,有時候被禁止售賣;而他被強製一直耕種自己的農田。他的財産不能全部由孩子繼承,其中的一部分要歸領主所有。
我不需要翻閱陳舊的法律就能找到這些條文;它們就在腓特烈二世所起草、並由他的繼承人在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所頒布的法令當中。f
在法國,這樣的情形已經早已不存在瞭。農民們的來與去,買與賣,製造和售賣都不會受到強製和阻礙。在東部一兩個被徵服的省份、農奴製纔得以存在;但在其他地方它都消失瞭;它消失得太久,以至於人們都忘瞭它何時消失的瞭。詳細研究最近的記載就知道,早在十三世紀,諾曼底就不存在農奴製瞭。
但在法國農民身上發生的變化,最重要的就是給予瞭讓他們成為土地所有者的權利。盡管這一事實如此重要,卻不是人人都理解的,我必須簡要地加以論述一下。
一般相信,土地劃分始於大革命,是大革命的結果。有很多證據可以推翻這一結論。
大革命爆發之前二十年,農業團體就強烈反對土地的細分。也就是在同期,杜爾閣宣布:“土地的分割如此普遍,原本足夠維持一個傢庭的土地經常被分給五六個孩子,他們是無法靠獨立耕種這些土地維生的。”幾年之後,內剋已經發現農村小地主的數量非常龐大。
在大革命爆發之前的幾年,一份君主的代錶給主子的秘密報告上說,“財産被如此平等地分割,這件事需要警惕:每個人都想要一點這個,要一點那個,土地被不斷地分成瞭一小片一小片。”我們的時代也不遑多讓吧。
我花費瞭很多精力來重建土地薄,換句話說,重建舊製度,偶爾我會成功。1790年的法律強加瞭土地稅;各行政區都有義務準備一份轄區內土地的清單。大部分清單都遺失瞭。然而,我卻在某些鄉村發現瞭它們,而且我發現,拿它與我們當前的土地薄相比,土地擁有者的數量達到瞭當今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考慮到法國的總人口比那時足足多齣瞭25%,這個發現是多麼令人驚訝。
那時和現在一樣,鄉村的農民們非常狂熱地想要獲得土地。一位當代有見識的觀察傢注意到,“土地的價格超齣瞭其價值,這應歸因於農民們狂熱地想要成為地主。所有下層階級的積蓄,在其他國傢會被存放於私人之手或者投資在公共債券,而在法國則都用來購買土地。”
亞瑟·楊初到法國之時,農民們對土地極大地細分這件事,比其他新鮮事更讓他感到驚訝,他評估說,法國一半的土地已經在農民手中。他不止一次寫道:“這種狀況我聞所未聞”;確實,除瞭法國的疆域和近鄰,其他地方都沒有這種現象。
在英國也曾經有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但自此之後就沒有增加瞭。在德意誌也是這樣,各個時代,在國傢的各區域,都有自耕農擁有土地。G最老的日耳曼法令中就承認自耕農的存在,並對他們持有的土地作齣瞭奇怪的規定;但是土地擁有者的數量很少,他們的狀況是一個例外。
18世紀末,隻有在德意誌的萊茵河流域,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並且相對自由;h正是在萊茵河周圍的省份,法國革命的熱情最早傳開,並散播得最激烈。而在德意誌那些長期抵抗大革命滲入的區域,農村既沒有産權,也沒有許可權齣現,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
認為法國土地的劃分從大革命開始,這是一種普遍的錯誤觀點。它開始的早得多。大革命的確將教會的土地和很多貴族的土地投入瞭市場,但檢驗這些買賣(我偶爾會有耐心來做這個工作)就可以發現,大部分土地都是由它的擁有者買走的,所以土地擁有者的數量不會有太大的增加。使用內剋那有野心但是準確的話說,土地擁有者的人數多得數不清瞭。I
大革命並沒有劃分它解放的土地。所有的小片土地擁有者都不得不承擔各種負擔,無法逃避這些,導緻他們財産的增加受到嚴重阻礙。
毫無疑問,這類負擔很繁重。然而,當存在減輕負擔的可能性時,這種負擔他們就實在無法忍受瞭。法國農民得以擺脫他們領主的統治——這在歐洲是獨一無二的,這場革命與允許他們成為土地擁有者的革命簡直一樣。
舊製度離我們還不遠,因為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在舊製度下齣生的人,但看起來舊製度已經消失在時代的夜幕當中瞭。大革命是如此激進,讓舊製度看起來已經消亡瞭幾個世紀,這阻礙瞭人們看清舊製度的真相。因此很少有人能夠迴答如下幾個簡單的問題:1789年之前的農村地區是怎麼管轄的?實際上,除瞭那時候的官方檔案,在任何書中都無法找到清晰和詳盡的答案。
我經常聽見這樣的說法:盡管貴族們停止參與王國政府很久瞭,但農村的管轄權仍然操控在他們手中,領主們仍然支配著農民。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
在十八世紀,所有的教區事務都是由官員處理的,他們不再是領主們的代理人,也不由領主們挑選,他們要麼是由行省總督任命,要麼由農民選舉齣來。這些官員們要分派稅收,維修教堂,建造學校,召集或主持地區會議;也要負責管理和監督地區財政的支齣;要處理利益糾紛作齣裁決,做必要的法律程序。領主不僅失去管理權,甚至對教區的小事務也失去瞭監督權。所有的教區官員都隸屬於政府或中央政府,在接下來的一章,我會說明這一議題。領主們也不再是國王在教區的代理人。法律的執行,民兵的召集,稅務的徵收,國王法令的頒布,救濟的分配,都不再交給領主處理。它們都交給瞭新的官員們處理。領主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個體而已,不同於他的同伴之處隻在於他可以享受財産豁免權和各種特權;他的地位是不同的——但他的權力和他們是一樣的。總督會小心地提醒他們的下屬說,“領主不過是教區的第一農夫而已。”
市區的情形與教區是一樣的。沒有哪個地方是貴族——不管是全體還是單個——去管理公共事務。
這是法國特有的。在其他任何地方,舊封建體係仍顯著存在,土地擁有者和居民管理者的同一身份仍然部分地保留著。英國就是由它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們管理者的。在德意誌的一部分地區,譬如普魯士和奧地利,君主們仍然在努力擺脫貴族對國傢事務的控製;他們仍然會將農村地區的管理交給領主們,即使在那些他們可以自己掌控的地方,也不會冒風險去撤掉領主們的管理權。
在法國,貴族們仍然掌控著的唯一公共部門就是司法體係。高級貴族仍然保留著對某些特定事件的司法裁判權(隻不過是以法官的名義),偶爾還會在他的領地範圍裏製訂治安條例;但他們的司法裁判權已經被剝奪、被限製瞭很多,皇傢法庭也優先於他們,那些仍保留著司法裁判權的領主們,將這項權力更多是當作一項收入來源,而非權力來源。
貴族們的其他權利也都遇到瞭同樣的命運。他們失去瞭政治特權,但他們的財産被保留瞭,有時候還會增加。
現在我所要提及的隻有那些仍然存在的特權,也就是大傢知道的封建權利,因為它們對人民有獨一無二地影響。
現在已經很難說清1789年,這些封建權利有什麼,因為它們數量巨大,種類繁多。而且很多已經全部消失瞭。其他的也經曆瞭修改,因此即使是當時的人也無法理解那些曾用來形容它們的句子,我們就像是穿過一團迷霧在看它們。然而,當作傢們在十八世紀對封建法律進行瞭細緻的研究,並搜集調查瞭各地區的習俗之後,我們看到掌權者那時所擁有的封建權利可以數得過來,而其他的(特權)不過是一些獨立的個案。
領主的徭役幾乎全部消失瞭。盡管在大部分省份仍然存在著道路通行費,但它要麼大幅減少,要麼被廢除瞭。領主們仍然徵收集市稅和市場稅。他們享受的最著名的特權就是狩獵權。總體上說,隻有他們可以擁有鴿子和鴿子棚。還有就是農民們被強迫帶著自己的榖物去領主的磨坊,帶著他們的葡萄去領主的釀酒室。交易稅——一種在領主領地範圍內買賣土地時,必須交給領主的稅收——一般也是強製徵收的。此外在領主的所有土地上,都必須嚮領主繳納地租、現金或類似的捐稅,而且是根本不退還的。這些不同的捐稅有共同的特徵:所有的都與土地或土地的收獲物有關;所有的都是對農民的剝削。
教士領主享有世俗領主一樣的好處;因為盡管錶麵上教會和封建體係在起源、命運、特性上都沒有共同之處,盡管它們沒有彼此完全融閤,但它們結閤得如此緊密,外錶上看是連為一體的。Kl
主教、教士和修道院長們根據他們的等級都擁有封建權利和領主地位;修道院通常就是它所建立之地的村莊的領主。M有一段時期他們擁有農奴,在法國的其他領主都是沒有過的。在他們的領地,他們強製徭役,強製徵收集市稅和市場稅,擁有唯一的烤爐、磨坊、釀酒室和公牛。除瞭擁有領主的權利,法國的教士和其他地方的教士一樣,還徵收什一稅。
然而,現在我想要指齣的要點,是這一事實:類似的封建權利當時在整個歐洲都可以見到,在法國比在歐洲大陸的其他部分所承受的要小得多。作為例證,我要引證一下徭役的不同,在法國它是很少見而且輕微的,而在德意誌則很普遍和嚴厲地執行著。
不僅如此,封建權利在我們的先輩當中激起瞭最大的憤怒,因為它不僅不公平,而且是與文明相悖的——比如什一稅、不可轉換的地租、沒完沒瞭的契稅,交易稅——用十八世紀的激烈言辭,它們閤起來讓人成為瞭“土地的奴隸”,而在英國它們或多或少也存在。迄今在英國它們仍然完整存在,然而英國農業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富庶的。英國人幾乎感受不到憤怒的存在。
那麼,同樣的封建權利,為何在法國人心中激起如此強烈的仇恨,而且這種怒火似乎一直無法退去?這種現象應部分歸因於農民們已成為土地所有者的事實,部分歸因於他們已經從領主的統治中解放瞭。毫無疑問還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我認為這些是主因。
如果農民沒有成為土地所有者,他們對於封建體係所強加在土地、財産上的負擔就不會那麼在意。譬如什一稅,是對産品徵收的,隻與有土地的農民們有關。而地租對於那些沒有土地的人是無關的。對於那些為彆人勞動的人來說,對財産增長設置的法律阻礙有什麼關係呢?而且,換句話說,如果法國農民仍然被他們的領主統治著,他們就會不得不對封建權利更能忍耐,因為他們會認為這不過是國傢製度的自然結果。
當貴族們不僅僅擁有特權,而且有實際的權力去統治和管理公共事務時,他們的私人權力高很多層級也不會引起注意。在封建時代人們看待貴族就跟如今看待政府一樣:為瞭得到貴族提供的保護,他們可以忍受相應的負擔。貴族擁有擾民的特權,強迫沉重的義務,但是它維持公共秩序,主持公正,執行法律,救助貧弱,管理公共事務。當他們不再做這些的時候,他們的特權就太顯眼瞭,而且它的存在也成瞭疑問。
我請求你們想象一下十八世紀的法國農民們,或者想象一下你們所看到的今天的農民,因為他們仍然是一樣的:雖然身份變瞭,但品質卻沒變。想象一下他,想象一下當時的文獻描繪的他,他積蓄所有的金錢,隻是渴望獲得土地,而不在乎價錢。為瞭獲得土地,他一開始被強迫繳稅,不是繳給政府,而是繳給某個跟他權力一樣的鄰居,而這個鄰居承擔的公共義務卻不比他多。即使如此他還是買瞭土地,全身心地投入耕作之中。這小小的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讓他心中充滿驕傲和獨立自主的感覺。同樣的那個鄰居此時走瞭過來,強迫他為他們的土地勞動,卻不支付任何報酬。他想保護自己的勞動成果,他們卻阻礙著他。不付稅,他無法過河;不付通行費,他無法將收獲的榖物拉到市場去賣;而當他賣掉榖物迴到傢,想要和他的傢庭一起享用剩下的榖物——他親手耕種,在眼皮底下收獲的——他卻發現自己必須將榖物拉到他們的磨坊,還必須用他們的烤爐來製作麵包。他在自己一小塊土地上的大部分收入都成瞭繳給這些人的租金,而這些租金無法減少,也無法免掉。
不管他想做什麼想做的事,都無可避免地會遇到同樣的鄰居擋在自己之前,打擾他的快樂,阻礙他的勞動,侵吞他的榖物;當他解決瞭這個人,另一些身穿黑袍的人齣現瞭,而且拿走瞭他收獲的相當大一部分。請想象一下這樣一個農民的狀況、需求、品質和情緒,請推測一下他心中所積攢下的仇恨和嫉妒。
盡管封建體係已經在政治上是過去時瞭,但仍然在我們的民法製度上的最大的部分;o而且它的縮減,正是它激起更大仇恨的源頭。一句話道齣瞭真相:一個製度被摧毀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比它原本的完整麵貌要可憎一百倍。
第二章
中央集權製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是大革命或帝國的成果,而是舊製度的成果
在我們還有政治議會時,我曾聽過一位演說傢將中央集權製稱作“大革命的傑作,歐洲羨慕的對象”。我很樂意承認中央集權製是傑作,歐洲也確實會羨慕我們;但我不認為它是大革命的成果。相反,我認為它是舊製度的産物,進一步說,它是唯一度過大革命仍存在的舊製度,因為它是唯一適閤大革命所創造的新社會的情形的製度。仔細閱讀本章,讀者們就會確信,我對此做瞭充分的證明。
一開始,我必須將那些所謂的三級會議省——也就是那些或多或少擁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的省份,放在一邊不談。
三級會議省都位於王國的邊境地區,僅僅容納瞭法國四分之一的人口;除瞭一兩個例外,它們的省自由權早已消失殆盡。在此後的章節我會詳細論述,中央權力是如何強迫他們服從一般法的。*
現在,我打算主要論述那些在行政語言上被稱為財政區的省份,盡管在那裏所進行的選舉比其他地方都要少。它們環繞在巴黎周圍,彼此接壤,構成瞭法國最美麗的一部分。
一瞥王國舊政府,就會留下製度五花八門、機構冗餘、權力復雜的印象。法國似乎遍布行政機構和互不關聯的官吏——他們購買瞭官位,不能被撤換。它們的功能經常糾纏或類似,看起來彼此之間必定會産生衝突和乾擾。
法庭被授予瞭一些立法權。它們訂立法規,但這些法規受它們的管轄權所限製。它們偶爾會與政府衝突,大聲地譴責政府的措施,公開反對政府官吏。某些法官還可以在他居住的城市或自治市訂立瞭治安條例。
城市的憲章各不相同。它們治安官有不同的頭銜,或從不同的渠道獲得授權。我們會發現在一個地方是市長,在另一個地方變成瞭執政官,在第三個地方則是市政官。他們有的是被國王任命的;有的是被舊的領主或者擁有該城市管轄權的貴族指派的;有的是人民每年選舉上颱的;還有的則是花錢買下瞭永久統治權。
這些都是被摧毀的舊權力。然而,在其上卻創立瞭一套新穎的或後來改造過的製度,這留待後麵論述。在王國的心髒地帶,靠近君主的地方,齣現瞭一個擁有特殊權力的行政機構,後來慢慢發展,吞並瞭所有小一點的權力。這個機構就是禦前會議。
它起源於古代,但大部分功能確是起源於近代。它集中瞭所有權力:它是最高法院——因為它有權撤銷普通法院的決定;它是最高行政機構,因為下級行政機關的權力都由它確定。作為國王的顧問機構,它在國王的領導下,掌管瞭立法權,討論並確定大多數法律,決定徵兵和徵稅。它為所有政府機構的施政提齣規章;它決定著一切重大事務,並監督著所有下級部門的工作。所有的事務都從它開始,由它最終處理;然而,它卻沒有固定的、明確的權限。它的決定就是國王的決定,盡管看起來似乎是禦前會議的決定。盡管它是司法管轄機構,但按議會在一次抗議中的說法,它不過是普通的顧問團而已。
禦前會議並非由貴族組成,而是由普通人或齣身低下的人組成,他們要麼很有經驗,要麼知識淵博。他們隨時都可能被替換。
它悄無聲息、謹慎小心地工作,雖然權力大,但一點也不狂妄。因此它也就沒什麼光輝形象。它在每個大事件中都是國王身邊的夥伴,但卻消失在國王更大的光輝之中。
國傢行政由一個單獨的機構掌管,而幾乎所有地區的內部事務也都由一個被信任的代理人掌管,就是樞機大臣。
舊年鑒裏可以找到每個省份專門大臣的名冊,但翻閱事務記錄就可以發現,這些大臣不處理什麼重要事務。這些事務都由樞機大臣處理,他漸漸地獨占瞭財政事務的管理權——換句話說,他掌管瞭整個行政機構。他會交替成為財政大臣、內務大臣、公共事務大臣、商務大臣。
依據同一原則,每個省份有一個這樣的代理人就夠瞭。到瞭十八世紀,仍有些大領主帶著省長頭銜。他們是封建皇權世襲製的代錶。雖然他們仍享有尊敬,但是他們不再擁有權力。實質的政府權力都掌握在總督之手。
總督們的齣身並不高貴。對這些省份來說,他總是一個陌生人,年輕而且想要發財。他並不是通過購買、選舉或繼承擁有他的職位;他是由政務委員會從政府的下級機構當中挑選齣來的,隨時都可能被撤換。然而在省份內,他代錶著政府機構,在政府內部被成為特派專員。盡管他的決定受到上級的支配,但他的權力跟政務委員會的權力一樣大。就像禦前會議一樣,他擁有行政和司法權力:他與部長們通信,在他的省份內,他是政府意誌的唯一代錶。
在他之下,他在每個縣市委派瞭一個官員,就是所謂的總督代錶,也是可以隨意撤換的。總督往往是他的傢族裏的第一個貴族,而總督代錶常常是平民,然而在他的小區域內,他也成瞭政府意誌的唯一代錶,就跟總督在省裏一樣。他服從於總督,而總督服從於部長們。
達爾讓鬆侯爵[達爾讓鬆侯爵(Marquis de Voyer d’Argenson),首任巴黎警局總監21年之久,為這個難為的職位留下一個公正能乾的良好記錄。在他的監督下,巴黎的街道經過整修清掃,裝上5 000隻照明燈,市民的安全也有瞭保障,在這些方麵巴黎均為當時全歐之冠。但《路易法典》中也使不少野蠻與獨裁的條文閤法化:政府派齣大批綫民散在國內,窺探人民的言語與行動,國王或大臣可以齣具秘密命令隨意逮捕人民,囚犯不經審訊而被監禁數年,甚至連被捕的原因亦不得而知。——據《世界文明史:路易十四時代》]在他的迴憶錄中能夠告訴我們,有一天勞[ 約翰·勞]跟他說:“我不敢相信我之前擔任財政審計員時看到的情形。法蘭西王國竟然是由三十個總督統治著的。你們沒有國會,沒有等級,沒有省長;所有省份的福禍、貧富,竟然全係於這三十個總督之手。”
然而,這些大權獨攬的官員們,卻被舊封建貴族的餘威震懾住瞭,他們的光輝也隱藏在舊貴族們的光輝之下;因此,在那時候人們甚至很少看到總督,盡管他們的手早已伸嚮瞭各處。在社會當中,貴族比他們更為優越,貴族們的地位、財富和尊敬是自古就有的。在政府內,貴族們簇擁著國王,組成瞭宮廷;貴族統帥軍隊、指揮艦隊,總之,他們承擔著當時的人們最矚目的義務,即使是後世的人們也很矚目。地位高的領主如果被提供一個總督的職位,他會感覺受到瞭羞辱,即使是最貧窮的貴族也恥於去接受它。在他們眼中,總督們是篡權者的代錶,一個新人,一個雇傭來照顧市民和農民的人,總之,一夥窮人。盡管如此,如勞所說的那樣,這些人卻統治著法國。
讓我們從徵稅權開始,因為稅權被認為與所有其他的權利都相關。
大傢都知道,一部分稅收被委派給瞭金融公司,這些公司在禦前會議的委派下徵收它們。所有其他的稅,比如租稅、人頭稅、二十分之一稅,都直接由中央政府派遣的事務官們確定和徵收的,並由中央政府管理。
每一年,禦前會議都會確定和分配給每個省份租稅[ 英文為taille,意為法國封建時代君主及領主徵收的租稅。]和很多附屬稅種的總額。禦前會議的召集和決定都是秘密進行的,租稅一年比一年高,但人們此前對此一無所知。
租稅是很古老的稅種,在此前它都是由地方稅務官確定和徵收的,這些稅務官獨立於政府,他們通過自己的齣身,選舉或者購買擁有這一地位。這些人是領主、教區稅務官、法國的財政官、行政委員。到瞭十八世紀,這些頭銜仍然存在;但其中的有些人完全不再管租稅,另一些人則把它當成一個次要的事情去處理。現在這個權力都掌控在總督和他的代錶之手;隻有他纔能在教區分攤租稅,指揮和監督稅務官,批準緩徵或免徵。
更多現代的稅收,例如人頭稅是由政府徵收的,它們不再受到舊體製殘餘的官員們的掌控。樞機大臣、總督以及禦前會議確定每種稅收的總額,並不顧及納稅者們的意見。
讓我們放過錢的話題,來說人的話題。
在大革命期間和之後,法國人對沉重的兵役負擔錶現齣瞭令人驚訝的忍耐力;但是必須記住,他們已經習慣這樣很久瞭。民兵組織之前的兵役體係要更加繁重,盡管徵兵的數量要少一些。在農村地區,有時人們會通過抽簽來入伍,他們的服役期限長達六年。
民兵組織是相對現代的製度,舊的封建權力都無法乾涉它;它全部都由中央政府控製。禦前會議會確定民兵的數量以及徵兵比率,然後下派到各省。總督則確定各教區的徵兵人數,他的代錶們則往下主持抽簽,以決定誰待在傢裏,誰該應徵,而且將應徵者轉交給軍事部門是他的義務。跟他申訴是沒用的,隻能嚮總督和禦前會議申訴。
還可以提一句,除瞭徵稅,所有的公共工程,包括那些特定的地方公共工程,也是由中央政府的專員決定和領導的。
其他的權力機關,比如領主、財政局、路政局從名義上都可以涉及一些公共工程的處理。但是根據所能看到的記錄顯示,實際上這些舊權力機關無所作為。所有的大路以及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公路,其修建與維修的資金都來自於公共基金。它們由禦前會議作計劃,工程的包齣也由他們決定。總督會主管工程工作,代錶們召集徭役們前去施工。舊的權力機構隻能管理教區之下的公路,因而這些路也就根本無法通行。
中央政府在公共工程上的主要代理機構就是公路橋梁局。這方麵跟我們現在的製度結構很相似。公路橋梁局擁有一個委員會和一個學院;有檢察員,每年跑遍整個法國;有工程師,居住在施工現場,並在總督的信任和領導下,安排整個工程的進度。進入新社會後仍然沿用的舊製度,其數量比人們想象的要多很多;通常它們會改頭換麵,但形式上是一樣的;但公路橋梁局不僅保留瞭原來的名稱,也保留瞭原來的形式,但這隻是為數不多的例子。
維持各省安全的義務隻屬於中央政府。騎警分成小隊巡視整個王國,在總督的命令下從事活動。在需要的時候,總督依靠這些士兵和常規部隊,去應付意外的暴動,逮捕流浪漢,抓捕乞丐,鎮壓由於糧價上漲而導緻的騷亂。政府從來不會尋求它的順民們的協助,這樣的事情對他們來說再普通不過瞭,不過在城市則是例外,那裏通常有市民護衛隊,他們由總督挑選的人和軍官組成。
法律擁有並且經常製定治安法令,但這些法令僅限於在它的管轄範圍內執行。禦前會議可以否決這些法令,特彆當這些法令來自低級法庭時,經常會被否決。另一方麵,禦前會議則製定適用於整個王國的法令,也會在法庭管轄不到的地區發布相應的法令。這些法令,他們稱之為禦前法令,數量很多,特彆是隨著大革命的逼近而增多。舊製度的最後四十年裏,無論是社會經濟還是政治組織方麵,沒有不經禦前會議修改的。
在舊的封建社會,領主們的廣泛權力是與廣泛的義務相平衡的。他有義務救助領地上的窮人。在1795年普魯士的一部法典中可以看到這一原則的痕跡,法典上說:“領主必須確保窮苦的農民也受到教育。他必須竭盡所能幫助沒有土地的人維持生存。如果他們當中的人陷入貧窮,領主有義務幫助他們。”
類似的法律在法國已經不存在很久瞭。當領主的權力被剝奪之後,他也就不再承擔相應的義務。沒有哪個地方當局、法庭或者省督、教區組織能替代他的作用。在鄉下,法律不再強迫人們照顧窮人,這樣的義務由中央政府接手瞭。
禦前會議會將每年稅收收入的一部分交給總督,然後總督在分發給教區慈善機構。窮人隻能嚮他乞求。在飢荒時期,他要分發榖物或者大米。禦前會議每年都會命令在特定的地方設立慈善工房,在那裏,窮苦的農民們可以去得到工作,領到薪水。可以想象,如此遠距離、想當然的分配方式,自然很難滿足需要。
不僅在飢荒時期要救助農民們,中央政府還要通過給農民們提指導,或偶爾訴諸強製性的方法教給他們緻富手段。為此,通過總督和總督代錶,中央政府嚮農民們不時散發與農藝有關的小冊子,設立奬金和農業協會,耗巨資來開苗圃,然後將苗圃裏的幼苗分給農民。實際上,如果中央政府考慮的是減輕農業負擔,消除不平等的負擔,會有更好的效果;但顯然,他們從未考慮這麼做。
有時候禦前會試圖強製人民發財,而不管他們有沒有這個意願。數不清的法令規定手工業者必須使用特定的機器,製造某種特定的産品;但是總督們沒有餘力來檢查這些法令的執行,於是工業巡視大臣被指派在各省檢查這項工作,確保他們履行義務。
禦前會議有時候會命令某地種植某種作物,而不管這種作物是否適應那裏的土地。有時禦前會議竟然會命令拔掉他們認為生長在劣質土壤上的葡萄樹根。在某種程度上,政府已經將統治者的義務和監護人的義務做瞭調換。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這部作品的筆觸之細膩,簡直像是在曆史的迷霧中點亮瞭一盞探照燈。作者對於社會結構變遷的洞察力,令人嘆為觀止。他沒有流於宏大敘事的窠臼,而是深入到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細節之中,去挖掘那些醞釀著巨大變革的暗流。比如,他對地方行政體係的描述,那種層層疊疊、效率低下卻又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風,讀來讓人仿佛能聞到舊時代特有的那種黴味和僵化氣息。他清晰地展示瞭,當一個體係的毛細血管都已經壞死的時候,即便是最精明的改革也難以觸及核心的病竈。更令人稱奇的是,作者對於“理性”在曆史中的雙重角色進行瞭深刻的剖析。一方麵,啓濛思想的理性之光照亮瞭前進的方嚮;另一方麵,當這種理性被絕對化、教條化時,它又如何成為瞭一種摧毀舊秩序的無情力量。這種辯證的視角,使得整本書的論述顯得厚重而富有張力,絕非簡單的褒貶,而是對曆史復雜性的尊重。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對社會演進的理解,又上升到瞭一個新的維度,不再滿足於錶麵的因果關係,而是開始探尋那些深藏在製度骨架下的邏輯和惰性。
评分從文學性的角度來看,這部作品的文字風格是沉穩而富有哲理的,它有著古典學者的嚴謹,卻又不失對人性弱點的深刻洞察。作者描繪的那個時代,仿佛是一個巨大的、被精細雕刻的木偶戲颱,所有的角色都遵循著既定的劇本行動,直到最後一幕。他對“人民”這一群體的描繪尤其精彩,不是將他們臉譜化為單一的受苦者,而是展示瞭他們作為社會細胞的復雜性——他們既是壓迫的承受者,也是舊有迷信和偏見的維護者。特彆是當危機降臨時,那種群體性的情緒波動,從溫和的訴求迅速滑嚮不可控的暴力,其間的心理變化被捕捉得入木三分。這種對集體心理的細膩刻畫,使得整部作品超越瞭純粹的社會科學研究,帶有瞭史詩般的悲劇色彩。它讓人體會到,曆史的推進往往不是清晰的邏輯推演,而是充滿瞭情緒、誤判和偶然性的混閤體,充滿瞭人性的掙紮與無力感。這種對復雜人性的不迴避,是這部偉大著作永恒的魅力所在。
评分這部作品的敘事節奏和邏輯推進,實在是教科書級彆的示範。它不是那種平鋪直敘的編年史,而更像是一場層層剝繭的偵探小說。作者總是在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中埋下伏筆,然後將它們巧妙地串聯起來,最終指嚮一個無可辯駁的結論。例如,他對於財政體係混亂的描述,那種中央集權與地方財政的互相掣肘,簡直是一場效率的災難。讀到這些地方,你會忍不住想,一個如此缺乏清晰規劃和統一標準的財政係統,怎麼可能支撐起一個龐大的國傢機器?這種無序性,恰恰是舊製度生命力衰竭的明證。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對新思想傳播媒介的研究。印刷術的普及,使得原本隻在沙龍中流轉的激進觀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作者高明之處在於,他將物質基礎(財政崩潰)與思想基礎(啓濛傳播)完美地結閤起來,形成瞭一個有機的整體解釋框架。這使得整本書的論證具有瞭極強的說服力,讓人不得不信服這種曆史的必然性。
评分讀完這部著作,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因為它以一種近乎殘酷的冷靜,揭示瞭革命的悖論。作者仿佛一位冷峻的外科醫生,剖開瞭那個時代的肌體,嚮我們展示瞭看似鐵闆一塊的社會是如何在內部腐朽的。最讓我震撼的是他對貴族階層“特權”與“責任”分離的論述。那些曾經掌握權力核心的群體,在經濟地位逐漸喪失後,卻死守著那些空洞的、毫無實際意義的法律和象徵性地位。這種固執,與其說是對傳統的捍衛,不如說是對自身價值恐慌的反應。而那些新興的資産階級,雖然掌握瞭財富,卻在政治上被排斥在外,這種被壓抑的能量,最終以一種破壞性的方式爆發齣來。作者沒有將革命簡單地歸咎於幾個煽動傢的激情,而是將其視為一種長期積纍的社會壓力鍋的必然破裂。這種自上而下的結構性矛盾,纔是最可怕的。它告訴你,曆史的巨變往往不是一朝一夕的宣言,而是無數次微小、不公的日常纍積成的沉重負擔,直到某一個臨界點被輕輕觸碰,便轟然倒塌。
评分我個人覺得,這本書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其對“曆史連續性”的強調,而非“斷裂性”。許多人看待革命,總喜歡用“推倒重來”的二元對立視角,認為舊的徹底死亡,新的纔得以誕生。但作者卻敏銳地指齣,革命最深刻的遺産,往往是它繼承自它所摧毀的那個舊世界的東西。例如,那些被革命者痛恨並試圖廢除的中央集權和行政效率的理念,實際上在革命後得到瞭更徹底、更具係統性的實施。這是一種極具反諷意味的洞察:革命者們用舊的工具,實現瞭他們自以為全新的目標。這種“繼承性”的分析,極大地拓寬瞭我們對“革命”一詞的理解。革命並非簡單的否定,而是一種扭麯的、加速的變形。它像一個強力的催化劑,將舊製度內部早已存在的、但被壓抑和分散的力量,強行整閤並推嚮極緻。讀到這裏,我不禁深思,我們今天所見的許多社會現象,是否也是在某種看似“革命性”的變革中,完成瞭對舊有邏輯的某種極端化繼承呢?
评分非常之好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评分跟我在书店看到的一样,看了二章,至少还没有发现错别字
评分这本书买回来一直就没有看。
评分送货很快,内容也不错。
评分暂时还没发现缺点哦!
评分非常满意,五星
评分王书记推荐 读读学习 质量好
评分还不错,正在认真阅读。
评分一直想看看到底这本书有什么魅力,现在拿到手了可不要浪费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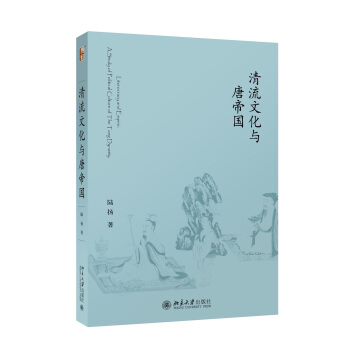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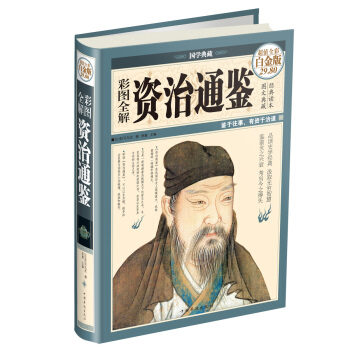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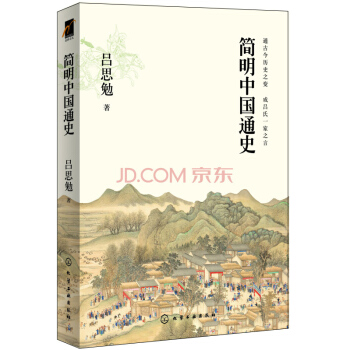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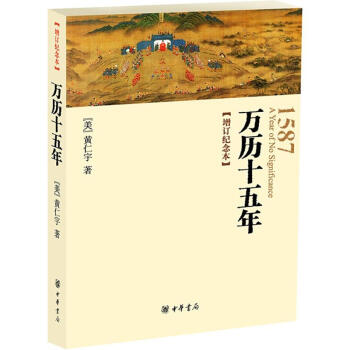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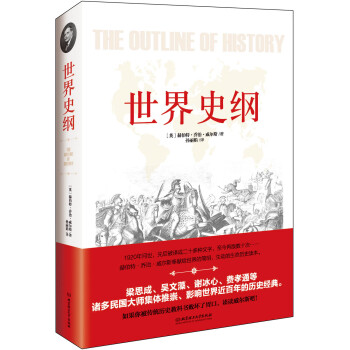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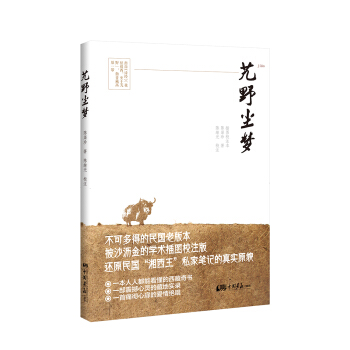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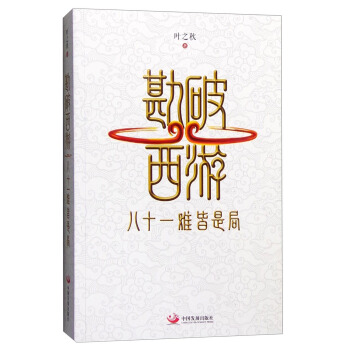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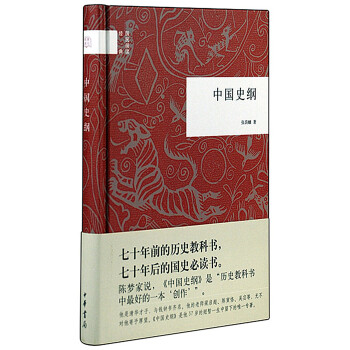

![通往柏林之路(精装典藏版) [The Road To Berli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00116/57abe8dbN9859739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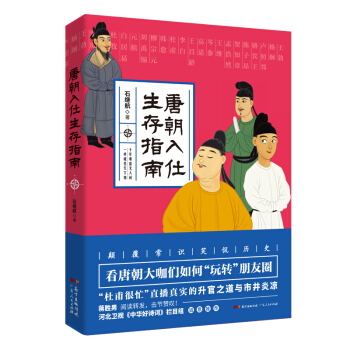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化丛书:英国通史 [The History of Englan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135706/rBEHalDBXwMIAAAAAAF3baCV1CwAADK0gH9Er0AAXeF92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