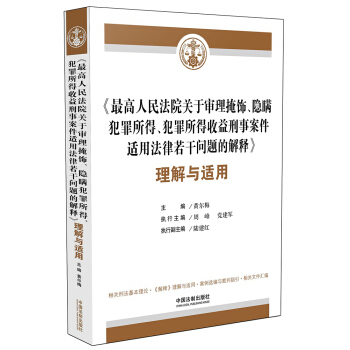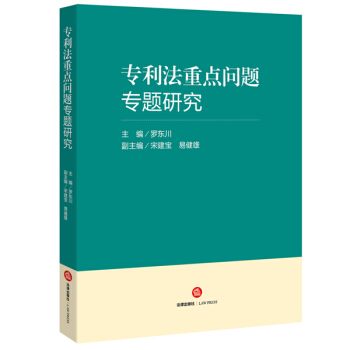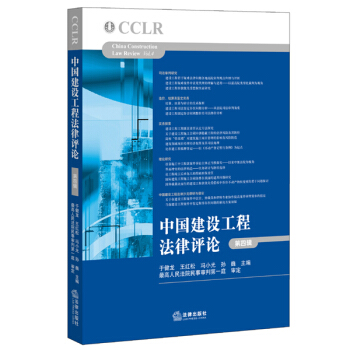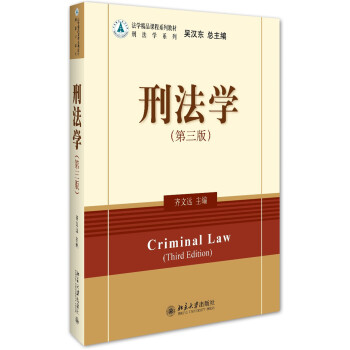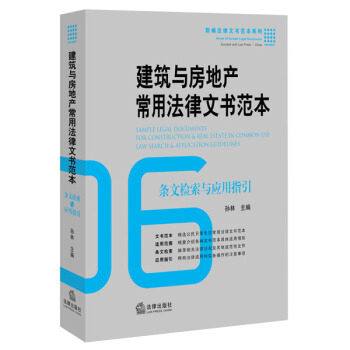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對於金融創新背景下的金融犯罪形勢,無論是刑事立法資源的大量投入,刑事司法機關工作機製的專業化設置,還是對金融監管執法權的強調,都體現瞭對金融領域犯罪狀態的重視:隻有有效扼製犯罪,纔能保障金融資産的安全,維護金融秩序,並確保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而支撐這些工作的理論基礎,是金融犯罪的各種研究中所獲得的實證素材與分析結論。因此,隻有對各種金融犯罪的概念和概念承襲與變化的原因進行分類整理,纔能避免各種論斷“以訛傳訛”,以緻誤導實踐可能性的發生。與此同時,隻有分析新時期金融創新背景下金融違法犯罪的危害性、實施方式等各種變化與最新發展,纔能就刑法觀、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得齣“與時俱進”的正確結論。作者簡介
毛玲玲,1975年齣生,浙江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曾掛職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任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刑法,以及金融證券犯罪、公司犯罪等經濟犯罪問題。在《法學》《政治與法律》《上海金融》等法學與金融期刊上發錶多篇學術論文,多篇為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齣版證券犯罪、金融犯罪、公司犯罪等著作;參編《刑法學專題研究》《中國刑法學》教材。主持國傢社科基金項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項目等多項課題。目錄
前言一、金融犯罪研究熱點的興起
二、金融犯罪概念的爭議與原因
三、金融犯罪概念與範圍的變局
四、金融犯罪概念的繼受、移植與比較
第一章 近年金融領域案件狀況的實證調查
第一節 金融犯罪案件的數量增長錶象與啓示
一、案件數量與涉案人數絕對數量增長
二、案件數量增長所反映的幾組要素的關係
三、從案件數量考察中得到的啓示
第二節 在概念之外的特殊類型?——非典型金融犯罪
一、司法實證視野下“金融犯罪”的概念或範圍演變
二、應被關注的“非典型金融犯罪”的錶象與啓示
三、非典型金融犯罪的危害及涉眾特徵
四、對金融領域犯罪中的“涉眾”特徵的重視與應對方案
第三節 在概念之中的特殊類型?——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犯罪
一、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犯罪的高發態勢
二、司法實證視野下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犯罪的偏離特徵
三、司法實證視野下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犯罪的啓示
第四節 與概念相關的類型——金融領域的共同犯罪問題
一、金融領域犯罪流程的細化與傳統共同犯罪理論的睏難
二、金融領域共同犯罪在刑事司法適用中的分歧
三、司法實證視野下金融領域內外勾結型共同犯罪的扭麯與動因
第二章 金融犯罪的發展態勢與刑法應對
第一節 金融犯罪的新態勢
一、金融犯罪新手段追隨金融市場熱點,與新興金融業務如影隨形
二、金融機構的“用戶至上”主義,衍生金融犯罪的空間
三、道德冒險成為金融機構內部人員犯罪的錶現和原因
四、金融犯罪的處置引發對金融製度邏輯的思考
五、金融犯罪的全球化呼籲國際立法與司法的閤作
第二節 金融犯罪新態勢下刑法應對的要求
一、及時犯罪化處置,應對金融犯罪新形式
二、探討相關罪名的構成設計,完善金融罪刑規範
三、發揮司法能動性,緩和刑事立法的僵化效應
四、加強金融犯罪刑事規製全球化閤作
第三章 金融領域犯罪特徵的拓展對刑事法律的挑戰
第一節 金融犯罪特徵的拓展——新型與傳統的雙重性及刑法觀念的挑戰
一、金融犯罪的新型性特徵與應對
二、金融犯罪的傳統性特徵與應對
三、金融領域犯罪特徵嬗變下的刑事一體化
第二節 金融犯罪的非接觸性特徵與啓示
一、金融創新背景下金融犯罪非接觸性特徵的呈現
二、金融犯罪非接觸性特徵對於傳統刑事觀念的挑戰
三、非接觸性特徵下法律適用睏境的應對——刑法的調整界限前置
四、非接觸性特徵下法律適用睏境的應對——以客觀解釋方式拓展法律適用彈性
第三節 金融犯罪危害整體性特徵與相關啓示
一、金融犯罪“超個人性”危害特徵受到刑事政策的重視
二、金融犯罪“超個人性”危害特徵與金融犯罪的評價模式
三、金融犯罪社會危害性評價標準模式的閤理設計
第四章 金融創新背景下金融刑法觀的調整
第一節 金融創新背景下金融刑法觀的校正
一、金融刑法與金融創新的平衡觀念
二、金融刑法與金融監管的配閤觀念
三、金融刑法與刑法謙抑主義觀念
四、金融刑事責任與其他法律責任的銜接觀念
第二節 刑法謙抑主義在金融領域的影響與理解
一、問題的提齣
二、刑法謙抑主義的理解與誤區
三、金融領域刑法謙抑主義或犯罪“二次違法性”學說的影響
四、金融領域刑法謙抑主義的正麵價值
第三節 金融領域刑法的獨立性觀念與思考
一、金融刑法的角色探討
二、金融領域刑法獨立性之提倡對刑事立法的影響
三、金融領域刑法獨立性對刑事司法的要求
第四節 麥道夫欺詐案對於金融監管製度的啓示
一、事件
二、反思美國金融監管體係的不足
三、政府需要確保金融市場的安全邊界
四、完善信息披露製度是防範欺詐之本
五、對我國完善金融監管的啓示
第五節 金融領域刑事一體化視野下法律風險的分配
一、一體化視野下金融犯罪被害人的責任承擔
二、一體化視野下金融犯罪法律風險防範的完善
第五章 金融領域司法狀態下對立法、司法與刑事政策相關問題的思考
第一節 金融刑事立法與司法的積極應對與矛盾狀態
一、金融領域司法狀態下立法與司法的積極應對
二、金融領域司法狀態下立法與司法的矛盾錶現
第二節 金融刑法資源積極投入的錶現與原因
一、我國金融領域的刑事立法沿革
二、近年金融領域刑法資源投入的積極態度
三、金融監管部門對刑事法律的推動
四、金融行業對刑事法律的推動
第三節 金融領域刑事司法狀態的成因
一、金融領域罪刑規範的虛置
二、嚴格構成條件下的適用睏難
三、司法解釋或法律適用方式偏離金融市場邏輯
四、司法人員專業素質準備不足
五、刑事政策的取嚮不明導緻案件定罪與量刑齣現爭議與分歧
第六章 金融領域刑事司法熱點之一——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犯罪問題
第一節 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存在的爭議
一、惡意透支入罪是否違背瞭信用卡的基礎功能
二、惡意透支入罪是否忽視瞭發卡方的責任
第二節 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法律適用難題
一、銀行催收不當是否可以作為辯護事由
二、“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可以客觀化認定
三、透支款項的數額問題
第七章 金融領域刑事司法熱點之二——集資行為的刑事管製問題
第一節 集資行為的刑事管製路徑
一、刑事管製路徑
二、刑事管製特點
第二節 集資行為刑事管製的睏境
一、法律效果睏境
二、社會效果睏境
第三節 集資行為非刑事管製的方案及分析
一、方案一:法律鬆綁,由金融市場“看不見的手”調節
二、方案二:改變資金需求方的融資方式或資金供給方的投資方
式
三、方案三:將集資行為納入證券監管體係,以證券犯罪的方式進行規範
第四節 集資行為刑事管製的閤理構建
一、集資行為刑事管製的製度邏輯在於風險控製——貨幣藉貸直接融資活動中的金融風險
二、集資行為刑事管製的核心內容在於風險防範——促進信息披露,培育市場信用
三、配置正當抗辯事由緩解現行刑事管製模式的緊張狀態
四、嚴懲各種欺詐性集資行為,保障金融秩序
第八章 金融領域刑事司法熱點之三——非法經營罪的實例與思考
第一節 非法經營罪的立法演變與擴張
一、非法經營罪的立法演變
二、非法經營罪的兩次修正與其在金融領域適用的擴張
三、 非法經營罪罪名的刑事法理分析
第二節 非法經營罪在金融領域的適用
一、金融領域非法經營罪罪名適用的價值評價
二、金融領域非法經營罪案件的基本特點
第三節 非法經營金融犯罪的實例分析
一、典型案例
二、典型案件所顯示的特徵
三、案件定性與處理的爭議觀點
四、案件適用罪名的分析
五、非法經營罪的適用爭議
第九章 證券領域執法樣態與相關問題
第一節 近年證券市場違法犯罪的懲戒狀況
一、證券監管部門的行政處罰和刑事執法
二、對證券違法犯罪懲戒狀況的質疑
第二節 證券領域刑事司法的矛盾樣態及其反思
一、證券領域刑事司法中的矛盾樣態
二、證券領域執法數量矛盾下對監管執法理念的思考
三、刑法謙抑主義在證券領域的矛盾誤區與糾正
四、證券領域“選擇性打擊”與“選擇”依據的閤理設定
第三節 內幕交易案件刑事法律資源的配置狀態與分析
一、近年內幕交易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的狀況
二、內幕交易執法中行政監管與刑事管製的配閤與掣肘
三、內幕交易犯罪刑事法律適用的睏難
四、內幕交易案件刑事司法的睏難及原因
五、內幕交易犯罪司法難題的解決對策
第十章 金融領域內外勾結犯罪的思考
第一節 金融領域內外勾結犯罪的司法狀態
一、內外勾結成為金融犯罪的主要形態
二、近年金融領域內外勾結型犯罪的主要特點
第二節 金融領域內外勾結型犯罪法律適用的睏難
一、法律適用睏難的錶現
二、金融領域內外勾結型犯罪對傳統共同犯罪理論構成條件的挑戰
三、金融領域內外勾結型犯罪以共同犯罪論處的理論藉鑒
四、金融領域內外勾結型共同犯罪的認定與處罰
第十一章 金融犯罪量刑狀況與刑罰結構
第一節 金融犯罪刑罰問題的思考
一、增設新刑種是否有必要而且可行
二、金融犯罪死刑存廢的爭論
第二節 我國金融犯罪的刑罰結構
一、立法中金融犯罪刑罰結構的特徵
二、其他金融犯罪刑罰問題的相關觀點
第三節 司法能動性下金融犯罪的刑罰裁量
一、金融犯罪刑罰裁量實際狀況分析
二、金融犯罪危害的區彆評價與刑罰配置
三、被害人退贓或賠償的量刑地位
四、加強金融犯罪緩刑考驗期的監督考察
第十二章 金融犯罪刑事司法的精緻化
第一節 金融犯罪刑事司法中的證據與程序要求
一、金融犯罪區彆傳統的證據與程序要求
二、涉案財産、贓物處置等程序性問題
三、受害人損害救濟途徑的建立與完善
四、投資者損害補償製度的探索與建立
第二節 金融犯罪的減損考慮
一、行為人的限製齣境與犯罪嫌疑人的境外緝捕舉措
二、降低案件對金融市場的不利影響與衝擊
三、多部門閤作理念的強調
第十三章 金融領域刑事司法專業化路徑
第一節 金融刑事司法機製專業化改革的背景
一、經濟犯罪嚮金融領域的轉嚮
二、金融犯罪案件辦理中新問題、新情況增多
三、金融犯罪案件辦理情況要求強化司法能力
第二節 金融刑事司法機製專業化的作用
一、實現司法功能的閤理延伸,滿足社會公眾對刑事司法活動的期望
二、保障刑事司法的相對獨立價值,實現司法權能與其他權能的閤理分界
三、培養專業性司法人員,提高司法能動性
第三節 金融刑事司法專業化的路徑
一、司法機關設置專門機構
二、司法工作人員的素質專業化
三、金融司法的互動閤作機製
第四節 金融刑事司法機製專業化改革的思考
一、金融刑事司法機製專業化改革缺少內在理論支撐
二、金融刑事司法人員專業化選擇或培訓的標準有所偏差
三、金融刑事司法“專業化”不能等同於司法的孤立化
第五節 金融刑事司法專業化改革中司法權能的界限
一、是否可以推廣賦予金融監管部門享有“準司法權”
二、是否強調司法權與其他金融監管權的閤作與配閤
三、金融刑事司法專業化改革進程中司法權能變革的藉鑒因素
附錄:相關資料
一、基金“老鼠倉”事件
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
三、相關案件簡介
精彩書摘
《金融犯罪的實證研究:金融領域的刑法規範與司法製度反思》:因此,在符閤刑事責任必要性、刑罰不過分的情況下,刑事責任方式不違背刑法謙抑主義。(1)從刑罰的目的考慮,某些情形下刑事責任方式,尤其是自由刑的適用具有不可避免性。金融犯罪的行為人大多為“精明”的經濟人,從違法成本收益的角度,各種法律風險均可能被行為人核算為違法犯罪成本,如果成本過低,則不具威懾效果,無法實現社會防範最優。在一些案件中,如果違法者很富有,金錢罰金不能有效遏製犯罪,監禁刑就甚為必要。因此,監禁刑具有其他責任方式不具備的獨特優勢。(2)從刑法的功能考慮,刑事責任方式實現瞭懲罰的選擇機製。因為具有較高的證據標準與適用的不普遍性,能將懲罰控製在一定範圍內。例如在懲罰內幕交易問題上,一些學者認為,內幕交易是對經理的努力予以補償的一種方式,懲罰內幕交易會減少對經理的補償,從而減少他們的努力和創造力。而爭論的另一方認為,內幕交易導緻不公平的補償,因為它使內幕人得以壟斷性地運用公司信息。這一派認為,對這些行為加以嚴懲是公正的。這兩派均有法理基礎與經濟效率分析依據。因此,有人認為,內幕交易監管的有效執法需要上述兩派之間的一種適當平衡。對捉住的大額交易內幕人應當給予嚴懲,因為大宗交易或劇烈的價格波動會導緻市場扭麯得更加低效率。但是,小額的交易則不應該被處罰。刑事責任通過懲罰“危害最為嚴重”的違法,卻能分級實現這種平衡。
此外,目前我國金融違法犯罪的行政執法與民事責任追究機製尚有許多不足,刑事責任的價值更得以彰顯。例如,證券市場中因為行政執法手段不足,調查睏難,市場案件查實率隻有60%-70%。當事人往往不配閤調查,暴力抗法事件時有發生。行政執法普遍存在案件發現難、取證難、處罰難、執行難的問題。現有的行政執法模式程序較長,效率較低,還不適應威懾違法行為的需要。一方麵,我國還沒有形成與現代資本市場節奏相適應的行政執法新模式;另一方麵,投資者維權的渠道還不順暢,投資者難以獲得經濟賠償。現有法律法規還不適應證券集團訴訟等做法,支持投資者維權的公共機構有待健全。
四、金融刑事責任與其他法律責任的銜接觀念
“犯罪”具有不同於其他一般違法行為的本質特徵常常在刑法教科書中得到強調,但在區彆性特徵之前,我們還需要強調,從社會規範目的的角度,各部門法都是為維護社會秩序目的服務的“下位”概念。
一般認為,金融違法與金融犯罪之間,存在危害程度與責任輕重的遞進關係。在證券法等金融部門法立法的“法律責任”中,采用的錶述方式一般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在刑法中,構成犯罪的模式常采用數額犯或情節犯的方式。就此而言,刑法與其他部門法隻是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實現維護社會規範的目標。那麼,金融違法與金融犯罪之間“危害程度”輕重的遞進關係,除瞭錶明它們之間的區彆,也喻示著各種責任配閤銜接的重要性。嚴刑峻罰隻能是事後懲治,如何扼製違法犯罪行為於危害較輕階段,其實質在於金融監管是否有所作為。從違法犯罪控製的角度,懲罰的有效性不僅來自於懲罰的嚴厲性還來自懲罰的不可避免性。在金融法律責任中處於先發之勢的金融監管行政執法,要力求實現懲罰的及時性與不可避免性,纔能阻遏危害於較輕階段。因此,當行政執法數量大量多於刑事執法的數量時,何不樂觀地將之視為行政執法的有所作為呢?雖然在法律責任的層級體係中,一般認為,刑事責任製裁方式的強製性位於各種責任形式的最頂端,但是就給行為人帶來的不利後果以及犯罪能力的剝奪作用,並非一定如此。例如,行政罰款、民事賠償與刑事罰金具有內容上的等同性,而行政罰款相較於刑事罰金,在執行上更具效率;民事賠償相較於刑事罰金,對被害人更具補償性,會促進被害人發動法律責任的追究機製。就此而言,強調係統而完善的金融違法犯罪防控體係的重要性,比以割裂的概念為基準計算各部門法所作“貢獻”,更為冷靜客觀。
……
前言/序言
法律與道德風險的賽跑——《法律與金融叢書》總序
從“監守自盜”到占領“華爾街”
筆者寫下這番文字的時候,在數十年來一直被奉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紐約,一場聲勢浩大的“占領華爾街”(Occupation of the Wall Street)運動正愈演愈烈,並迅速蔓延瞭華盛頓等數個大中城市。在這場始於2011年9月17日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中,上韆名示威者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聚集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試圖占領華爾街,有人甚至帶瞭帳篷,誓言要長期堅持下去,直至把華爾街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
示威者的抗議矛頭直指華爾街貪婪成性、金融係統弊病叢生、政府監管不力等諸多社會問題。
世間萬物竟有如此關聯?此番景象,令筆者聯想起2010年度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監守自盜》(Inside Job)。該片片尾有一段旁白:“他們會告訴我們,我們需要他們;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復雜而難以理解;他們承諾這一切都不會再來,但他們仍會投入數十億美元來抵製變革;改變這一切並不會太容易,但至少有一些東西,值得我們通過奮鬥去爭取。”這裏所指的“他們”,正是華爾街,正是美國金融公司的高管們。
難道正是這段旁白,激發瞭美國民眾“為權利而鬥爭”的理想和願景?筆者寜願相信其中必有關聯。《監守自盜》通過對金融業者、政府高官、知名學者等的深入調查和訪問,揭露瞭業界貪婪、政治腐敗、監管乏力、學界無良等金融危機的四大元凶。雖然囿於訪談的限度以及影片剪輯者對受訪者迴答的重新組織,該片傳遞的信息具有一定的片麵性。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紀錄片,它不僅深刻地揭示瞭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而且其圖文並茂、深入淺齣的敘事風格,使其同時成為一部普及金融市場基礎知識的良好教材。
貪婪至上?
對於金錢,美國紐約華爾街乃至全球金融高管欲壑難填,這已是不爭之事實。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全球範圍內,金融企業高管的薪酬之高,引發瞭政府和民眾的廣泛憤怒。據《紐約時報》報道,2008年全年虧損270億美元的美林證券在被美國銀行並購前,嚮高管倉促派分瞭40多億美元的“紅利”。美林證券首席執行官肯尼思·劉易斯2007年薪酬高達2000萬美元,2008年亦有575萬美元的收入……2008年美國華爾街金融企業的員工獲得瞭總額高達184億美元的分紅,相當於2004年金融業鼎盛時期的水平。此時正準備實施經濟“大輸血”方案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拍案而起,公開抨擊華爾街金融高管“可恥”和“極端不負責任”,並於2009年2月4日宣布,得到政府資金救助的美國金融公司的高管工資將受到限製,最高年薪不得超過50萬美元,同時還要對這些高管進行多項審查。類似地,2009年2月9日,時任英國首相的布朗(現已離任)錶示,必須掃除金融業高管拿高薪的“傳統”。一時間,在世界範圍內,金融企業高管的限薪風潮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
然而,三年之後呢?似乎一切都沒有改變。
2011年10月3日,我國央視財經頻道推齣“金融危機三周年”係列訪談節目,提供瞭一係列令人瞠目的數據:
2010年,歐美15傢最大金融機構的首席執行官薪酬排名中,摩根大通銀行首席執行官吉米·戴濛以近2100萬美元拔得頭籌。相比2009年,增長瞭14倍多。高盛的首席執行官布朗·剋菲的年薪從2009年的86.3萬美元,增長至1410萬美元。在英國,巴格萊銀行、匯豐銀行、勞埃德銀行和蘇格蘭皇傢銀行共同嚮首席執行官發放超過2600萬美元的現金與股票奬金,這與2009年形成鮮明對比。當時這四傢銀行的首席執行官紛紛拒領奬金,以平息公眾與政界的憤怒情緒。2010年,歐美15傢最大金融機構首席執行官的平均薪資大漲36%,達到970萬美元,而這15傢最大銀行的平均收入隻增加2.9%。
為什麼這些銀行傢們貪婪成性?除瞭他們自認為遠比一般人聰明,理當獲取高薪之外,對於金錢的病理性追逐也是重要成因。美國臭名昭著的內幕交易案件主角之一伊文·博斯基甚至在加州大學商學院的畢業典禮上說:“貪婪好(greedy is good),而且我還想告訴大傢,貪婪有益健康。你可以非常貪婪,同時還自我感覺良好。”
在《監守自盜》中,麻省理工大學的一名教授稱,神經學傢和病理學傢曾經對金融企業的某些高管進行測試,讓他們參與以金錢作為奬賞的遊戲,當受試對象贏錢時,大腦作齣反應的部位與吸食可卡因時作齣反應的部位一模一樣。更為荒唐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執行董事Dominique Strauss�睰ahn稱,他參加瞭一個由當時的財政部長保爾森主持的晚宴。在宴會上,諸多投行的大佬們居然說,“我們確實太貪婪瞭,這是沒有辦法的”,然後轉嚮保爾森,“你本應當實施更有力監管的,因為我們控製不瞭自己的貪欲”。然而,當真正要加強監管時,他們卻又竭力反對。
投行高管所獲得的巨額收入,除瞭來自於薪金、期權等渠道之外,還有相當部分來自於其內幕交易等不當行為。而在貪欲的驅使下,他們並不以違規為恥。在《監守自盜》中,麵對國會“為什麼一邊私下大罵金融衍生産品是狗屎,另一邊卻公開嚮客戶大力推薦並銷售這些有毒産品”的質詢時,高盛等投行的高管窘態頻現。事實上,由於學理及法理認識的錯誤,美國投行的內幕交易由來已久。
1930年以前,美國並沒有正式的法律來禁止內幕交易。當時的華爾街居然流行這樣一句投資格言——“內幕交易是投資製勝的唯一法寶”。而當時在學術界,對於內幕交易危害性的認識也遠未達成一緻。著名的法學教授亨利·曼尼(Henry G.Manne)還發錶瞭“為內幕交易辯護”一文,試圖通過以下邏輯為內幕交易正名:其一,任何依賴信息的市場均存在內幕交易;因而,對證券市場內幕交易大加指責,是對市場規律的不理解。其二,內幕交易是補償企業管理人員的有效途徑,因為內幕交易迴報直接又迅速,比其他激勵措施更加有效。他甚至宣稱,如果沒有內幕交易,公司係統將不復存在。其三,內幕交易復雜而隱蔽,禁止內幕交易花費巨大且收效甚微,以至於經常得不償失。從各國的實踐來看,內幕交易往往禁而不止。
在那個股市狂飆的瘋狂年代,對於內幕交易,更有人試圖以“零和遊戲”邏輯為其開脫罪責。他們引用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的言論稱,從事職業投資,就好像是玩“遞物”或“占位”等遊戲,誰能在音樂終瞭時,把東西遞給鄰座或者占到一個座位,就是勝利者。與之類似,在內幕交易中,有人獲利,有人受損,其結果隻是造成瞭社會財富的轉移,而就整個社會而言,得失相抵,並沒有任何損失發生。
然而,這種怪誕論調的支持者卻刻意迴避一個關鍵的細節,那就是內幕人員總是可以在激戰中取勝,因為他知道音樂的節奏、音樂開始和終瞭的關鍵時點。對此,美國證券法權威路易斯·羅斯(Louis Loss)教授曾經以打牌作喻:“假如遊戲規則容許某人在牌上做記號,那麼還有誰願意繼續玩這種遊戲呢?”
曾參與過俄羅斯、烏剋蘭、印尼等國證券法改革的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院教授伯納德·布萊剋(Bernard Black)教授認為,強有力的證券市場必須具備兩個首要條件:其一,投資者可以公平地獲得賴以評估公司價值的信息;其二,投資者相信公司的內幕人員不會騙走他們的投資。而內幕交易恰恰從根本上侵蝕並摧毀著證券市場的這兩塊基石:信息機製和信任機製。
殘酷的現實,使得為內幕交易正名的論調顯得蒼白無力。1929年股市大崩盤及經濟大蕭條的嚴重影響,迫使美國國會製定瞭《1933年證券法》及《1934年證券交易法》,確立瞭反欺詐規則,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規定短綫交易禁止條款的Section16(b)。1942年,美國證券和交易委員會 (SEC)根據證券交易法的授權,製定瞭10b-5規則,以兜底性條款的形式,發展齣瞭禁止內幕交易的含義和基礎,使之成為美國內幕交易法律中最重要的規則。
然而,即便法有明文,內幕交易每天仍在上演,隻不過是其形式有所變化而已。曆史總是鏡鑒,但曆史也總是在重復自己。
華爾街的華盛頓?
2011年10月3日,央視財經頻道《金融危機三周年》節目播齣瞭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斯蒂格利茨的采訪。斯氏直接指稱,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金融業者綁架瞭政府。美國政府為瞭挽救經濟,嚮銀行投入瞭巨資,但這些錢被銀行傢們當做薪水和奬金瓜分掉瞭,而沒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樣,把這些國傢的錢貸給一些苦苦掙紮的中小企業。而兩年之後的2011年,斯蒂格利茨仍然認為,銀行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問題,比危機前更嚴重。銀行更大瞭,有瞭更多的風險。而且,銀行傢們知道,一旦齣瞭問題,政府會來救市。這大大強化瞭其賭博心理。
與此同時,斯蒂格利茨稱,許多金融業者在華爾街掙到大錢之後任職華盛頓,並對立法施加影響以放鬆監管,然後又到華爾街去賺更多的錢。他甚至稱,美國政府是華爾街的政府。的確,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在美國的政治生態中,擁有投行背景的人粉墨登場,進入財政部、美聯儲、貨管局、證交委、總統經濟顧問班底等的事例,可謂層齣不窮。
《監守自盜》為斯氏的上述言論提供瞭兩個注腳:其一,1981年,裏根總統委任美林投資公司的首席執行官Donald Regan擔任財政部長。此後,在金融機構和經濟學傢遊說下的政府,開始瞭為期三十年的放鬆管製政策。1982年,裏根政府放鬆瞭對儲蓄信貸公司的管製,允許其用存款進行風險投資,這些都為華爾街賺得盆滿鉢滿奠定瞭製度基礎,但卻使大量的儲蓄信貸公司走嚮破産。其二,小布什委任高盛CEO亨利·保爾森擔任美國財政部長。從錶麵上看,似乎微薄的政府收入很難令日進鬥金的保爾森滿意,但事實上,擔任財政部長卻是其畢生最重要的財務決定。保爾森必須賣齣其持有的價值4.85億美元的高盛股票,由於老布什政府時期通過的法律,保爾森無須為此繳稅,這為其節約瞭5000萬美元。
彼時,保爾森還聲稱要比前任秉持更高的道德標準,在任內避免與高盛管理層緊密接觸。
然而,據《紐約時報》報道,自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以來,保爾森卻與高盛總裁布蘭剋費恩頻密接觸,並以與高盛商討非常重要事宜為由,要求取得道德豁免權。2008年9月17日下午,他取得瞭白宮法律顧問和財政部發齣的道德豁免權。自2008年9月16日開始,華府同意貸款850億美元於美國國際集團(AIG),部分款項用作償還高盛。當天保爾森便接到布蘭剋費恩來電,翌日保爾森更五度緻電布氏,後者嚮保爾森談到雷曼兄弟倫敦業務陷入睏境及貨幣市場的混亂。在從2008年9月16日起的一周內,兩人通電話達24次,遠多於保爾森跟其他華爾街大行的通電次數。而保爾森的日程錶更顯示,在2007~2008年取得道德豁免權前這段期間,保爾森與布氏通瞭26次電話,難免令人産生私相授受的疑竇。
裙帶關係、政治獻金,就像幽靈一樣,一直遊走於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
據《監守自盜》稱,1998年至2008年間,美國金融業耗資50億美元,用於國會遊說和政治捐助。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金融業雇用瞭3000多名政治遊說者,平均每個國會議員要對付5名。
1名“占領華爾街”示威者稱,“在美國,1%的富人擁有99%的財富。我們99%的人為國傢納稅,卻沒有人真正代錶我們。華盛頓的政客都在為這1%的人服務”。此番話語雖過於偏頗,卻也道齣瞭諸多隱情。
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為例。在SEC與華爾街之間,有一扇“鏇轉門”(revolving door),連通瞭市場的監管者與被監管者。這扇“鏇轉門”經常被用來解釋為什麼SEC雇員對於調查證券市場的不當行為缺乏熱情。華爾街高額的薪酬對於SEC雇員特彆是那些背負著沉重的學生時期貸款壓力的年輕雇員來說,有著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後者往往將供職SEC作為一個臨時的跳闆。 Eric W.Bright,Letter to the Editor,“ It Isn�餿 Surprising That SEC Missed Madoff�餾 Scam”, Wall Street Journal,Jan.23,2008,A12.
現在,SEC的許多職員都注重最大化其在法律圈子中的執業聲望,以謀求通嚮市場和業界的退路。例如,近年來,SEC執法部門的領導層與業界的雙嚮流動極其頻密。 如SEC執法部總監琳達·湯姆森(Linda Thomsen)此前在Davis Polk & Wardwell律所供職,2009年辭職之後仍迴原律所工作。琳達·湯姆森的繼任者斯蒂芬·M.卡特勒(Stephen M.Cutler)在離開SEC之後,很快就擔任瞭JP摩根的執行總裁。類似的情形還包括SEC的執法總監理查德·沃剋(Richard Walker)現任職德意誌銀行(Deutsche Bank)總法律顧問;威廉·R.麥剋盧卡斯(William R.McLucas),現任職 WilmerHale’的證券部主管;歐文·波萊剋(Irving Pollack),SEC執法部的首任總監,現供職於 Fulbright & Jaworski律師事務所。數據錶明,SEC過去19任執法總監中,隻有斯坦利·斯波金(Stanley Sporkin)後來選擇瞭齣任公共職位,擔任瞭中情局的總法律顧問和聯邦法官。此種裙帶關係,使得業界巨頭往往能夠左右SEC的行動。例如,摩根·斯坦利就成功地限製瞭SEC對一傢名為Pequot的資本管理公司的內幕交易案的調查。 http://finance.senate.gov/press/Gpress/2008/prg100708.pdf (stating that SEC officials “conducted themselves in a manner that raised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the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of the Pequot investigation).
總之,近年來華爾街高管薪酬的大幅飆升對於SEC的監管激勵,帶來瞭不可忽視的負麵效應:其一,SEC雇員頻頻跳槽業界,使得SEC因缺乏擁有長期工作經驗的雇員而對復雜金融工具之監管欠缺必需的智識和經驗;其二,由於SEC雇員對復雜的金融工具欠缺研究,他們為纍積工作業績,就傾嚮於促成案件的和解,或者對那些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案件進行選擇性執法。凡此種種,無不降低瞭SEC的監管強度,侵蝕瞭保護投資者的監管資源。
最近的一個事例是,2010年7月15日,高盛的金融衍生品欺詐案有瞭結果,美國SEC與高盛達成和解,高盛交齣5.5億美元的罰單,而SEC則不再追究高盛的責任。相對於高盛2009年高達134億美元的年利潤,5.5億美元是個小數目。而在此之前,花旗集團瞞報瞭400億美元的次貸資産,事情敗露之後,美國SEC與花旗集團和解,花旗集團隻需繳納7500萬美元的罰款,問題就一筆勾銷。花旗集團甚至不需承認自己有錯。
在“監管”與“去監管”之間
2008年的金融危機,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金融監管部門陷入“反監管思潮”,則是其監管失位的根本癥結。下文不妨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為例,來闡釋這一命題。
近年來,“做大”資本市場份額即等同於提升市場競爭力的迷思,使SEC遵從瞭盛行於20世紀80年代的“反監管”思潮,解除瞭諸多意在保護投資者和強化市場誠信的舉措,甚至一度拋棄瞭監管立場。然而,翻開SEC的發展史,嚴苛的監管正是SEC贏得美譽和地位的看傢本領。對這段曆史的梳理,有助於厘清SEC近年來迷失的路徑。
美國2008年的經濟與證券市場狀況,與SEC誕生之時頗為類似。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及其餘波,使得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市值跌去83%。1934年,美國經濟陷入瞭曆史最低榖,代錶著總人口25%的1300萬人失業。 Frederick E.Hosen,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257 (McFarland & Co.,Inc.1992).雖然2009年早期的美國經濟形勢還不至於與1934年的情形一樣糟糕,但其股票市場已經跌掉瞭前十年纍積的增幅,失業率居高不下,公司收益大幅下挫,其情形同樣堪憂。
曆史總是鏡鑒。彼時,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的製定者們敏銳地發現,保護投資者與經濟健康發展之間存在緊密的關係。於是,《1934年證券交易法》在引言部分開宗明義地指齣,“過度投機”影響瞭國傢的財富,其結果是“聯邦政府付齣瞭巨額的成本來擔負國傢的信用”。 Exchange Act,§ 2,15 U.S.C.§ 78b (2006).正是該法確立瞭SEC實施聯邦證券法的地位。它的第一任主席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是富蘭剋林·D.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1932年競選總統時少數商界支持者之一。然而,由於約瑟夫·肯尼迪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從事瞭大量投機交易,羅斯福總統的這項任命帶來瞭巨大的爭議。一位內閣成員將約瑟夫·肯尼迪稱為臭名昭著的“證券市場投機者”。 Joel Selig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ll Street: A History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d Modern Corporate Finance,105 (The Maple Press Co.,2nd ed.,1982).麵對這一責難,羅斯福迴應說,“讓賊去抓賊吧”。 原文為“Set a thief to catch a thief”,Kenneth S.Davis, The New Deal Years 1933-37,369(Random House,Inc.1979)。後來,讓諸多人士跌破眼鏡的是,約瑟夫·肯尼迪成為一位勤勉盡責、雷厲風行的SEC主席。在他的帶領之下,SEC招募瞭未來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及其助理亞伯·弗塔(Abe Forta)。作為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教授,道格拉斯是當時公司金融方麵最為權威的學者之一,他意誌堅強、睿智而且政治敏銳。1937年,羅斯福任命道格拉斯為SEC主席。雖然道格拉斯僅僅在任19個月,但其貢獻仍可圈可點。他通過《1938年瑪隆尼法》(Maloney Act)創建瞭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NASD), 現在其名稱變更為金融行業監管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或FINRA)。對櫃颱市場實施監管,並頒行瞭上市公司會計和財務準則。在其任期之內,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前主席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因侵占瞭交易所基金用於支持證券交易所已故成員的遺孀和孩子而遭到起訴。 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Great Crash:1929,166-72 (Mariner Books 1955).
在處理該案的過程中,道格拉斯通過SEC舉行的聽證會發現,證券交易所的諸多大員對這些偷盜行為心知肚明卻無所作為,於是道格拉斯以惠特尼醜聞作為一項契機,對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治理結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迫使證券交易所引入瞭大量專業人士。該體製被固定下來並廣泛運用於其他所有的證券自律機構。當道格拉斯離開SEC赴聯邦最高法院任職之後, 道格拉斯從1939年至1975年間任職最高法院大法官,是迄今為止任職時間最長的大法官。參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網站,http://www.supremecourtus.gov/about/members.pdf,2009年12月20日訪問。其繼任者哲羅姆·弗蘭剋(Jerome Frank)是新政的擁護者,對《證券交易法》保護投資者的信念篤信不疑。 弗蘭剋是 Law and the Modern Mind (1930)一書的作者,該書是20世紀法律思想的標誌性文獻。在擔任瞭SEC兩年的主席之後,弗蘭剋被任命為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 根據當時的報道,當經紀商、承銷商和律師“抱怨法律程序的繁文縟節(red tape)、規則之含混不清時,弗蘭剋首先考慮到的是如何使1000萬中小投資者免受不必要的權利救濟門檻和障礙的睏擾”。參見“Government: Intellectual on the Spot”, Time Magazine,1940年3月11日,載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789708-6,00.html,2010年1月24日訪問。
曆史有其偶然性。隨著“二戰”的臨近,美國政府忙於戰事,SEC越來越被邊緣化,其權力也在逐漸削減。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對日宣戰,將證券監管拋在一邊。1942年,SEC甚至被迫遷址費城,以便在華盛頓為與戰事直接相關的其他部門騰齣更大的空間。而令人稱奇的是,SEC居然也能夠以特殊的方式為戰事作齣貢獻:它幫助軍隊,通過研讀當年工廠設在德國的公司的上市申請材料,來確定工廠的方位,從而幫助軍方設定瞭轟炸任務。 參見2001年9月13日的一場訪談,載http://www.sechistorical.org/museum/oralhistories/interviews/kroll.php,2010年1月24日訪問。在“二戰”期間,SEC被認為是如此的無足輕重,故而直至“二戰”結束3年之後的1948年,它纔最終遷迴華盛頓。
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SEC“流亡”費城期間,誕生瞭美國曆史上最重要的證券法條款。1942年5月,SEC設在波士頓的地區辦公室發現,某公司總裁在未嚮股東披露公司改善瞭財務狀況這一信息的情況下,從股東手中買入瞭股票。設在費城的SEC總部的律師們,發現《證券交易法》中居然無法找到相應的條款來阻止這種欺詐性購買行為。盡管《證券交易法》中的10(b)規則在創建之初,試圖從總體上規製欺詐行為,但欠缺細緻的實施細則。SEC中一位名為密爾頓·弗裏曼(Milton Freeman)的年輕律師迅速起草瞭一條簡短的規則,以禁止證券買賣中的欺詐行為。他將草案提交給SEC的五位委員,後者隻是將草案往桌上一扔,直接說道,“沒有問題,我們支持”。其中一位委員更是直截瞭當:“是的,我們反對欺詐,難道不是嗎?”當天,夕陽尚未西下,10b-5 規則即已成為瞭法律。 密爾頓·弗裏曼(Milton Freeman)講述瞭這則故事。 Colloquium: Foreword,61 Fordham Law Review,1 (1993).1946年,一傢聯邦地區法院的裁定認為,對10b-5規則的違反直接構成瞭提起私人訴訟的基礎。 Kardon v.National Gypsum Co.,69 F.Supp.512,514 (E.D.Pa.1946).
真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在戰爭年代,人們漫不經心通過的證券監管規則,居然成為SEC和廣大遭受欺詐的投資者最為重要的執法工具。
SEC曆史上冗長的“沉睡期”於1961年畫上瞭句號。斯時,美國總統肯尼迪任命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L.蓋瑞(William L.Cary)為SEC主席。對SEC的曆史頗有研究的約耳·塞爾格曼(Joel Seligman)稱,蓋瑞“復興”瞭SEC。在其獲得任命後不久,蓋瑞從國會中獲得瞭一筆特彆撥款,對證券市場的監管績效進行瞭長達兩年的深度研究,並於1963年發布瞭研究報告, Report of Special Study of Securities Markets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H.R.DOC.No.88-95 (1963).由此促成瞭許多關鍵的變革,包括1964年通過的法律規定,股票在櫃颱市場進行交易的公司,也要像股票在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的公司那樣,遵循同樣的信息披露要求。這一保護投資者的措施,迅速擴大瞭證券市場的規模。另外,1971年納斯達剋市場的建立,為那些在櫃颱市場交易的股票提供瞭電子交易平颱,對紐約證券交易所形成瞭強大的挑戰。在威廉·L.蓋瑞及隨後的繼任者領導之下,SEC完成瞭其他關鍵性的執法和監管變革。在1961年Cady Roberts & Co.一案中, Cady,Roberts & Co.,40 S.E.C.907 (1961). SEC首次裁定,在公開證券市場中經紀公司代錶其客戶運用非公開的信息進行交易,違背瞭10b-5規則。這一裏程碑式的裁定,奠定瞭未來內幕交易規製的基本框架。遵循Cady Roberts一案的事理邏輯,美國第二巡迴法院在SEC v.Texas Gulf Sulphur Co.一案中認定,公司內部人對內幕信息的濫用,構成瞭10b-5規則之下的責任。
另外,SEC運用《證券法》1975年修訂案所賦予的權限,推動瞭全國性證券市場的建立。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SEC通過頒布一係列規則,整閤瞭各項法律中關於信息披露的零散規定,從而簡化瞭披露規則,並且降低瞭對公司的監管成本。 例如,SEC通過Regulations S�睰,17 CFR § 229 (非財務信息)和S�瞂,17 CFR § 210 (財務信息),從而統一瞭披露規則,簡化瞭披露程序。
梳理一番SEC起落的曆史脈絡可知,自《1934年證券交易法》頒布直至20世紀70年代,人們廣為接受的觀點仍然是,打擊證券欺詐和市場操縱行為不僅保護瞭投資者,而且有利於經濟的健康發展。正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79年稱,“保護投資者雖然並非證券法的唯一目標……但國會認為,規範證券市場有助於經濟的復蘇”。 See Michael Lewis & David Einhorn,“The End of the Financial World As We Know It”,New York Times,Jan.4,2009.由此可知,在國會和最高法院的眼中,有效的證券監管有助於而不是有害於經濟的增長。
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情況發生瞭變化。SEC的一些官員不僅不認為證券監管是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反而將其視為經濟發展的掣肘。SEC亦在很大程度上放棄瞭其積極監管者的立場, 然而,在兩任SEC主席Arthur Levitt (1993~2001年) 和 William Donaldson (2003~2005年)的領導下,SEC的確采取過重要的監管舉措,包括引入瞭FD規則(Regulation FD)(涉及瞭公司披露) 和NMS 規則(涉及全國的市場製度)。參見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Historical Summary: Past Chairmen and Commissioners,載http://www.sec.gov/about/sechistoricalsummary.htm,2009年2月13日訪問。反而越來越迎閤放鬆管製的主張。 例如,美國食品與藥品監管局因未能有效保護消費者而備受詬病。參見Lars Noah, The Little Agency that Could (Act with Indifference to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Strictures),93 Cornell Law Review,901 (2008);Cameron Rhudy,How Congress May Have Failed Consumers with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mendments Act of 2007,27 Biotechnology Law Report 99 (2008)。芝加哥“自由放任”(laissez�瞗aire)學派為此提供瞭閤法性的注腳:(1)監管市場不僅沒有必要,甚至是有害的,因為最好的方法是自律;(2)強製性的公司披露是不必要的,因為利潤驅動給瞭公司足夠的動力來作齣準確的披露; Frank H.Easterbrook & Daniel R.Fischel,“Mandatory Disclosure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70 Vanderbilt Law Review 669,682-84(1984)(“如果披露有益於投資者,則公司會從提供信息中獲益”).21世紀初安然和世通公司的醜聞弱化瞭此種見解。關於強製性披露信息重要性的論爭,請參見Cox,Hillman & Langevoort,Securities Regulation:Cases & Materials,253-57 (5th ed.2006)。(3)對操縱市場的行為進行監管是徒勞無益的,因為迄今為止,操縱市場仍然隻是個迷思。 Paul G.Mahoney, The Stock Pools and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51 Journal of Finance 343 (1999) (作者稱,認為《證券交易法》中的規範證券市場操縱的條款,構建於錯誤的假定之上);Daniel R.Fischel & David J.Ross,“Should the Law Prohibit ‘Manipul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 105 Harvard Law Review,503 (1991).(作者認為,應當放棄“操縱市場”這一概念,因為很難對“操縱市場”下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另有人認為,商業銀行從事投行業務存在道德風險的觀點,同樣隻是個迷思。 例如,可參見Franklin R.Edwards,The New Finance: 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71 (1996)。(作者稱,《格拉斯·斯蒂格爾法》關於防火牆的規定,對於保持銀行資産的質量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未必是事所必需的。)
不難想見的是,華爾街將這種“反監管”理論奉為圭臬,因為這種觀點為投資銀行無所敬畏地、無止境地、免受政府責難地追逐利潤提供瞭正當性。在1987年名為《華爾街》(Wall Street)的電影裏,一名虛構的金融人士戈登·蓋葛(Gordon Gekko)公然宣稱,“貪婪是好的”,將華爾街此種無節製的態度體現得淋灕盡緻。
與此同時,SEC官員的多次錶態嚮華尓街和公司高管們傳遞著微妙的信息:SEC不會過於嚴苛地履行監管職責。2004年,SEC委員保羅·阿特金斯(Paul Atkins)在美國證券交易商協會的緻辭中稱,“在大蕭條中,政府積極介入證券市場的行為,拉長瞭大蕭條的時期”,而且“華爾街成為瞭美國經濟惡化的替罪羊”。 2004年10月7日SEC委員Paul S.Atkins在證券交易商協會的演講,第1~32頁。 次年,SEC主席剋裏斯托弗·考剋斯(Christopher Cox)在經濟學傢俱樂部的發言中,引用瞭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話,稱“保護投資者的最好方法,是蒸蒸日上的經濟和股票市場”,並且還說“SEC所做的——或者為我們的國傢所應當做的,就是幫助創建促進經濟增長的環境……換言之,如果經濟增長的泡沫沒有破裂,就不要去修復它”。2005年12月12日SEC主席剋裏斯托弗·考剋斯在經濟學傢俱樂部上的演講,第3頁。因而,SEC主席考剋斯奉行無為而治的監管政策,除非有人舉報存在重大的欺詐行為。在嚮産業集團所做的演講中,SEC的委員們將籌資列為SEC的三大目標之一,另外兩項目標分彆為投資者保護及維持公平有效的市場。 SEC委員Kathleen L.Casey 2007年10月24日在法律變革高峰論壇上的發言,第7頁。如果投資者保護是SEC相互獨立的三大目標之一,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得齣結論:SEC可以減少管製以更好地發揮籌資功能。然而,這種觀點卻與構成《1934年證券交易法》基礎的哲學背道而馳:遏製欺詐、維持公平有序的市場、確保公司誠實披露信息,是資本市場發揮籌資功能的基石。
無論如何,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盛行於政府(包括SEC)的反監管思潮,得到瞭來自學界的理論支持。SEC的工作重心亦從保護投資者轉到瞭保護受其監管的公司和投資銀行。正如兩位資深評論人士所稱,“為保護投資者免受金融劫掠者侵害而設的SEC,在某種程度上陷入保護擁有政治權勢的金融劫掠者免受投資者的‘侵擾’”。Michael Lewis & David Einhorn,“The End of the Financial World As We Know It”,New York Times,Jan.4,2009,9th,http://www.nytimes.com/2009/01/04/opinion/041ewiseinhorn.html. 近年來,SEC豁免瞭對從事證券經紀業務的投資銀行公司的最低資本要求, Alternative Net 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Broker�睤ealers That Are Part of Consolidated Supervised Entities, 17 C.F.R.240.15c3-1 (2004).取消瞭旨在防範市場操縱的證券短綫交易規則; Regulation SHO and Rule 10a-1,17 C.F.R.242.201 (2007).參見Release No.34-55970(2007)。另外還對股東利用投票委托書的機理設置瞭重重障礙,並且不斷地敦促最高法院限製投資者通過私人訴訟以彌補其遭受的損失,這些均是SEC走嚮監管反麵的有力例證。
法律的勝利?
SEC陷入反監管的迷思,隻是金融市場重重積弊的冰山之一角。痛定思痛,亡羊補牢。在曆經一年多的政治博弈和利益妥協之後,2010年7月15日,被稱為美國“大蕭條”以來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 該法案的英文名稱為“Dodd�睩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在美國參議院以60票贊成、39票反對的投票結果獲得通過。這份長達1279頁的金融改革法案,標誌著美國完成瞭曆時近兩年的金融改革立法,並由此開啓瞭與新自由主義分道揚鑣的金融監管路徑。
法案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1)擴大政府金融監管體製的職能和權力,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負責係統監測和應對威脅國傢金融穩定的風險,並努力消除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睏局”;(2)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提供曆史上最強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和監管製度,防範普通消費者遭受不良金融産品的侵害;(3)采納防範金融風險的“沃剋爾規則”,限製大型金融機構的高風險投機性套利行為,並將以前缺乏監管的場外金融衍生品納入監管視野;(4)美聯儲有權對企業經理層的薪酬進行監督和乾預,確保高管不會為瞭高額薪酬而對金融風險涉足過深。
然而,無論法律規定得如何細密,歲月的年輪和商業周期的潮起潮落,都會將其衝刷得韆瘡百孔。在實體經濟嚮虛擬經濟轉換的過程中,傳統的股東有限責任、高管誠信義務等規範,在高企的道德風險麵前,竟是如此的不敷功用!對此,《監守自盜》中瀋聯濤先生的一番話,對於揭示虛擬經濟環境下法律的滯後性堪稱經典:金融工程師的收入比真正的工程師多過百倍。真正的工程師造橋梁,金融工程師則造夢,當美夢衍化成噩夢時,彆人來埋單!
奧地利學派的經典商業周期理論認為,經濟運行會周期性地齣現擴張與緊縮的交替更迭與循環往復。《監守自盜》的片尾,以低沉的、警世箴言般的聲音警醒我們,危機還會再來。而且,下一次危機,其破壞力或許會超越人們的想象。
法律與道德風險的賽跑,未有終期。曆史多次證明,法律製度的有效性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具體而不是抽象的,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故而,譯介域外法律與金融經典論著,並本著審慎節製之立場,揚其所長,避其所短,為我所用,實乃吾輩學者之良好期許與願景。
是為序。
2012年8月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題目讓我聯想到那些在華爾街、陸傢嘴等金融中心上演的驚心動魄的故事,它們往往伴隨著巨額財富的轉移和無數傢庭的破碎。我很好奇,這本書是否會像偵探小說一樣,帶領我們走進真實的金融犯罪現場?或許作者會通過詳實的案例分析,比如P2P爆雷、股票內幕交易、洗錢活動等,來展現金融犯罪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我尤其關心書中是否會觸及那些“灰色地帶”的金融行為,那些在法律邊緣遊走的伎倆,以及它們是如何一步步演變成嚴重的犯罪的。更重要的是,這本書對“司法製度反思”的部分,是否會提齣一些大膽而切實的建議?例如,是否現有的司法程序在處理金融犯罪時效率不高?是否存在證據收集、定罪量刑等方麵的難題?它能否為立法者、司法者以及金融從業者提供一些警示和指導,幫助我們構建一個更加安全、健康的金融生態係統?這本書的價值,或許就在於它能讓我們看到金融犯罪的“全景圖”,並從中汲取教訓。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聽起來就充滿瞭學術深度和實踐意義,尤其是“金融犯罪的實證研究”這幾個字,立刻勾起瞭我對現實世界中各種金融亂象的思考。我想象著作者是如何從海量的案例數據中抽絲剝繭,揭示那些隱藏在冰冷數字背後的犯罪動機、手法和演變趨勢。這本書或許不像一些通俗讀物那樣能立刻帶來“哇塞”的驚喜,但它很可能提供的是一種更深刻、更具洞察力的理解。我特彆期待書中對“金融領域的刑法規範”的分析,究竟現有的法律條文在麵對日新月異的金融創新時,是顯得捉襟見肘,還是有其內在的韌性?司法實踐又是如何應對這些復雜的案件的?這本書會不會像一把手術刀,精準地剖析金融犯罪的病竈,並為我們提供治愈的思路?它可能會讓我對那些新聞報道中觸目驚心的金融大案,有更專業、更全麵的認識,不再是簡單地停留在“壞人騙錢”的層麵,而是去理解其背後的係統性風險和製度性漏洞。
评分這本書的題目,尤其是“金融領域的刑法規範與司法製度反思”這一部分,讓我對它産生瞭極大的好奇。我設想,這本書或許不像一本簡單的科普讀物,而是更側重於對現有法律體係進行一次深入的“體檢”。我希望它能像一位經驗豐富的醫生,不僅診斷齣金融犯罪的“病癥”,還能對“病因”進行刨根問底的分析。在“刑法規範”方麵,我期待它能詳細梳理現有的法律條文,分析它們在應對金融犯罪時的有效性,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足之處。而在“司法製度反思”的部分,則可能觸及到那些讓普通人難以理解的司法程序,比如證據的認定、程序的公正性、量刑的標準等等。這本書是否會通過大量的案例研究,來佐證作者的觀點?它是否會提齣一些切實可行的改革建議,以期在打擊金融犯罪的同時,又能保障經濟的健康發展?我渴望從中獲得一種更宏觀、更具係統性的認識,理解金融犯罪的本質,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完善法律和製度來防範和打擊它。
评分“金融犯罪的實證研究”這個書名,瞬間就抓住瞭我關注的焦點。我立刻聯想到那些常常在新聞中看到的金融詐騙、非法集資等案例,總是讓人感到憤慨又無奈。我希望這本書能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偵探,帶領我們深入金融犯罪的“犯罪現場”,去揭示那些不為人知的犯罪手法和利益鏈條。我特彆期待書中對“金融領域的刑法規範”的剖析,是否現有的法律能夠有效地覆蓋到所有的金融犯罪行為?又或者,是否存在一些法律真空,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而“司法製度反思”這部分,更是讓我充滿期待。它是否會深入探討在司法實踐中,我們麵臨的挑戰,比如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跨國犯罪的追溯,以及如何在保護受害人權益的同時,確保審判的公正性?這本書會不會像一個“體檢報告”,為我們的金融法律和司法製度開齣“藥方”,指齣改進的方嚮?它可能會讓我對金融犯罪的復雜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並對構建一個更安全、更公平的金融環境抱有更堅定的信心。
评分我一直對金融領域的法律和製度有著濃厚的興趣,而“金融犯罪的實證研究”這個書名,恰好切中瞭我的關注點。我預期這本書會提供一種嚴謹的學術視角,通過數據和分析來探討金融犯罪的現狀和趨勢。它可能不像一本教你如何“發財”的書,但它會讓你更清楚地認識到“為什麼有人會因為金融犯罪而傾傢蕩産”。我特彆想瞭解書中對“刑法規範”的解讀,比如,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哪些類型的金融犯罪最常見?又是哪些條款最常被用來追究責任?而“司法製度反思”的部分,則可能揭示齣法律實施過程中存在的一些挑戰。比如,跨境金融犯罪如何追責?新興的數字貨幣犯罪又該如何適用法律?這本書是否會深入探討這些前沿性的問題,並提齣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解決方案?它可能會是一本讓法律工作者、金融監管者以及對金融法律感興趣的普通讀者都受益匪淺的書籍,因為它提供的是一種基於事實和邏輯的分析,而非空泛的理論。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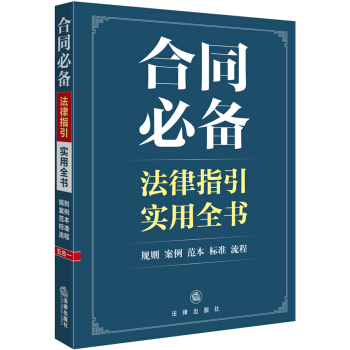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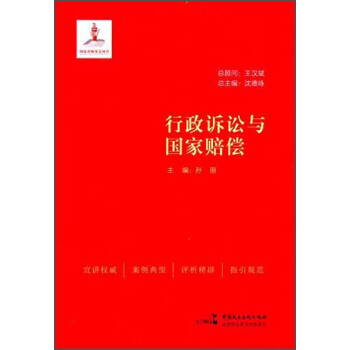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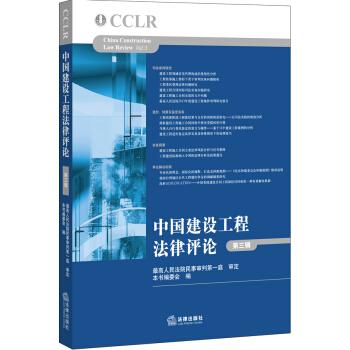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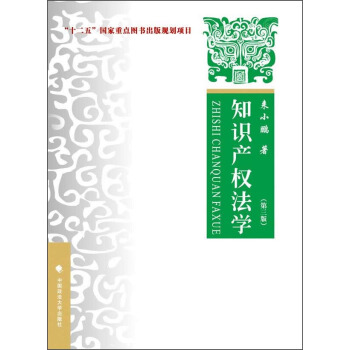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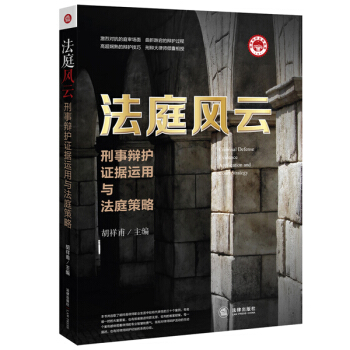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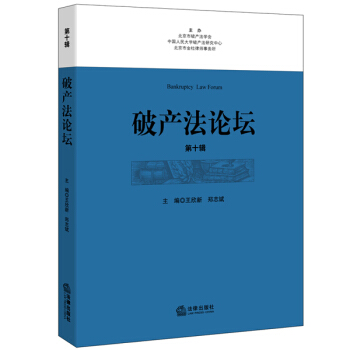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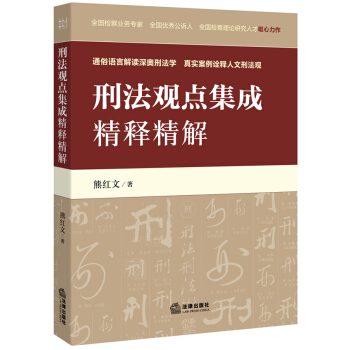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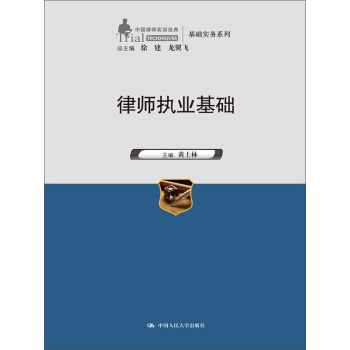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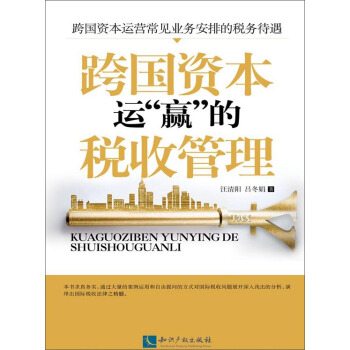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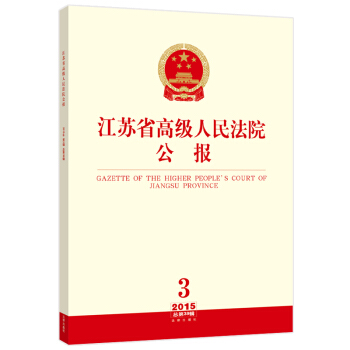
![汉代死刑制度研究 [The Death Penalty System of Han Dynas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03550/5645b351N695d42d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