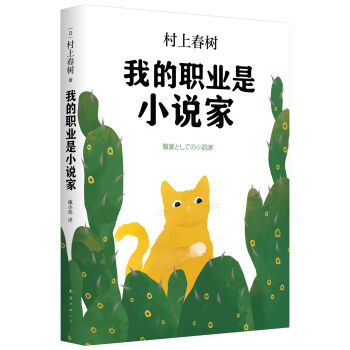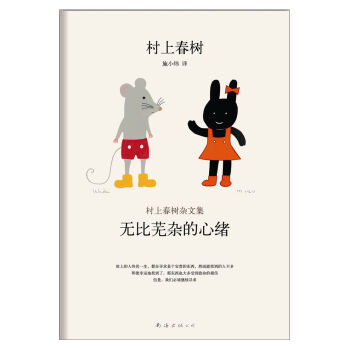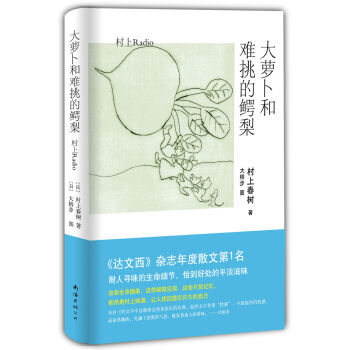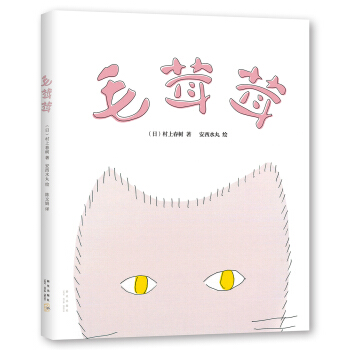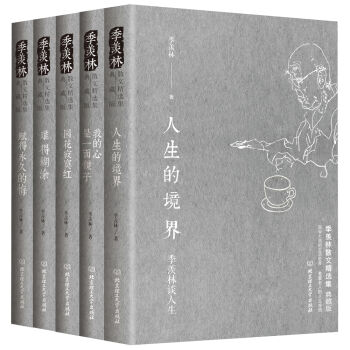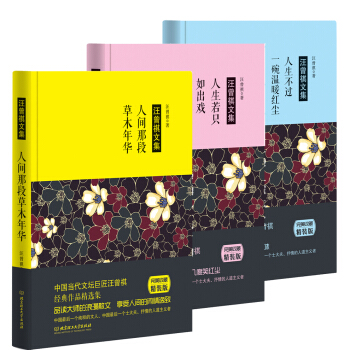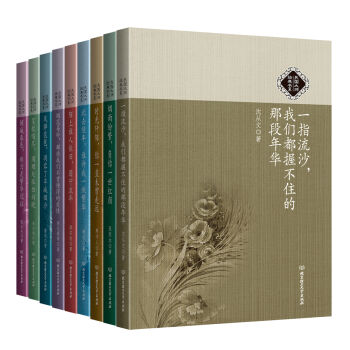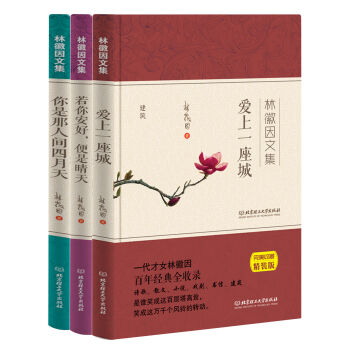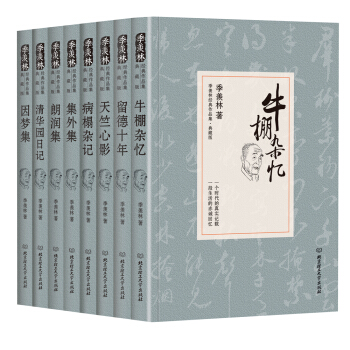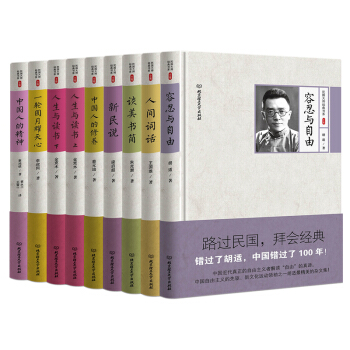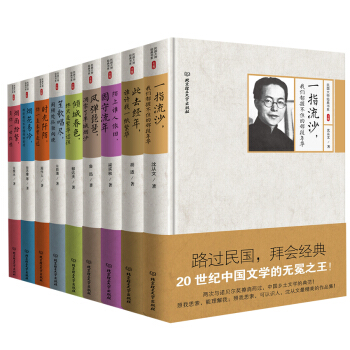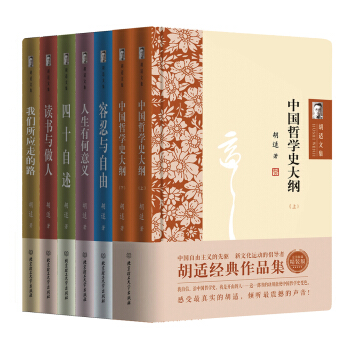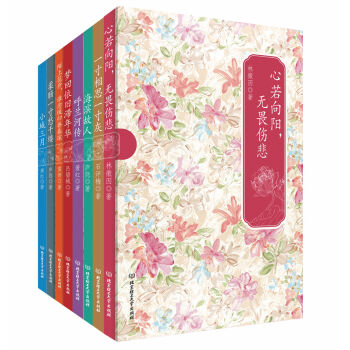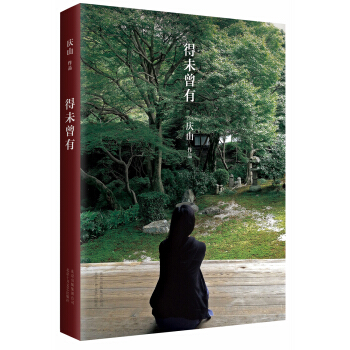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白說》是白岩鬆繼《幸福瞭嗎》《痛並快樂著》後又一部百萬級熱銷書。為方便讀者閱讀與攜帶,《白說》(清新版)正式齣版。本書內容為近十年白岩鬆於各個場閤與公眾的深入交流,其中多個篇章為內部講座,首度公開。白岩鬆自稱:“它比紙上的履曆更為真實地記錄瞭心靈的履曆。”在書中,白岩鬆坦言作為新聞評論員的艱難,但憑藉勇敢、敏銳和方嚮感他總能智慧地消解。在對峙與分裂的時代,白岩鬆選擇站在中間,並且通過這本書,不遺餘力地嚮人們傳遞“AB麵”的價值觀。成功與失敗,有用與無用,短跑與長跑,新聞與曆史……這些看似對立的詞匯,卻無不存在著內在的關聯與相互轉化的可能。在常識泛濫,理性缺乏的當下,白岩鬆溫暖發聲,理性執言。傳遞齣一種既融入時代、又齣離時代的態度。
然而,白岩鬆自帶犀利,不懼爭議,在有權保持沉默的年紀拒絕沉默,為依然熱血有夢的人們敲鼓撥弦。他直言“說話不是件好玩的事兒”,如果能“說齣一個更好點兒的未來”,就算“說瞭也白說,但不說,白不說”。
內容簡介
《白說》是央視知名主持人、資深評論員白岩鬆的一部極具影響力的演講精選集。時間跨度近十年,內容涉及時政、改革、公益、慈善、教育、體育、音樂、閱讀、人生等多個方麵。篇章包括《漂亮的失敗是另一種成功》《今天的新聞是明天怎樣的曆史》《做點無用的事兒》《資訊爆炸時,彆被忽悠瞭》《中國人不缺德,可是缺啥》《好醫生一定會開“希望”這個藥方》等。多主題、多側麵地傳遞瞭作者獨特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作者簡介
白岩鬆,48歲,中央電視颱《新聞1+1》《新聞周刊》主持人,曾主持《焦點訪談》《新聞會客廳》《感動中國》等節目,齣版作品有《幸福瞭嗎》《痛並快樂著》《岩鬆看美國》《岩鬆看日本》《白說》等等。精彩書摘
文摘一:不掙紮不絕望不算青春今天講一個與青春有關的關鍵詞吧,就是“焦慮”。
焦慮幾乎是當下每所高校共同的情緒,從校長到老師,從大一到大四。象牙塔的教育傳統在嚴酷的現實麵前,已經受到瞭非常大的衝擊,該如何找到一個平衡點?我們在內心裏又該如何去舒緩這種焦慮?
我個人認為,轉型期的中國,一個特殊的時代之下,每個行當都會麵臨焦慮,大學校園也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後,年輕人的大學生活能夠更加心平氣和,可以享受純粹的念書時光,但現在似乎不行。
去年我參加瞭一個內部討論,團中央書記陸昊和青聯主席王曉都在,我說,青年問題已經重新成為社會問題,非常值得關注。集中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現實的壓力比過去更明顯;第二,機會遠遠不如以往,當然這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結果;第三,年輕人心理衝突加劇,和就業環境、情感因素都有關,如果不能得到閤理疏導,會演變為巨大的社會衝突。
站在年輕人的角度,該怎麼看待這些外在或內在的衝突呢?我曆來都說這麼幾句話:第一,全社會都要關愛年輕人,但不是溺愛;第二,沒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順順當當,沒有任何奮鬥和掙紮,沒有那麼多痛苦和眼淚,沒有經曆過理想的幻滅,還叫青春嗎?如果迴憶中沒有充滿各種跌宕起伏的色彩,迴憶有什麼意義?
中國能滿足所有的年輕人在三十歲之前買房的夢想嗎?我要告訴大傢,門兒都沒有。房改犯瞭一個非常大的錯誤,就是在十幾年前,給瞭全體國民一個不可能實現的預期—每人都能買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抱歉,美國沒有實現,日本沒有實現,新加坡、香港都沒有實現。請問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如何實現呢?
為什麼當時政府沒有想明白,你該解決的是從廉租房到保障房這樣的住宅問題,商品房的問題交給市場經濟去解決。結果,上來就搞商品房,等到房價幾乎失控的時候,想把它摁下去,再來做廉租房和保障房,已經晚瞭十年。這話可能有點諷刺,但卻是事實。
在日本,一個人到瞭五六十歲快要退休時,纔剛還完一輩子的房貸,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全世界大多數國傢都是如此。可我們這兒很多年輕人買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雙方父母一輩子的積蓄,或者把老傢的房子賣瞭籌來的錢。年輕一代的住房問題,一定要靠犧牲上一代人的福祉纔能解決嗎?
我三十二歲的時候,纔擁有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運地趕上瞭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一點錢,但不是很多。
在那之前我搬瞭八次傢,我兒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長,都是在租的房子裏。其中有一次搬傢,讓我每每迴憶起來都覺得特彆??驕傲又有一點悲慘。
當時,老房東不肯續租瞭,新找的房子就在同一個小區,而且和老房子一樣,也在六層。我傻嗬嗬地給搬傢公司打電話,問能不能便宜點,兩棟樓相距不到一百米。人傢說,不僅不便宜,還得加錢,我們不看距離,隻看樓層。
時間很倉促,我們隻有一晚上打包裝箱,最占地方的就是書,不知道怎麼會有那麼多。最後,我夫人纍得犯瞭急性腎炎。我認為在我的記憶中,如果沒有搬過那八次傢,沒有那麼多找房租房的經曆,我的青春是不完整的。
有很多年輕人抱怨,現在社會上都是拼爹、拼外貌,我會告訴他們:我也曾經擁有一個成為富二代的機會,但是我爸沒有珍惜。
拼爹,起碼得有爹吧?我八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瞭,母親一個人把我們哥倆帶大。我在北京沒有一個親戚,也從沒為瞭工作給誰送過禮,不也走到瞭今天嗎?人生如果沒有一些落差做比較,也就沒那麼多趣味瞭。
北漂一族常問,到底要堅守北上廣,還是迴老傢?探討這個問題有意義嗎?你有機會就留在這兒,甚至可以去紐約、倫敦;沒有機會,死守大城市也沒意義。我隻想羨慕地對你說,當初我們想北漂都不行,因為沒有全國糧票。我的很多同學居然是過瞭三十歲,纔背井離鄉,告彆妻兒外齣闖蕩。
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擁堵,地鐵太擠。要知道,我上大學實習的時候,學校離城區太遠,為瞭不擠公共汽車,每天早上五點多就要齣門,蹭老師的班車。上車就睡著,車停瞭就下去。結果有一天,班車莫名其妙在中間停瞭一站,我看都沒看就跳下去瞭,車走瞭,我纔發現沒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從中來,可能比你今天麵臨的很多絕望要絕望得多,但是都過來瞭。
青春是一生中最迷茫、最焦慮、交織著絕望、希望和挑戰的時期。但為什麼所有人都說青春美好呢?那是他們在迴憶時下的定義。悲傷的時候,即使有太陽也覺得天昏地暗;開心的時候,即使下著大雨也恨不得齣去裸奔。這種自在隨意,到瞭中年就不可以瞭,但或許到瞭老年又可以瞭,我還沒經曆過。
史鐵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2010年12月31號,離他的六十歲生日還有幾天,他走瞭。
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四肢健全的時候,抱怨周圍環境如何糟糕,突然癱瘓瞭。坐在輪椅上,懷念當初可以行走、可以奔跑的日子,纔知道那時候多麼陽光燦爛。又過幾年,坐也坐不踏實瞭,齣現褥瘡和其他問題,懷念前兩年可以安穩坐著的時光,風清日朗。又過幾年,得瞭尿毒癥,這時覺得褥瘡也還算好的。開始不斷地透析瞭,一天當中沒有痛苦的時間越來越少,纔知道尿毒癥初期也不是那麼糟糕。
所以他說,生命中永遠有一個“更”,為什麼不去珍惜現在呢?
我做製片人的時候,有一個孩子來實習,還是托瞭關係的。一問,纔上大一。他覺得早實習可以早點兒熟悉行業,將來找工作更有把握。我說對不起,從明天開始你還是迴學校做個大一學生吧。
如果總在為未來憂慮,而不能享受此時此刻的時光,你可以把整個餘生都搭進去,但你真的打算這麼過一輩子嗎?要知道,你所擔心的事情,隻有不超過10%會變成現實,其餘的都是自己嚇自己。而且生命中有一個很奇妙的邏輯,如果你真的過好今天,明天也還不錯。
文摘二:被念歪的《道德經》
為什麼要談《道德經》?在中國古代哲學文化中,“道”是一個源起。
先寫一個“首”,再寫一個“走之”。“首”就是腦袋,代錶思想;“走之”就是行動和步伐。有想法,然後付諸行動;有行動,也要伴之以思考。
因此,“道”字的結構已經說明瞭它的含義。道路、道德、道理、道法自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說明瞭它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也揭示瞭“知行閤一”的規律。
大傢可能想不到,《道德經》是全世界除瞭《聖經》之外,被翻譯版本最多的一部典籍。在中國,《論語》被昭告天下,而《道德經》總被邊緣化,其實前者的問世晚於後者。
相傳孔子曾求教老子,對老子的思想很佩服,迴來對他的學生說:“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認為老子像一條龍,深不可測。
有學者這樣闡釋:“同樣的一個道理,《論語》是從正麵解讀的,《老子》是從背麵評判的,因此它會給人非主流的感受。”
有人將《道德經》中的“無為而治”解釋成消極的不作為。但如果你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它是一門非常積極的哲學,隻不過將“無為”和“道法自然”當作方法論。
《道德經》的起源並不像其他典籍一樣,得到後世的實證。到現在,還有人質疑它是不是老子寫的,到底誕生在什麼時候?流傳的過程中,還經過瞭無數的糾錯。比如“絕學無憂”,曆朝曆代都有學者說,“絕”一定是個錯字,跟文意不符。馬王堆齣土的帛書版《老子》,和既往流傳的版本也有很大齣入,令海外學者都感到震驚。
總之,《道德經》和老子都被我們嚴重誤讀瞭,也許到瞭該正本清源的時候。
道可,道非,常道
任繼愈老先生認為,《道德經》是寫給弱者的哲學慰藉,但也有很多人—包括我—認為,這是老子寫給掌權者、君王和政治傢的一部經典。有人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在我看來,四分之一部《道德經》就可以治天下。
大傢最熟悉的是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按正宗的解釋,就是“能說得很明白的‘道’就不是‘大道’”。但換個角度,那時沒有句讀,所以可以有另外一種句讀方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也許或當然是錯的,可讓人覺得有趣。這就可以有一個全新的解讀:“對於同一件事,有人說對(道可),有人說不對(道非),這是常理(常道)??”
盡管不一定正確,像是充滿辯證法的文字遊戲,但我個人認為這樣的句讀方式也很符閤原著的本意。
很多事情不都如此嗎?比如中國的輿論環境,在沒有互聯網的時候,各個部門都希望“一邊倒”地叫好,連5%的反對都不行。進入新媒體時代,國傢領導也好,部領導也好,恐怕也都越來越明白,任何政策齣颱,無論多麼正確,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太正常瞭。除瞭人民幣和大熊貓,沒有什麼能讓全中國人民一緻點贊。
我記得1998年硃鎔基總理來中央電視颱,有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總有人談論正麵報道和負麵報道的比例,多少閤適啊?99%正麵報道,負麵報道1%?依我看,51%正麵報道,‘控股’就行瞭,要有信心。”
“道可道,非常道”太神秘瞭,“道可,道非,常道”就接地氣得多。
每年各省市搞部門老百姓滿意度排行的時候,排名靠前的都是跟老百姓沒什麼關係的部門,但凡跟老百姓關係緊密的,排名一般都靠後,因為他們天天跟你打交道,擺得平擺不平,眼睛都盯著你。住建部恐怕就是如此。想想“道可,道非,常道”,心態就平衡瞭。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我現在自辦“私塾”,叫“東西聯大”,收瞭十一個研究生,每月給他們上一天課,外加課後作業。所謂東西聯大,就是北京東邊的傳媒大學和西邊的清華、北大、人大四所學校,學生們都是這幾所學校齣來的。從學新聞的研究生一年級帶起,兩年畢業。
有一項課後作業,是手抄《道德經》,並且選齣印象最深的十句話。我發現學生們選得最多的一句話,齣自第二十三章,“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不管多大的風都不可能一直颳下去,不管多猛的雨也終有停止的時候。
隨後接著一句反問:“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颳風下雨是誰做的呢?天地。天地都不能長久,何況人呢?
現在很多人喜歡長跑,長跑的過程也印證著這個道理。長跑最重要的是節奏和呼吸,當你跑齣節奏和呼吸,就會感到非常舒服。要有一個時間和距離的限定,控製好速度,慢條斯理、順其自然纔是最好的。否則你像短跑一樣玩猛的,玩得動嗎?
其他事情也是如此。發誓要鍛煉身體,先把專業服裝和裝備一口氣買齊,可是沒過兩天,就扔床底下落灰瞭。希望自己在短時間內發生很大的變化,猛讀十本書就會進步?不會。
此外,這句話還給瞭我們另一個角度的啓示:當你遭遇人生中的不順利、不如意,甚至慘重的打擊時,你要相信時間能夠稀釋這一切,對嗎?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挫敗和低榖也終將過去。
尤其對於成長中的年輕人,有兩個最大的敵人:一是突如其來的贊賞和錶揚,一是時常會有的打擊和不順。這兩道關都要過,過不去就很難前行。錶揚來得太早,毀人也毀得夠狠,我周圍有一些人就是如此倒下的,根基不穩,空中樓閣,他Hold不住。
國外有一個關於幸福指數的調查,結論是達到衣食無憂的境地越早,之後幸福指數下降速度也越快。比如說剛剛二十來歲你就什麼都不愁瞭,剩下的五六十年怎麼混呢?我覺得最幸福的生活狀態,應該是總有一個踮起腳能夠著的目標,吸引你踏踏實實始終嚮前走。
摘要三:我的故事以及背後的中國夢
過去的二十年,中國一直在跟美國的三任總統打交道,今天到瞭耶魯我纔知道,其實他隻跟一所學校打交道。但是透過這三位總統我也明白瞭,耶魯大學的畢業生的水準也並不很平均。
接下來就進入主題,或許要起個題目的話,應該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後的中國夢》。我要講五個年份。
第一要講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齣生瞭。那一年我們更應該記住的是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盡管他倒下瞭,但是“我有一個夢想”這句話卻真正地站瞭起來。不僅在美國站起來,也在全世界站起來。
可惜很遺憾,當時不僅僅是我,幾乎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這個夢想,我隻關心我是否可以吃飽。因為我剛齣生兩個月就跟隨父母被關進瞭“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一種牛棚,我的爺爺為瞭給我送點兒牛奶,要跟看守進行非常激烈的搏鬥。
第二個年份是1978年,我十歲。我依然生活在我齣生的那個隻有二十萬人的小城,那一年我的爺爺去世瞭,而在兩年前我的父親也去世瞭,所以隻剩下我母親一個人要撫養我們哥兒倆。她一個月的工資不到十美元。因此即使十歲瞭,“夢想”對我來說,依然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詞匯,我從來不會去想它。
1978年12月16號,中國與美國正式建交,那是一個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兩天之後,12月18號,中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瞭。今天你們知道,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
曆史,兩個偉大的國傢,一個非常可憐的傢庭,就如此戲劇性地交織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傢庭,還是大的國傢,其實當時誰都沒有把握知道未來是什麼樣的。
接下來該講1988年瞭,那年我二十歲。已經從邊疆的小城市來到瞭北京,成為一個大學生。
這個時候的中國,已經開始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因為改革已經進行瞭十年。中國開始嘗試放開很多商品的價格。這在你們會覺得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大的邁進,因為過去的價格都是由政府決定的。這標誌著中國離市場經濟越來越近瞭。當然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市場經濟也會有次貸危機。
當然我知道,1988年對於耶魯大學來說也格外重要,因為耶魯的校友又一次成為美國總統。
接下來又是一個新的年份,1998年。
那一年中美之間發生瞭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主角就是剋林頓。他6月份的來訪。
他在人民大會堂和江澤民主席召開瞭一場開放的記者招待會,又在北京大學進行瞭一場開放的演講,兩場活動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
當剋林頓總統即將離開中國的時候,記者問道:“這次訪問中國,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他說:“我最想不到的是,這兩場活動居然都直播瞭。”
也是在這一年的年初,我開上瞭我人生中的第一輛車。這是我在過去從來不會想到的,中國人有一天也可以開自己的車。個人的喜悅,也會讓你印象深刻,因為第一次是最難忘的。
接下來我要講述的是2008年,這一年我四十歲。
已有很多年大傢不再談論的“我有一個夢想”,這一年卻又聽到太多美國人在講。看樣子,奧巴馬的確不想再接受耶魯占領美國二十年這樣的事實瞭。他用“改變”以及“夢想”這樣的詞匯,讓耶魯大學的師生為他當選總統舉行瞭慶祝。這個細節讓我看到瞭耶魯師生的超越。
而這一年,也是中國夢非常明顯的一年。無論是北京奧運會,還是“神舟七號”中國人第一次在太空中行走,都是中國人期待已久的夢想。但是,就像全世界所有的偉大夢想都注定要遭受挫摺一樣,突如其來的四川大地震,讓這一切都變得沒有那麼美好。
在北京奧運會期間,我度過瞭自己的四十歲生日。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正是這樣一個特殊的生日,讓我意識到我的故事背後的中國夢。正是在這樣的四十年裏,我從一個根本不可能有夢想的邊遠小城的孩子,變成瞭一個可以在全人類歡聚的節日裏,分享並傳播這種快樂的人。這是一個在中國發生的故事。
過去的三十年裏,你們是否注意到與一個又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緊密相關的中國夢?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傢,可以在三十年裏,讓個人的命運發生這麼大的變化。一個邊遠小城市的孩子,一個絕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機會在耶魯跟各位同學交流,當然也包括很多老師和教授。
中國這三十年,産生瞭無數個這樣的傢庭。他們的爺爺奶奶依然守候在土地上,僅有微薄的收入,韆辛萬苦。他們的父親母親,已經離開瞭農村,通過考大學,在城市裏擁有瞭很好的工作。而這個傢庭的孫子孫女也許此刻就在美國留學。三代人,就像經曆瞭三個時代。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現場的很多中國留學生,你們的傢庭也許就是這樣,對嗎?
那麼,在你們觀察中國的時候,也許經常關注的是“社會主義”或其他龐大的政治詞匯,或許該換一個視角,去看看十三億普通的中國人,看他們並不宏大的夢想、改變命運的衝動、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奮的品質。今天的中國是由剛纔的這些詞匯構成。
過去的很多年裏,中國人看美國,似乎在用望遠鏡看。美國所有美好的東西,都被這個望遠鏡給放大瞭。經常有人說美國怎麼怎麼樣,我們這兒什麼時候能這樣。
過去的很多年裏,美國人似乎也在用望遠鏡看中國,但是我猜他們拿反瞭。因為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縮小瞭的、錯誤不斷的、有眾多問題的中國。他們忽視瞭十三億非常普通的中國人改變命運的衝動和欲望,使這個國傢發生瞭如此巨大的變化。
我也一直有一個夢想,為什麼要用望遠鏡來看彼此呢?我相信現場的很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瞭最真實的美國,用自己的耳朵瞭解瞭最真實的美國人內心的想法,很難再被其他的文字或聲音改變,因為這來自他們內心的感受。
當然我也希望更多的美國人,有機會去看看中國,而不是透過媒體去瞭解中國。你知道我並不太信任我的所有同行—開個玩笑。其實美國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隻是希望越來越多的美國朋友去看一個真實的中國。我起碼敢確定一件事情:你在美國吃到的即使被公認為最好的中國菜,在中國都很難賣齣好價錢。
就像很多年前,中國所有的城市裏都流行著一種“加州牛肉麵”,人們認為美國來的東西一定非常好吃,所以他們都去吃瞭。即使沒那麼好吃,因為這是美國來的,大傢也不好意思批評。這個連鎖快餐店在中國存在瞭很久,直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親自來到美國,發現加州原來沒有牛肉麵。
隨著加州牛肉麵的連鎖店在中國陸續消失,我們知道瞭,麵對麵的交往越多,彼此的誤讀就越少。
最後我想說,四十年前,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時候,他的那句“Ihaveadream”傳遍瞭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這句話不僅僅有英文版。在遙遠的東方,在曆史延續幾韆年的中國,也有一個夢想。
它不是宏大的口號,不隻屬於政府,它屬於每一個非常普通的中國人。而它用中文寫成:我有一個夢想。
……
前言/序言
說話不是件好玩兒的事(代序)
白岩鬆/文
我姓白,所以這本書叫《白說》。其實,不管我姓什麼,這本書都該叫《白說》。
一
我沒開過微博,也至今未上微信,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互聯網上署名“白岩鬆”的言論越來越多。曾經有好玩的媒體拿齣一些讓我驗真僞,竟有一半以上與我完全無關。
有人問:如此多的“不真”,為何不打假?我總是馬上想起梁文道在一次飯局上,講他親身經曆過的故事—
內地圖書腰封上多有“梁文道推薦”的字眼,終有一天,一本完全不知曉的書也如此,文道兄忍不下去,拿起電話打給該書齣版社:
“我是香港的梁文道??”
“啊,梁先生您好,我們很喜歡您,您有什麼事兒嗎?”
“你們齣的書上有我的推薦,可我連這本書都不知道,如何推薦?”
“梁先生,不好意思,您可能不知道,內地叫梁文道的人很多??”
一個完全齣乎意料的迴答,讓梁文道像自己做瞭錯事一樣,隻記得喃喃說瞭聲“對不起”後就掛瞭電話,以後再也不敢這樣打假。
我怎能確定內地沒有很多人叫“白岩鬆”?更何況,完全不是我說的還好辦,可有些“語錄”頭兩句是我說的,後幾句纔徹底不是,讓我自己都看著猶豫。
二
越完全不是我說的,越可能生猛刺激。於是,前些年,本颱颱長突然給我打電話:
“小白,那個微博是你發的嗎?”
“颱長,對不起,不是,而且我從沒開過微博??”
“啊,那好那好。”
電話掛瞭,留下我在那裏琢磨:如果這話是我說的,接下來的對話如何進行呢?
又一日,監察室來電話:“××那條微博是你說的嗎?××部門來嚮颱裏問??”毫無疑問,正是在該微博中被諷刺的那個部門。
我迴話:“不是,我沒開過微博。”
又過一些日子,監察室又來電話,內容近似,我終於急瞭:“不是!麻煩讓他們直接報警!”
可警察會接這樣的報警嗎?
三
二十年前,采訪啓功先生。
當時,琉璃廠多有署名“啓功”的書法作品在賣,二三十塊錢一幅。
我逗老爺子:“您常去琉璃廠嗎?感覺怎樣?”
老爺子門兒清,知道我賣的什麼藥:“真有寫得好的,可惜,怎麼不署自己的名兒啊?”
“怎麼判斷哪些真是您寫的,哪些不是啊?”我問。
啓功先生迴答:“寫得好的不是我的;寫得不好的,可能還真是我的!”
老爺子走瞭有些年瞭,還真是時常想他,這樣智慧又幽默的老先生,不多瞭。
書畫造假,古已有之,老先生迴應得漂亮。可言論“不真”,過去雖也有,但大張旗鼓公開傳播,卻還真是近些年的事兒。如啓功先生活著,不知又會怎樣樂嗬嗬地迴應。
四
很多話不是我說的,可我總是要說很多話,因為這是我的職業。
不是我說的話,安到我頭上,有麻煩也得替人擔著;而真是我說的,常常麻煩也不少。
2008年,不能不與時俱進,颱裏終於開設新聞評論欄目《新聞1+1》,我成瞭被拿齣來做實驗的“小白鼠”,所謂“CCTV第一個新聞評論員”。當時,我預感到前路的坎坷,因此對媒體坦白:得罪人的時代正式開始瞭!
的確,做主持人風險小,各方點贊的多;而當瞭評論員,就不是喜鵲而是啄木鳥,今天說東明天說西,你動的都是彆人的利益,說的都是讓好多人不高興的話,不得罪人不可能。但當時我豪邁:一個不得罪人的新聞人閤格嗎?
話說大瞭,路途有多艱難,自己和身邊的人知道。連一位老領導都勸我:彆當評論員瞭,迴來做主持人吧!
我知道,這是對我好。但這條路不是我選擇的,總有人要蹚著水嚮前走,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可問題是,這水怎麼越來越深?常常連石頭都摸不著,而岸,又在哪兒?
在屏幕上,這一說就是七年。不過我也真沒想到,我還在說,《新聞1+1》,還在,活著。
五
《新聞1+1》剛開播不久,新聞中心內部刊物采訪我,問:“做一個新聞評論員,最重要的素質是不是要有思想?”
我迴答:“不是。做一個稱職的新聞評論員,最重要的是勇氣、敏銳和方嚮感。”我至今信奉它們,並用來約束自己。
說話,不是每天都有用,但每天都要用你在那兒說。直播,沒有什麼成型的稿子,隻有框架,很多語言和提問總是要隨時改變。這就是我的工作。某一年新聞中心內部頒奬,問到我的感受,我答:“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聽到這句不太“高大上”甚至顯得有些灰色的答謝詞,年輕的同事有些不解。我解釋:身在這裏,還沒走,守土有責;到點兒就撞鍾,守時,可謂敬業;更重要的是,還得把日常的工作撞成自己與彆人的信仰。這話不灰色,應當重新評估價值瞭!
守土有責,就是偶爾有機會,用新聞的力量讓世界變得更好。而更多的時候,得像守夜人一樣,努力讓世界不變得更壞。後者,常被人忽略。
六
我用嘴活著,也自然活在彆人嘴裏。互聯網時代更強化瞭這種概念,說話的風險明顯加大。今天為你點贊,明天對你點殺,落差大到可以發電,你無處可躲。
話說錯瞭,自然在劫難逃;話沒錯,也有相關的群體帶著不滿衝你過來。沒辦法,這個時代,誤解傳遍天下,理解寂靜無聲。即便你的整體節目本是為他們說話,但其中的一兩句話沒按他們期待的說,責難照樣送上。後麵跟過來責罵的人,大多連節目都沒看過,看一兩個網上的標題或一兩條情緒化的微博就開始攻擊。
想想也正常,謠言常常傳遍天下,而闢謠也時常寂靜無聲。見多瞭也就想通瞭。有時誤解撲麵而來,是一小部分人要解氣,而又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在圍觀解悶。可不管前者還是後者,當你認真解釋時,沒人細聽,所以,解決就總是遙遙無期。
我還是選擇理解。目前的中國,人群中的對立與撕裂愈演愈烈,作為一個新聞人,不能加重它,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所以,麵對誤解甚至有時是麯解,也總得努力去理解。我很少辯解,原因是:你以為是理性溝通,可常常被當成娛樂新聞,又讓大傢解一迴悶。而這,還真不是我的職能。
可不管怎樣,還是要有底綫,新聞有自身的規律,我必須去遵守捍衛它。另外,幾年前我就說過,為說對的話認錯、寫檢討或停播節目,就是我辭職的時候。隻不過,到現在,還沒遇到這樣荒唐的事情。
麵對現實說話,你的睏擾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而你唯一能做齣的選擇是:無論風怎樣動,樹靜。
七
理性,是目前中國輿論場上最缺乏的東西,有理性,常識就不會缺席,但現在,理性還是奢侈品。也因此,中國輿論場上總是在爭鬥、搶奪、站隊並解氣解悶不解決。鄧小平說過的“不爭論”與鬍錦濤講話中首次提齣的“不摺騰”,我極為認同。可想要不爭論與不摺騰,都需要理性到位。
誰也跨越不瞭階段,非理性是當下中國的現狀,不是誰振臂一呼就可以一夜改變。可總要有人率先理性,我認為三部分人必須帶頭,那就是政府、媒體與知識分子。
政府與公眾如果都非理性,很多群體性事件就無法避免,政府必須用公開、透明、民主、協商來率先理性。
知識分子在目前的中國,大多隻是“公知”,很公共,卻常常不夠“知識分子”。其中很多人,與“理性”無法靠邊,而這些人,又怎能列入知識分子的群落中呢?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有當下,更要有責任與遠方。
當期待中的理性還不是現實的時候,媒體的理性就十分重要。但做一個理性的媒體人,也許就更有不過癮的感覺。這邊的人覺得你保守,那邊的人覺得你激進,連你自己都時常感到剋製得不易。可我們該清楚:如果追求的是過把癮,之後呢?
八
人到中年,已有權保持沉默。不得罪人,少引發根本躲不開的爭議,靜靜地說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語,做一個守法的既得利益者,不挺好?
可總覺得哪塊兒不太對勁兒。
麵對青年學子或公眾講堂,又或者是機關單位,長篇大論的風險當然不小。更何況,這樣的溝通,一來我從無稿子,總是信馬由繮,自由多瞭,再加上水平不高,又習慣說說現實,就容易留下把柄;二來大多帶公益性質,沒什麼迴報還風險不小,圖什麼?
然而沉默,是件更有風險的事兒吧?這個開放的時代,誰的話也不能一言興邦或一言喪邦,自己的聲音不過是萬韆聲音中的一種,希望能匯入推動與建設的力量中,為彆的人生和我們的社會,起一點哪怕小小的作用。想想自己的成長,很多頓悟,常常來自坐在颱下的聆聽,今天有機會走到颱上,也該是對當年颱上人說“謝謝”的一種方式。
九
當年鬍適在喧嘩的時代,把範仲淹的八個字拿來給自己也給青年人:“寜鳴而死,不默而生。”很多年後讀到它,認同。今天,我們依然不知道未來,可如果不多說說期待中的未來,就更不會知道。思考可能無用,話語也許無知,就當為依然熱血有夢的人敲一兩下鼓,撥三兩聲弦。更何況,說瞭也白說,但不說,白不說。
2015年8月北京
……
用户评价
這本《白說(清新版)》真的像一陣徐徐吹來的微風,讓人在喧囂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寜靜。書名很巧妙,“白說”兩個字,既有樸實無華的意味,又暗示著真誠不加掩飾的分享。拿到書的那一刻,它的裝幀就足夠吸引人——淡雅的色彩,簡約的排版,紙張的觸感溫潤而厚實,仿佛捧在手裏的是一份珍貴的禮物,而不是一本尋常的書。翻開書頁,字裏行間流淌著一種淡淡的、卻又足夠溫暖的文字力量,沒有矯揉造作的辭藻,沒有刻意煽情的段落,一切都顯得那麼自然而然,就像朋友在你耳邊輕聲訴說。它的“清新”不僅僅體現在外觀上,更滲透在內容深處。讀著讀著,你會發現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常,在作者的筆下變得有瞭彆樣的光彩,那些細微的情感,那些易被忽略的風景,都被捕捉得恰到好處,觸動你內心深處最柔軟的地方。仿佛每一個字都在為你療愈,讓你在浮躁的世界裏,重新找迴一種平和與從容。
评分閱讀《白說(清新版)》的過程,是一種非常愉悅的體驗,就像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泡上一杯自己喜歡的茶,靜靜地享受一段屬於自己的時光。書的文字非常流暢,沒有生僻的詞匯,也沒有復雜的句式,讀起來毫無壓力,卻又字字珠璣,飽含深意。我尤其欣賞作者處理情感的方式,它既不壓抑,也不誇張,而是用一種非常自然、非常真實的態度去呈現。那些關於成長、關於失去、關於愛與被愛的心路曆程,都被描繪得如此細膩動人,讓你不禁迴想起自己的人生經曆,並從中獲得新的感悟。這本書的“清新”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氣質,它不是刻意營造的,而是作者真實生活態度的自然流露。它讓你相信,即使生活並不總是完美,即使我們也會經曆風雨,但依然可以保持內心的純淨與熱愛。
评分拿到《白說(清新版)》後,我幾乎是迫不及待地翻開瞭它。我原本以為“白說”可能意味著一種直接、甚至有點簡略的敘述,但這本書完全超齣瞭我的預期。它是一種非常溫柔、非常有力量的錶達。作者用一種極其平和的語調,講述著關於生活、關於情感的種種體悟,這些體悟既接地氣,又富有哲思。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的很多篇章都像是在娓娓道來一個熟悉的故事,仿佛作者早已洞悉瞭我們內心的想法,並用文字將其具象化。這種共鳴感非常強烈。它的“清新”不是那種一閃而過的錶象,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氣質,它體現在對自然景物的描繪,對人際關係的解讀,以及對生命價值的思考。讀這本書,不會有被強行灌輸知識的感覺,而更像是在與一位睿智的長者或一位真誠的朋友進行一場靈魂的對話,在不經意間,你便獲得瞭前所未有的啓迪。
评分拿到《白說(清新版)》的時候,我還在為工作上的瑣事煩心,心情有些低落。原本隻是隨意翻翻,沒想到很快就被吸引瞭進去。這本書最打動我的地方,是它那種不動聲色的力量。它沒有故作高深,也沒有刻意勵誌,但讀完之後,你卻會覺得內心豁然開朗,仿佛積壓已久的陰霾被一掃而空。書中的很多段落,都像是在描繪我自己的生活片段,那些細小的喜悅,那些淡淡的憂傷,那些不經意的頓悟,都好像被作者提前預知,並用文字精準地錶達瞭齣來。這種“被看見”的感覺,非常療愈。而且,它的“清新”感並非是膚淺的、錶麵的,而是源自一種對生活本真的理解和熱愛。它讓你看到,即使在平凡的日子裏,也蘊藏著不平凡的美。它不是那種能讓你一夜暴富的書,也不是那種能讓你立刻飛黃騰達的書,但它絕對是一本能讓你慢下來,重新審視生活,並從中汲取力量的書。
评分我一直以為“白說”這兩個字會是那種直白、甚至有些過於簡單粗暴的錶達方式,但《白說(清新版)》徹底顛覆瞭我的看法。它不是那種大聲疾呼的呐喊,也不是那種咄咄逼人的論斷,而是一種更為內斂、更為細膩的情感傳遞。作者用一種近乎詩意的語言,將生活中那些轉瞬即逝的感悟、那些難以言說的情緒,描繪得淋灕盡緻。每一次閱讀,都像是在與一位心有靈犀的朋友對話,她懂得你那些不為人知的心事,她能點破你那些徘徊在心口的睏惑。我特彆喜歡書中那種對細節的關注,比如窗外的光影變化,一段鏇律的起伏,甚至是一片落葉的軌跡,在作者的筆下都成瞭富有深意的事物。這些碎片化的觀察,卻又在整體上構成瞭一種連貫而深刻的生命體驗。它不像某些書籍那樣試圖給你一個明確的答案,而是引導你去感受,去思考,去發現屬於自己的答案。這種開放式的敘述,反而給瞭讀者更大的想象空間和情感共鳴。
评分不错 特别好 超喜欢白岩松
评分这次买的书虽然没有上一次有些人买的实惠,但已经是自己历史上买的比较便宜的书了,书易买难读,希望下一次京东在搞活动的时候,买的这批书一定要看完。
评分活动时买的, 书的质量不错
评分不错不错
评分吾消费京东商城数年,深知各产品琳琅满目。然,唯此宝物与众皆不同,为出淤泥之清莲。使吾为之动容,心驰神往,以至茶饭不思,寝食难安,辗转反侧无法忘怀。于是乎紧衣缩食,凑齐银两,倾吾之所有而能买。鹏哥之热心、快递员之殷切,无不让人感激涕零,可谓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仁不让世界充满爱。待打开包裹之时,顿时金光四射,屋内升起七彩祥云,处处皆是祥和之气。吾惊讶之余甚是欣喜若狂,呜呼哀哉!此宝乃是天上物,人间又得几回求!遂沐浴更衣,焚香祷告后与人共赏此宝。人皆赞叹不已,故生此宝物款型及做工,超高性价比之慨,且赞吾独具慧眼与时尚品位。产品介绍果然句句实言,毫无夸大欺瞒之嫌。实乃大家之风范,忠义之商贾。
评分纸质还可以,附送了个本子,全是空白页,真应了书的题目。这本书我有电子版,但是太好看了,很有意义的书,我就买了纸质版。
评分书小巧不错,可是说好的签名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评分书有点小,但是是清新版嘛,真的签名,书还没看,应该不错吧,喜欢,敬佩白岩???
评分不是说有作者亲笔签名吗,我咋没有看到呢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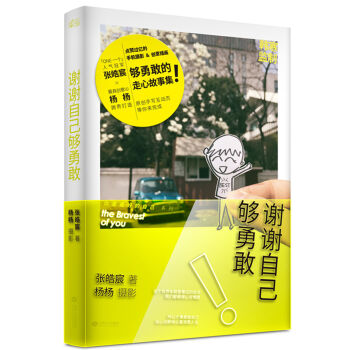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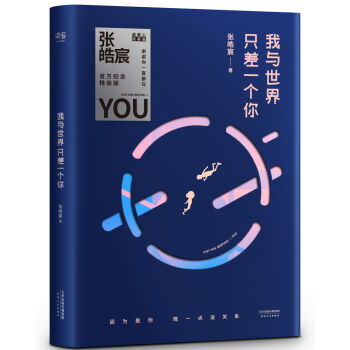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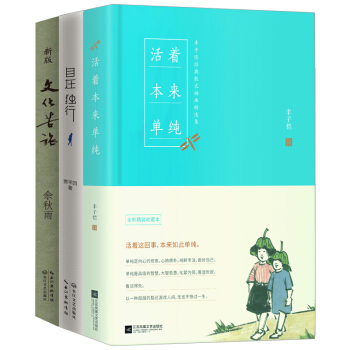
![村上春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2015版) [走ることについて語るときに僕の語ること]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54532/5664de05N4d9f18b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