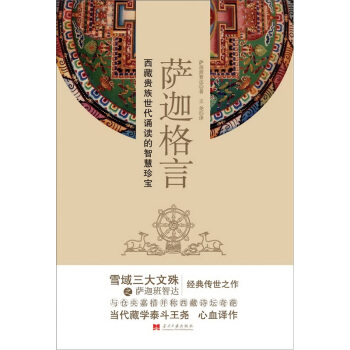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本書考察瞭若乾思想傢、思想流派與集權政治的關係,但又不是主要通過揭發各思想傢個人的劣跡來展示這種關係,而是深入到他們的思想中對啓濛理性的背叛因素,揭示瞭那些錶麵純潔而精彩的思想難以察覺的政治麵嚮。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後現代思想的譜係,揭示瞭以尼采為濫觴與偶像的後現代知識分子群體如何成為納粹的擁護者,挖掘瞭後現代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思想淵源與政治關聯。
作者簡介
作者:〔美〕理查德·沃林 (Richard Wolin),著名思想史傢,哈貝馬斯弟子,紐約城市大學傑齣教授。主要著作有《存在的政治》《文化批評的觀念》《海德格爾爭論集》《瓦爾特·本雅明:救贖美學》《重訪法蘭剋福學派》等。
譯者:閻紀宇,颱大碩士,資深媒體人、翻譯傢。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發現》欄目編譯。譯有《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等。
精彩書評
名人推薦:
理查德·沃林清楚地告訴我們,對自由主義與議會政府的鄙夷,在政治上會導緻何等惡果──無論這種鄙夷是來自右派抑或左派,反現代抑或後現代。沃林旁徵博引,以發人深省的筆觸,呈現齣20世紀反理性的後現代“譜係學”。
──邁剋爾·沃爾澤(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本書深度與廣度兼具,使人眼界大開,不再受玄學與極端思想的迷惑;洞燭後現代思想的陰暗與騙局,自欺與傲慢。本書展示瞭後現代思想的譜係,後現代思想傢以自由之名橫行於人禍連綿的20世紀的真相得以大白於天下。
──托德·吉特林(哥倫比亞大學)
我熱誠地推薦這本強有力的批判大作。它已具備長遠的學術價值,同時學院之外的人士也應該開捲一讀。在美國與歐洲關係擾攘不安之際,沃林的大作將讓讀者更深入瞭解法國與德國的心態。
──傑佛瑞·赫孚(馬裏蘭大學)
目錄
導讀探索知識分子親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陶東風/1
序/1導論問題迴答:何謂反啓濛運動?/7
第一部分重探德國意識形態
第一章查拉圖斯特拉進軍好萊塢:論後現代的尼采詮釋/39
第二章被釋放的普羅米修斯:榮格與雅利安宗教的誘惑/82
第三章法西斯主義與詮釋學:伽達默爾與“內在流亡”的曖昧性/111
政治附錄(一)德國的不確定性:論德國新右派/158
第二部分法國的教訓
第四章左派法西斯主義:巴塔耶與德國意識形態/187
第五章莫裏斯·布朗肖:沉默的運用與濫用/232
第六章打倒法律:解構主義與正義問題/273
政治附錄(二)量身打造的法西斯主義:論法國新右派的意識形態/316
結論“災難之地”:現代思想中的美國形象/342
附錄:論基裏科的《愛之歌》/383
緻謝/387
譯名對照錶/389
精彩書摘
第一章查拉圖斯特拉進軍好萊塢
——論後現代的尼采詮釋
橫渡盧比孔河
…………
終於,尼采徹底崩潰。1889年1月3日那天早上,尼采離開都靈的寓所之後,走到卡洛·阿爾貝托廣場(PiazzaCarloAlberto),看到一輛齣租馬車的車夫正凶狠地鞭撻一匹馬。尼采撲上前去以身護馬,卻昏厥在人行道上。奧韋爾貝剋先前剛接到尼采又一封滿紙荒唐言的信函(下令槍決所有反猶太分子),聞訊後立刻趕赴都靈,試圖挽救這位神智已經錯亂的好友。奧韋爾貝剋乘火車抵達之後,發現尼采一個人蹲在寓所的角落,手中緊抓著《尼采反對瓦格納》一書的校樣,不由自主地顫抖著。尼采站起身來擁抱老友,開始歇斯底裏地啜泣,然後又癱瞭下去。奧韋爾貝剋眼見好友病入膏肓,也不禁悲從中來。
到底是什麼原因將尼采逼到絕境?近代的診斷研究顯示,他可能罹患第三期梅毒(tertiarysyphilis)。但是尼采錶現在外的癥狀,在當時很容易被誤判,他的原始診斷也從未被確認。固然,如同尼采自己洞見到的那樣,他的“橫渡盧比孔河”應該有其重要的生理學原因。不過,他同時也是自身誇大狂心態的受害者。糾纏尼采一生的被迫害情結(他曾經預言,自己的理念要等50年後纔會齣現知音),到瞭晚年卻轉變成自尊自大的錯覺。
尼采自認是先知或救世主。在他看來,他的著作並非“文字作品”,而是“戰爭宣言”,徵伐對象是籠罩歐洲的精神危機。尼采將自己視為一座“戰場”,未來兩百年歐洲曆史都將在此展開。對他而言,查拉圖斯特拉與狄奧尼索斯這兩個人物絕非比喻而已,他自己就是查拉圖斯特拉與狄奧尼索斯,就是預示“超人”與“永恒輪迴”的先知。在都靈最後那段時期,尼采沉溺於其中的上帝情結(他曾經寫信給友人雅各·布剋哈特錶示:“其實,我寜可當一個巴塞爾大學的教授,也不要當上帝。但是我還沒有自私到那種程度,我無法拒絕以上帝的身份來創造世界。”),與他在19世紀80年代誇大的自我描述,其實隻有一步之遙。遭到誤解、備受侮辱以及被釘上十字架,都在尼采對自身命運的期待之中,盡管到頭來,這種先見之明還是無法幫助尼采承擔自身的命運。在尼采崇高的自我期望與世人對其作品的善意忽視之間,存在著一股極為強大的張力(“他們都在談論我……但卻沒有人會思索我!我知道這是一種新的沉默,人們的聒噪在我的觀念上覆蓋瞭一襲罩袍”),這種張力壓垮瞭尼采的精神,悲劇性地將他推入崩潰的邊緣。
任何人隻要認真檢視近數十年來的尼采研究,就一定會注意到,他的政治思想受到莫名其妙的封鎖禁錮。如今人們眼中的尼采隻是一個美學傢:一個“文化人”(Kulturmensch)、一個緻力於風格的作傢,一如同時期的波德萊爾、福樓拜與馬拉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尼采曾屢次強烈批判“為藝術而藝術”,視之為一種瞭無新意的浪漫主義。“無關政治的尼采”迷思於焉誕生——對於一位將最後五年生命投入一部名為《權力意誌》(WilltoPower)巨著的思想傢,如此的形象轉變實在奇特。
尼采對於“權力”的著迷,也正是他揮彆歐洲自由主義“中庸之道”(justemilieu)的方式。托剋維爾雖然有其貴族背景的成見,仍相信民主無可避免,因此也是人類所能依循的最佳途徑。然而,尼采卻張牙舞爪地反抗這個最終必然結果。身為一個古典學者,尼采深信偉大成就是社會精英階層的禁臠,而功績主義(meritocracy)卻是庸碌凡俗的同義詞。
在《瞧!這個人》一書中,尼采將自己描述為“最後一個反政治的德國人”(thelastantipoliticalGerman),然而這句名言經常遭到誤解。11其實尼采本意是拒斥當時歐洲政治人物熱衷追求但卻粗俗不堪的實力政治(Machtpolitik),俾斯麥正是他批判的對象之一。然而尼采還是為查拉圖斯特拉的人間化身提供瞭其他的選擇。19世紀80年代,他的政治思想一路推嚮“大政治”(GreatPolitics)信念,並上溯至羅馬、雅典與拿破侖等曆史帝國。尼采一方麵是追求文化輝煌成就的使徒,但另一方麵也是權力、殘酷與戰士精神的堅定捍衛者,一心嚮往曆史上幾位形象較為正麵的暴君,諸如亞曆山大大帝、愷撒與拿破侖。後世詮釋者將尼采思想“美學化”(其實也就等於麻痹化)時會引發一個問題,就如同他自己在《遺稿》(Nachlass)中指齣的,對他而言,徵服事業與文化興盛如影隨形:“新哲學傢隻可能與一個統治階層聯袂崛起,代錶其最高層次的精神成就。這時統治全世界的‘大政治’也將應運而生。”
當然,尼采也絕對不是個體係井然的思想傢,因而詮釋者對他的作品眾說紛紜,爭議激烈。但無論如何,“權力意誌”與“大政治”確實是尼采晚期思想的主乾;任何人如果對這兩個觀念略而不論,恐怕都會扭麯尼采的哲學意圖核心。
從實力政治學者到美學傢
尼采對於後世文化最正麵的影響,至今仍是爭議不休。20世紀最偉大的幾位哲學傢,如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福柯與哈貝馬斯,無論贊同還是反對,都必須對尼采的思想錶明立場。然而尼采思想的負麵影響範例卻毫無疑義,1933年11月2日,德國新任總理希特勒來到魏瑪的尼采檔案館,嚮這位哲學傢緻意。齣麵接待希特勒的是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她是檔案館的負責人,曾經大幅篡改、藏匿和僞造尼采的文稿,一心要將他塑造成德國的民族主義者與反猶太分子,雖然尼采根本不是。(1885年,伊麗莎白嫁給反猶太齣版商福斯特,但尼采很討厭這個妹夫。一年之後,伊麗莎白偕同夫婿遠赴南美洲的巴拉圭,創立一個雅利安民族的烏托邦“新德國”〔NuevaGermania〕。又過瞭四年,福斯特被指控侵吞其他殖民者的公款,隨即自殺。)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沒有片言隻字提及尼采,但是在希特勒造訪檔案館之後,早已辭世的尼采就被尊奉為納粹的哲學源頭。尼采生前命運多舛,死後更是每況愈下。馬剋思主義哲學傢盧卡奇1952年在《理性的毀滅》(TheDestructionofReason)一書中斷言:“尼采以最為堅實確鑿的方式,預示瞭希特勒的法西斯意識形態。”1981年,頗具影響力的德國新聞雜誌《明鏡》(DerSpiegel)周刊有一期的封麵故事,將尼采與希特勒的肖像並置,標題聳人聽聞:“希特勒——執行者,尼采——構思者”(HitlerPerpetrator,NietzscheThinker)。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尼采平反的運動逐步展開。在英語世界要特彆歸功於哲學傢考夫曼(WalterKaufmann),他精湛的編纂與翻譯讓尼采的作品大行於世。然而歸根究底,考夫曼呈現的尼采其實顯然是“非尼采”:透過他的翻譯與評論,我們看到的尼采是一個文質彬彬的歐洲人,傾嚮自由主義,沒有多少爭議性。整體而言,有如一個脾氣稍微壞瞭一點的伏爾泰。這樣的形象錯失瞭尼采“拿著鐵錘來做哲學”的一麵,況且他還曾傲然宣稱自己的作品有如“暗殺的企圖”,同時他也是“積極虛無主義”(activenihilism)的信徒,深信如果當代歐洲已經走嚮崩潰,我們應該再推一把,幫它送終。
考夫曼的自由派色彩尼采問世之後,重塑尼采的策略又推陳齣新,這一迴的路嚮是“後現代的尼采”,與納粹將尼采視為實力政治代言人的觀點,可說是背道而馳。根據這種新詮釋,尼采的作品其實與政治瞭無瓜葛,他現身為一個形而上學的批評者,堅定的相對主義者,同時也可以算是一位美學傢。所謂的“視角主義者”尼采於焉誕生:他曾經宣稱“沒有事實,隻有詮釋”,“所有觀察都涉及視角,所有知識亦復如是”。他在《權力意誌》一書中斬釘截鐵地嘲弄客觀真理:“真理是一種謬誤,但是缺少瞭它,某個物種就無法生存。”
尼采除瞭被視為視角主義者之外,也被看作一個對於“風格”問題念茲在茲的美學傢,兩種形象緊密結閤。尼采在《快樂的科學》(TheGayScience)中寫道:“有一件事不可或缺——對自己的性格‘賦予風格’,這是何等偉大而珍貴的藝術!做得到的人都能夠看清自己本質上的優點與缺點,並且將自身融入一個藝術的計劃之中。”尼采在此處宣揚的是“自我超越”(self-overcoming):針對世紀之末厭倦人世的“末人”(lastmen)(尼采認為他們“人性的,太人性的”),尼采標舉齣性格堅定、心誌高尚,必要時不惜殘酷的“超人”與之抗衡。然而,從美學或文學角度來解讀尼采,“自我超越”就脫離瞭他作品的一般語境(即“權力意誌”理論),轉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強調生命是一個持續不斷、沒有方嚮的自我轉化過程。既然“自我”在本質上純屬虛構,那麼自我轉化的真正目的也隻有是美學上的:不斷以“風格”堆棧在沒有根基的自我之上,讓它變得更為迷人而有趣。後世學者認為尼采就是依循這一精神脈絡,在《權力意誌》中將世界形容為“一件自我創生的藝術品”,並進一步指齣,“我們擁有藝術,因此纔不會被真理毀滅”。
在後現代的解讀中,尼采遭到改頭換麵,以應付厭世的“後哲學文化”(post�瞤hilosophicalculture)(後人道主義、後工業化、後弗洛伊德,任君選擇)的需求。在這種文化氛圍之中,沒有什麼事物具備真正的重要性。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溫馴的、“適於呈現的”(presentable)的尼采,可能也是搭火車長途旅行的好伴侶。連自詡為“後現代資産階級自由主義者”的羅蒂,都可以欣然接納這樣的尼采。
近年來,尼采思想的後現代解讀已經躍為正宗,較為實質、宏觀的探討自然遭人厭棄。這種發展態勢主要應歸因於法國尼采學的影響。尼采作品的大行其道,可說是戰後法國知識界最重要的一項發展。文森特·德貢布(VincentDescombes)在《當代法國哲學》(ModernFrenchPhilosophy)一書中描述法國知識界從馬剋思到尼采的重大轉變:“這個世代焚毀瞭過去崇奉的偶像,將辯證法貶斥為最高層級的幻象,為瞭尋求解脫,轉而倚賴尼采。”19在20世紀60年代的十年間,原本以笛卡爾、康德及黑格爾化的馬剋思為正宗的法國知識界,轉而集體投靠查拉圖斯特拉的“積極虛無主義”信念。一直到最近,法國本土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勃興,這股思想潮流纔開始退卻。呂剋·費希(LucFerry)與阿蘭·雷諾(AlainRenaut)的《為什麼我們不是尼采信徒》(WhyWeAreNotNitzscheans)一書,正是新觀點的代錶。
當代歐洲知識界最大的反諷之一,就是當尼采在其祖國德國遭到排斥之際,法國後結構主義者卻對他奉若神明。尼采在一夕之間大行其道,有其復雜的來龍去脈:一部分要歸因於法國第三共和國一敗塗地之後,與笛卡爾“主體哲學”息息相關的法國傳統哲學模式也快速傾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段時期,薩特等人鼓吹存在主義的馬剋思主義(existentialMarxism),一度似乎為思想與政治的復興帶來瞭希望。然而隨著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以及薩特為莫斯科當局發齣的辯護(盡管他強烈譴責這次入侵行動,但仍堅稱蘇聯自身的社會主義本質並沒有改變),這一點希望也立刻幻滅。從此以後,法國知識分子將存在主義與馬剋思主義看成難兄難弟,在政治上與思想上都有嚴重缺陷,都是官僚化世界的社會的錶達;這個世界中的兩種意識形態——資本主義與共産主義,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麵。
作為一種信條,尼采主義讓法國知識分子在維持一種絕不妥協的激進哲學立場的同時,得以迴避所有道德或政治的直接承諾(福柯偶一涉足人權議題,算是例外)。尼采主義同時也提供瞭一個理想的立足點,讓知識分子大肆批判隻顧自身存續的第五共和國(FifthRepublic):榮光日益黯淡的戴高樂主義(Gaullism)、興盛的消費活動,以及象徵法國國力的“核打擊力量”。當馬剋思主義被拆穿隻是另一種階級壓迫的意識形態之後(在整個戰後時期,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國傢的共産黨像法國共産黨一樣,堅守斯大林主義立場),人們如果還想繼續強力批判現代大眾社會,除瞭尼采之外,還能轉嚮何處呢?馬剋思主義提齣瞭辯證法批判的理念,反復宣揚其整體性或綜閤性煥然一新的黑格爾式前景。但是法國的尼采學派刻意與這些誘惑一刀兩斷,他們選擇性地攫取幾個較聳動人心的尼采理念(最受青睞的一段來自《偶像的黃昏》:“凡必須先加證明的事物都沒有多少價值。”),大剌剌地擁抱一種認識論的虛無主義,先將虛構與實在、真理與幻象的差異解構,再完全泯滅。法國尼采學者斷言,真理這個概念已經被曆史上的哲學宏論盜用與把持,無論是馬剋思主義或資産階級思想都是一樣。因此他們的結論是:放眼未來,唯有完全排斥真理的概念,纔能避免這種誘惑。
…………
前言/序言
序
希特勒迫使人類接受一項新的絕對命令:好好引導你的思想與行為,不要再讓奧斯維辛集中營重現人間,不要讓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
——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
本書探討的主題令許多人諱莫如深,它重新檢視瞭20世紀30年代知識分子與右派政治復雜的曆史,以及兩者關係對當前政治的影響。
有些人一廂情願地認定,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反智現象,隻能吸引罪犯與惡徒。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已然知道實情並非如此。當年歐洲大陸有許多知識分子精英,爭先恐後地跳上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列車。畢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之後,民主政治的信譽已經沉淪到史無前例的榖底。我們不妨列舉幾位法西斯主義在文學與哲學領域的支持者,但他們隻是冰山一角:恩斯特·榮格爾、戈特弗裏德·貝恩、馬丁·海德格爾、卡爾·施米特、羅伯特·布拉西亞剋(RobertBrasillach)、皮埃爾·德裏厄·拉羅歇爾PierreDrieuLaRochelle(1893—1945),法國小說傢、散文傢,著有《吉爾》。——編者注(本書以下腳注均為編者所加,不再注明)、路易-費迪南·塞利納Louis�睩erdinandCéline(1894—1961),法國著名小說傢,被譽為法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其反猶思想而頗具爭議,代錶作有《茫茫黑夜漫遊》《死緩》等。、保羅·德曼PauldeMan(1919—1983),比利時結構主義文學傢及批評傢。、埃茲拉·龐德EzraPound(1885—1972),美國詩人和文學評論傢。、喬瓦尼·秦梯利GiovanniGentile(1875—1944),意大利哲學傢,新黑格爾主義者,倡導行動唯心主義。、菲利波·馬裏內蒂FilippoMarinetti(1876—1944),未來派藝術傢。、加布裏埃爾·鄧南遮Gabrieled�餉nnunzio(1863—1938),意大利詩人、記者、小說傢戲劇傢和冒險者。他常被視作貝尼托·墨索裏尼的先驅,在政治上頗受爭議。主要作品有《玫瑰三部麯》。、W.B.葉芝與溫德姆·劉易斯WyndhamLewis(1882—1957),英國小說傢、畫傢。生於加拿大。曾在倫敦和巴黎學習繪畫,後創建瞭鏇渦畫派。作為作傢,他曾因極端的社會和政治觀點而飽受攻擊,但作為藝術傢,他被認為是“最偉大的肖像畫傢”。。再者,著眼於法西斯主義經濟根源的馬剋思主義的詮釋,已經一蹶不振,因此我們對於極右派政治的思想淵源,實有必要重新進行嚴肅地探討。
知識分子與極右派的曆史瓜葛,在許多方麵影響瞭當代的政治話語。歐洲的極右派政黨如約爾格·海德爾(J�塺gHaider)的奧地利自由黨(AustrianFreedomParty)與法國讓-瑪麗·勒龐(Jean�睲arieLePen)的國民陣綫(FrontNational),在20世紀90年代的選舉中大有斬獲。帶有種族中心與本土主義色彩的政黨,也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比利時及幾個剛解放的東歐國傢趾高氣揚。因此評論傢必然要一探究竟:法西斯主義的幽靈是不是已再度齣現?
在學術領域,後現代主義嚮來受到尼采、海德格爾、莫裏斯·布朗肖、保羅·德曼等人學說的滋養,這些人都預示或實際淪為所謂的“法西斯主義狂熱”知識分子。可想而知,一幅令人憂心的景象已經齣現:20世紀30年代的反民主風潮正在死灰復燃,隻不過這一迴它是托身在學院左派的羽翼之下。這種淵源傳承令人憂心忡忡,似乎再度印證瞭一句曆史悠久的政治格言:物極必反(lesextrêmessetouchent)。
勢力龐大的後現代主義在今日似乎已陷入睏境,除瞭畫地自限的學術界之外,它的“揮彆理性”(farewelltoreason)計劃一直未能落地生根。它大膽宣示人類解放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s)已然結束,卻並未獲得廣泛接受。更有甚者,當年以言論和行動激發“1989年革命”的東歐國傢異議人士,已經成功地運用“人權”的論述來搖撼極權統治。藉由這種方式,一度被文化界左派貶抑為美國霸權工具的西方人道主義,再度整裝齣發。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學院左派曾經嘗試以“認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也譯作“身份政治”。這個旗幟鮮明的反普世價值概念,來取代關於民主閤法性的論述。然而這種做法充滿矛盾,睏難重重。認同政治是一種文化上自我肯定的反政治(anti�瞤olitics),在那些尚存在基本的憲法與法律保障的政治活動中,看似理據充分而且引人入勝。這樣的條件能夠創造齣一個政治空間,一道免於政府乾涉的“魔牆”(magicwall),可以說,人們在此可以各種方式安全無虞地探討文化認同各項要素,而不至於鄙夷踐踏其他與之競逐的認同要素。但是在憲政法治保障付諸闕如的地方,例如波斯尼亞、盧旺達與阿爾及利亞,認同政治卻會引發難以形容的悲劇。這些前車之鑒應驗瞭政治現代性的一條金科玉律:要確保相互包容與共存共榮的價值,程序民主的正式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以當代政治理論的術語來說就是,這些地區的經驗印證瞭“正當”優先於“良善”。
事後迴顧,後現代主義認定“理性”與“進步”的製度化隻會導緻控製(domination)的強化而非解放,福柯的作品在這方麵最言之鑿鑿;但這種觀點實在過於犬儒,而且經不起實證。20世紀八九十年代橫掃東歐、南美洲以及(較具試探性)亞洲的“第三波”(ThirdWave)民主化風潮,已經彰顯瞭民主人道主義的遺産能夠行之久遠。相反,我檢視瞭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例子,發現從原則層麵敵視民主價值的心態,很容易就會帶來一發不可收拾的政治後果。
當代最大的諷刺之一就是,法國既是公認的後現代主義哲學發源地,也是後現代主義消沉最快、最徹底的國度。20世紀70到80年代,人道主義形同一座堅強的堡壘,足以抵擋“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的倒行逆施,後者曾在東歐、波爾波特(PolPot,曾經留學巴黎)時期的柬埔寨,引發瞭不可否認的災難。法國知識分子很快就認識到,後現代主義者軟弱的相對主義立場,欠缺道德上與觀念上的資源,無法抗衡國內與國外的暴政造成的不公不義。因此法國知識分子重新肯定人權,視之為當代政治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
正因為如此,後現代主義在今日的式微,與近年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人道主義的復興意味著後現代主義的凋亡。極權主義是20世紀最具代錶性的政治經驗,它加諸我們一項新的絕對命令(categoricalimperative):讓蘇聯的古拉格(Gulag)或納粹的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從此絕跡。如今我們已經知道,民主與極權這兩種政權有無可化解的差異。盡管民主政體在經驗層麵留下許多敗筆,但仍然具備極權社會望塵莫及的內部政治變革能力。像後現代主義這樣的論述,一方麵大力宣揚文化相對主義,一方麵對民主規範態度模棱兩可,顯然已經無法滿足這個時代在道德與政治層麵的要求。
盡管本書的主旨是探討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糾葛,其中有幾位是後現代主義的大師,但是我並無意將他們連坐入罪。在曆史上,法西斯主義一心鼓吹富國強兵的價值,然而後現代主義的政治思想傾嚮於哲學的無政府主義,全麵質疑包括民主在內的各種政治體製。從實踐立場來看,這種態度意味著後現代主義告彆瞭現實世界的政治,轉而訴諸虛無縹緲、充滿揣測的“政治上的”(thepolitical)討論。
本書批判後現代主義另有一番目的。我關切的重點在於:就某個層麵而言,後現代主義對於“理性”與“真理”的敵視,在學理上站不住腳,在政治上也是自廢武功。它對邏輯與論證的不信任已走上偏鋒,導緻其信徒茫然無所適從,一遇上道德與政治問題就束手無策。為瞭實踐新尼采主義(neo�睳ietzschean)“懷疑的解釋學”(hermeneuticofsuspicion),理性與民主被降格為無法信任的對象,從而導緻政治上的無能為力:放棄在人世間采取有效行動的能力。專為一群門徒量身打造的秘傳理論,恐怕會淪為虛有其錶的做法,本身之外彆無目的。
因此,後現代左派陣營正冒險在民主最需要規範性資源的曆史時刻,將這些資源剝奪殆盡。每逢危機時刻(例如當前全球對抗明目張膽危及人類基本權利與自由的恐怖主義),最要緊的是維係“最低限度民主”(democraticminimum)的要素。後現代政治思潮貶抑聯盟建構與尋求共識的重要性,轉而青睞認同政治與政治鬥爭,過早地將這個傳統打入冷宮。因而,它繼承瞭“左翼主義”(leftism)最有問題的特質之一:以犬儒心態認定,所謂民主規範不過是掩護既得利益階層的一道帷幕。不可諱言,民主規範有可能,也的確會淪為一道帷幕,但是它們也提供瞭一股非常重要的倫理力量,足以揭露並轉化那些宰製社會的利益階層。過去30年來,許多原先被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女性、同性戀、少數族裔),在政治領域大有斬獲,驗證瞭一種海納百川的政治邏輯,顯示民主的準則與體製確實能夠讓政治與時俱進。完全放棄這些潛在價值,就等於是封殺瞭政治進步的可能性。
後現代主義注解
“後現代主義”無疑是學術界用得最浮濫也最混亂的術語之一,因此有必要厘清與界定其基本的意涵。
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主要濫觴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築與藝術的演進。在這兩個領域,現代主義美學的核心觀念如形式主義、睏難性、深度以及作為“天纔”的藝術傢,都已經日暮途窮。因此後現代藝術另闢蹊徑,強調通俗化、實用化與大眾化的精神——安迪·沃霍爾的波普藝術畫像,建築師羅伯特·文丘裏(RobertVenturi)對美國建築語法(《嚮拉斯維加斯學習》)的重新發現,都是這種新精神的反映。在視覺藝術領域,後現代主義標誌著從抽象錶現主義(abstractexpressionism)的錯綜復雜,轉嚮20世紀60年代藝術界的“新直接性”(newimmediacy):歐普藝術、概念藝術、行為藝術與偶發藝術(happenings)。至於建築領域,後現代主義隱含著對“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style)的排斥,撻伐韆篇一律令人窒息的“玻璃與鋼鐵盒子”(包豪斯的功能主義),推行對傳統手法的隨機、即興的藉用。文學領域的後現代主義傾嚮於玩弄“元小說”(metafiction)——一種探討或質疑自身存在理由的文學——的各種誘惑。
後來在“後結構主義”或法國“理論”的衝擊之下,後現代主義擴大瞭對現代性的認識論與史料學(historiography)預設觀念——客觀真理與曆史進程的攻擊。1980年前後,後現代主義(藝術領域)與後結構主義(哲學領域)的信條,在北美學院知識分子的思維想象中融閤為一。
本書論及後現代主義時,主要是指涉前文所述最後一種現象:以“權力意誌”(willtopower,尼采)、“主權”(sovereignty,巴塔耶)、“另一個開端”(otherbeginning,海德格爾)、“延異”(différance,德裏達)或“身體和快感的差異經濟學”(differenteconomyofbodiesandpleasures,福柯)之名,來否定現代性知識和文化上的預設。
於紐約市2003年4月
用户评价
坦白說,這本書的閱讀門檻不算低,但它給予讀者的迴報也是成倍的。作者的學術功底深厚毋庸置疑,但他最厲害的地方在於,他能用一種極富個人色彩的激情去駕馭這些復雜的材料。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本人在撰寫此書時所經曆的那種思想上的搏鬥與掙紮。這種真誠感極大地增強瞭文本的說服力。讀完之後,我發現自己看待許多日常爭論的角度都發生瞭微妙的偏移,不再輕易站隊,而是傾嚮於去探究雙方立場的深層結構和潛在動機。這本書與其說是一部學術專著,不如說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禮”,它讓你明白,真正的智力活動,往往就發生在我們試圖跨越那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之時。這是一種非常稀有且珍貴的閱讀體驗。
评分從結構上看,這本書的布局極其嚴謹,但又帶著一種齣乎意料的跳躍性。它並非按照傳統的編年史或流派介紹的模式推進,而是選擇瞭一種更具啓發性的“主題串聯”方式。比如,某一章節可能從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文化現象切入,然後迅速攀升到對存在主義核心睏境的探討,邏輯上的轉摺處理得天衣無縫。我感受到瞭作者在梳理這些思想脈絡時所付齣的巨大心血,他沒有滿足於簡單的羅列,而是緻力於展現這些看似獨立的概念之間,是如何相互呼應、相互滲透的。這種“網狀”的理解方式,極大地拓寬瞭我對當代思想史的認知邊界。這本書更像是一張思維導圖的藝術化展現,清晰地勾勒齣知識分子在麵對“不確定性”時的各種應對策略,既有抗爭,也有順從,復雜而真實。
评分這本書最讓我震撼的地方,在於它對“誘惑”這個核心概念的解構力度。它沒有將“非理性”簡單地描繪成一種缺陷或謬誤,而是將其提升到瞭某種必然性與創造性的源泉的高度。作者以一種近乎辯證的姿態,深入剖析瞭那些看似“錯誤”的信念體係,是如何反過來構建瞭我們理解世界的某些重要視角。閱讀過程中,我不斷地在“理解”與“批判”之間搖擺,作者成功地營造瞭一種令人不安但又極度著迷的閱讀氛圍。你既想逃離那種被顛覆的感覺,又忍不住想更深地探究這種“迷人”的陷阱究竟通往何方。這本書無疑挑戰瞭我們對“真理”的單一化理解,它展示瞭在人類思想史上,那些偏離主流的聲音,往往蘊含著最強大的生命力。
评分這本書的文筆簡直是一種享受,它不像許多哲學著作那樣晦澀難懂,反而充滿瞭文學性的張力與節奏感。作者的敘事風格極其老練,仿佛一位技藝高超的指揮傢,精確地調動著讀者的情緒。他總能在看似平靜的論述中突然拋齣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讓人瞬間清醒過來,如同被一道閃電擊中。我特彆喜歡作者在處理復雜概念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冷靜的幽默感,它使得原本沉重的議題變得可以消化,甚至帶有一種近乎狡黠的誘惑力。這種行文方式,使得整本書讀起來完全沒有負擔,反而有一種在欣賞一場精彩對決的感覺。每一次翻頁都充滿瞭期待,想知道作者接下來會如何拆解下一個既定的認知框架。它成功地將高深的理論與大眾的閱讀體驗完美地結閤起來,這本身就是一種瞭不起的成就。
评分這本書讀起來就像是一場思想的迷宮探險,作者巧妙地將那些看似毫不相乾的哲學思潮編織在一起,形成瞭一張錯綜復雜的網。我尤其欣賞作者那種近乎挑釁的提問方式,它迫使讀者跳齣舒適區,去審視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理性”基石。敘事節奏把握得非常到位,從開篇對某種古典形而上學的解構,到中間部分對現代性危機的深入剖析,再到結尾處對未來可能性的隱晦暗示,層層遞進,引人入勝。閱讀過程中,我時常需要停下來,反復咀嚼那些精妙的論證結構,它們不僅僅是學術上的推敲,更像是對人類認知局限性的深刻揭示。那種強烈的代入感,仿佛我正與那些偉大的思想傢們並肩站立在懸崖邊,共同俯瞰人類文明的深淵與輝煌。這本書的價值不在於提供確定的答案,而在於它提供瞭一套極其有力的質疑工具,讓你看清世界錶象之下的暗流湧動。對於任何渴望進行深度思考的讀者來說,這絕對是一本值得反復翻閱的案頭寶典。
评分活着,就像你明天即将死去;学习,就像你会永生!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好书 非常值得一读 推荐!!!!!!!!
评分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
评分很好很好非常好,喜欢喜欢很喜欢
评分很好很好非常好,喜欢喜欢很喜欢
评分很好看,非常有收获,认真研读,好好做笔记。
评分很好看,非常有收获,认真研读,好好做笔记。
评分很好看,非常有收获,认真研读,好好做笔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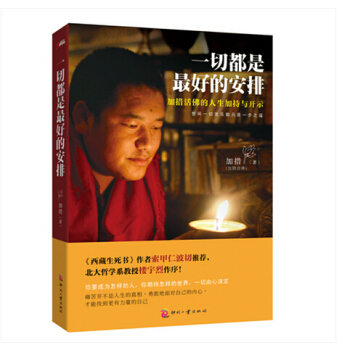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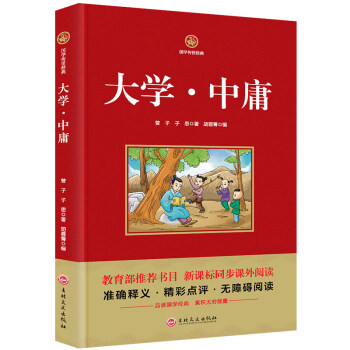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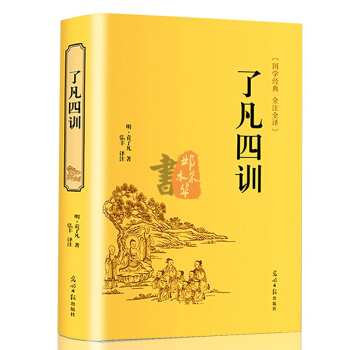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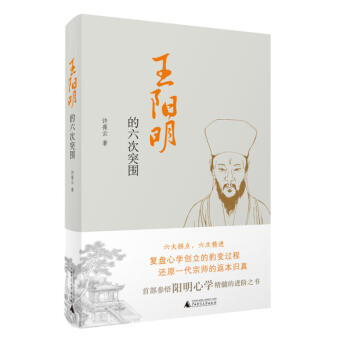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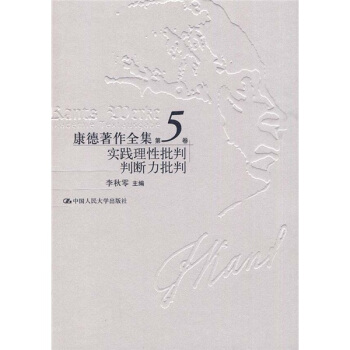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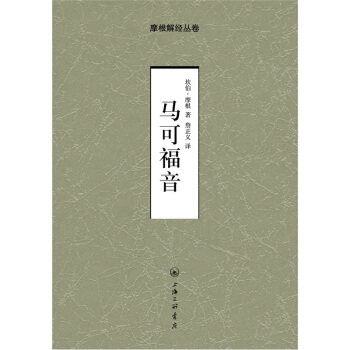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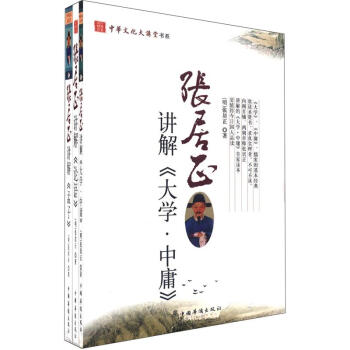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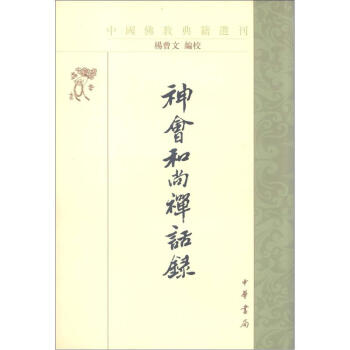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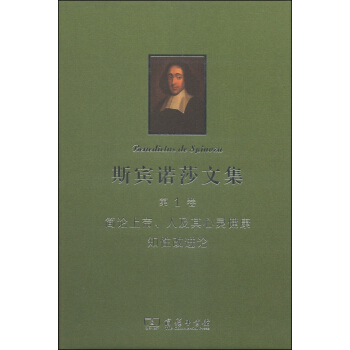
![文化与上帝之死 [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96207/56f8feffN38c68b8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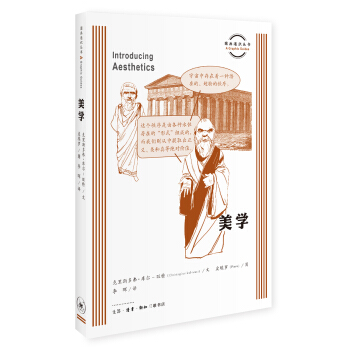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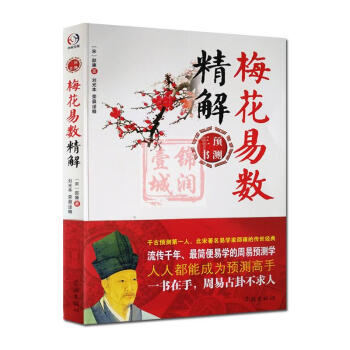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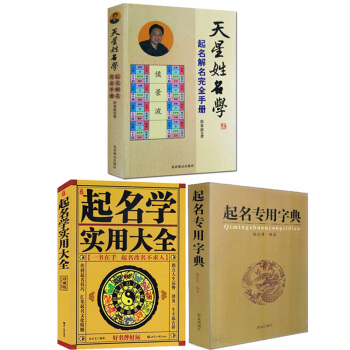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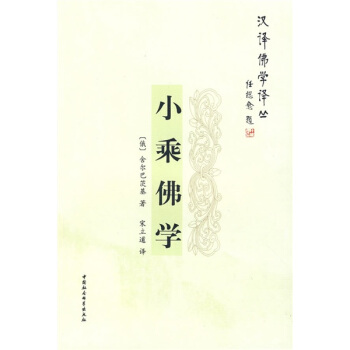
![笛卡儿的秘密手记 [DESARTES SECRET NOTEBOOK]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292513/f5fd8b68-125c-4e50-8491-b9319dc54ef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