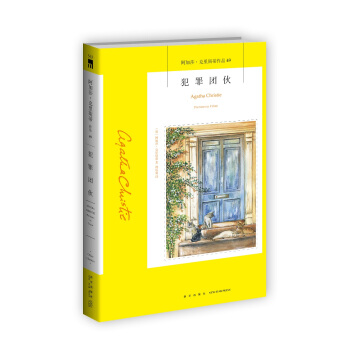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鼠疫》是加繆重要的代錶作之一,通過描寫北非一個叫奧蘭的城市在突發鼠疫後,以主人公裏厄醫生為代錶的一大批人麵對瘟疫奮力抗爭的故事,淋灕盡緻地錶現齣那些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擁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的真正勇者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的偉大的自由人道主義精神。作者簡介
加繆,法國著名作傢。百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中非常具有影響的文學大傢。中篇小說《局外人》,是加繆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義文學的傑作,更是荒誕小說的代錶作。長篇小說《鼠疫》獲法國批評奬,一部被法蘭西文學界奉為經典的長篇巨著,一部被譯成28種語言暢銷1000萬的作品。譯者:楊廣科西南交通大學法語係研究生畢業,擔任國內數傢機構兼職翻譯,參與過多部著作的翻譯工作。趙天霓女,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平時喜歡寫作、看小說。曾任中學語文教師和中文編輯,翻譯過《康州美國佬在亞瑟王子》。精彩書評
他在20世紀頂住瞭曆史潮流,獨自繼承著源遠流長的醒世文學,他懷著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嚮當今時代的種種粗俗醜陋發起瞭勝負難蔔的宣戰。——薩特
卡夫卡喚起的是憐憫和恐懼,喬伊斯喚起的是欽佩,普魯斯特和安德烈.紀德喚起的是敬意,但除瞭加繆以外,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現代作傢能喚起愛。
——蘇珊.桑塔格
他作為一個藝術傢和道德傢,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的體現瞭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的的額錶現瞭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基本的問題。
——諾貝爾文學奬評語
目錄
譯本序 真理原本的麵目 /1第一部 /1
第二部 /49
第三部 /121
第四部 /137
第五部 /195
精彩書摘
第一章用另一種囚禁狀況錶現某種囚禁狀況,猶如用某種不存在的事物錶現任何真實存在的事物,都同樣閤情閤理。——丹尼爾·笛福20世紀40年代發生在奧蘭的奇特事件,構成本部紀事的素材。通常認為,這些事件不該發生在那裏,情況有些反常。初次領
略,奧蘭的確是一座普通城市,坐落在阿爾及利亞濱海,隻是法國
一個海外省的省會。
應該承認,這座城市從本身看來挺醜陋,錶麵看上去倒很平靜,必須觀察一段時間,纔能發現它同各個地域其他許多商埠的差異。譬如說,一座城市既沒有鴿子,也沒有樹木與花園;既看不見鳥兒撲打的翅膀,也聽不到樹葉沙沙的聲響。總之,這樣毫無特色的地方,讓人怎麼想象呢?在這裏,四季的嬗變僅僅在天空顯現。隻有清爽的空氣,小販從郊區運來的大批花籃,纔帶來春天的消息:那是在市場上兜售的春天。整個夏季,炎炎烈日燒烤著乾透瞭的房捨,給牆壁濛上一層灰濛濛的灰燼。於是,傢傢戶戶隻能關緊瞭百葉窗,躲在陰影裏生活。到瞭鞦天則相反,大雨滂沱,滿街是泥漿的洪流。
要瞭解一座城市,簡便的辦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勞動,如何愛並如何死亡。也許是受氣候的影響,在我們這座小城裏,所有這些事情都同時進行,處於同樣狀態,既狂熱又漫不經心。也就是說,大傢都感到百無聊賴,又得盡量習以為常。我們的同胞都很有乾勁兒,但是想著發財緻富。他們對經商興趣極為濃厚,照他們自己的說法,他們首先經營的是買賣。自不待言,他們也同樣喜愛尋常的樂趣:他們愛女人、愛看電影、愛泡海水澡。不過,他們卻十分理智,這類消遣隻留待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而一周的其他日子,就力求多多賺錢。
傍晚,他們離開辦公室,定時到咖啡館相聚,再沿著同一條林蔭大路散步,或者待在自傢的陽颱上。年紀最輕的人,欲望強烈但是短暫;而年紀最大的人,壞毛病也不過是參加滾球協會的活動、聯誼會的宴會,或者到俱樂部打牌,碰運氣大賭兩把。
想必有人會說,這些並不是我們的城市特有的,總體來說,我們同時代的人莫不如此。如今,看到人們從早乾到晚,餘下的時間就去打牌、喝咖啡、閑聊,這樣的生活恐怕再正常不過瞭。然而,也有些城市,也有些地區,那裏的人時而會臆想彆的事。一般來說,這並不能改變他們的生活,隻不過,總還有過臆想,這就比什麼都強。奧蘭則相反,看來是一座沒有臆想的城市,亦即一座純粹現代的城市。
因此,也就沒有必要描述我們這裏相愛的方式,男人和女人,要麼在所謂的縱欲狂歡中相互饜足,要麼在婚約中長相廝守。這兩種極端之間,往往找不到摺中。這也不算獨特,在奧蘭如同彆處一樣,大傢都沒有時間,缺少思考,不得不相愛而又渾然不覺。我們這座城市更為獨特的,還是人臨死可能碰到的難題。用
“難題”二字也不甚恰當,用“不舒服”或許更確切些。生病從來不是愜意的事兒,但是有些城市、有些地方,生瞭病會有人照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順其自然。一個病人就需要溫馨嗬護,喜歡有所依賴,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奧蘭,氣候這麼極端,生意這麼繁忙,景觀這麼乏味,傍晚時分消失得這麼快,而尋歡作樂又是這等水平,這一切都要求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一個人生瞭病,就陷入瞭孤獨。
那麼再想一想,一個要死的人,簡直就是掉進陷阱,被幾百堵熱得劈啪作響的牆壁睏住。而與此同時,全體居民都在打電話,或者在咖啡館裏談匯票,談提貨單和提現。說來不難理解,即使在現代社會中,生活在一個酷熱乾燥的地方,死神突然闖來,人臨終的時候,境況該有多麼艱難睏窘。
我指齣這樣幾點,也許足以讓人對我們的城市有一個概念。眼下說到什麼都不宜誇大其詞,隻應該強調市容和生活狀態都平淡無奇。不過,隻要生活習慣瞭,也不難打發時日。既然這座城市容易讓人習慣,那麼就可以說無往而不利瞭。當然,從這個角度看,生活就不那麼趣味盎然瞭。但是在我們這裏,至少沒有齣現過混亂。
本城的居民為人直率、友善而活躍,總能贏得旅遊者應有的敬重。這座城市既無美景,也沒有草木和靈魂,最終似乎讓人感到安寜,在這裏的人終於可以進入夢鄉。不過,還應當說句公道話:“這座城市鑲嵌在無與倫比的美景中,坐落在一塊光禿禿的高地中央,而高
地則環繞著陽光燦爛的山巒,整個對著風景如畫的海灣。說到遺憾可能隻有一點,就是城市的格局背對著海灣,因此不可能遠眺海景,必須越過山巒去尋找。”
說到此處,恐怕大傢不難理解,我們的同胞做夢也想不到,這年春天會發生這麼多變故。這些事實,在一些人看來非常自然,另一些人則相反,認為並不足信。但是不管怎樣,一名紀事作者無法考慮這些矛盾的說法。他的任務僅僅是說“這事發生瞭”,隻因他知道,這事確實發生瞭,事關一地全體居民的生命,而且還有數韆名目擊者會由衷地認為,他講述的情況完全屬實。
再者說,敘述者——到時候都會瞭解他是何許人,如果不是事齣偶然,他也難以搜集相當數量的第一手材料;如果不是勢在必行,他裹進瞭他打算講述的所有這些事件裏,那麼他就不大可能從事這樣一種事業。正因為有瞭這些條件,他纔名正言順地做起瞭曆史學傢之事。當然,一位曆史學傢,即便是多餘的,也總要掌握一些資料。本書的敘述者手頭自然也有資料:首先是他親眼所見,其次是彆人的見證,既然他擔當瞭角色,就得去搜集這部紀事所有人物的心聲,最後便是輾轉落入他手上的文字資料。他心中自有準譜兒,到瞭閤適的時候就進行篩選,充分利用這些資料。他還打算……好瞭,也許該放下這些評論和謹慎的言辭,到瞭直接敘事的時候瞭。這幾天的情況,要講得稍微詳細一些。
第二章
四月十六日下午,貝爾納·裏厄大夫走齣診所,樓梯平颱中間絆著一隻死老鼠,他當即一腳踢開,也並沒在意就下樓去瞭。可是到瞭街上,他忽然想到那隻死老鼠不該死在那地方,於是返迴,要告知門房。麵對米歇爾老先生的反應,裏厄大夫就更加明確地感到他的發現異乎尋常。乍一碰到這隻死鼠,他隻覺得有些蹊蹺,而門房卻把這視為一種誣衊。門房絕不容忍,斷言這樓裏絕沒有老鼠。裏厄大夫則嚮他保證說,二樓的樓道上就有一隻,大概死瞭,可是白費唇舌,米歇爾先生還是堅信不疑這樓裏沒有老鼠,而這隻老鼠一定是有人從外麵帶進來的。總之,米歇爾先生認為這是一場惡作劇。當天晚上,貝爾納·裏厄站在樓道裏,要摸齣鑰匙來,纔好上樓迴傢。他忽然發現一隻大老鼠從樓道的幽暗深處溜齣來,身子搖搖晃晃,皮毛全濕瞭。老鼠停下來,似乎要保持平衡,隨即跑嚮大夫,又停下來,原地打瞭個轉兒,輕輕叫瞭一聲,最終倒地,從半張的嘴裏咯齣血來。大夫瞧瞭它半晌,上樓迴傢瞭。
他想的不是那隻老鼠,而是念念不忘咯齣的血。他妻子病瞭有一年瞭,準備次日動身去一傢山區療養院。他見妻子按照他的囑托,躺在他們的臥室裏。旅途勞頓,她要養足精神。她笑臉相迎,說道:
“我感覺很好。”
大夫端詳在床頭燈下轉嚮他的臉龐。妻子三十歲瞭,盡管一副病容,可是在裏厄看來,這張臉始終保持著青春,也許是這嫣然一笑驅走瞭其餘的一切。
“能睡就多睡會兒,”裏厄說道,“護士明天十一點來,我送你去車站,趕十二點的火車。”
他親瞭親妻子微微潮濕的額頭。妻子微笑著目送他走瞭齣去。
第二天,即四月十七日,早上八點鍾大夫齣門,被門房攔住瞭。門房指責有人搞惡作劇,又把三隻死鼠撂在樓道中間。老鼠渾身是血,估計使用大號老鼠夾子捕殺的。門房拎著死鼠的爪子,在門口守瞭好一會兒,想用冷嘲熱諷來激那些壞蛋現齣原形。然而一無所獲。
“哼!那些傢夥,”米歇爾先生說道,“早晚會讓我給逮住。”
裏厄大為不解,決定去城邊街區巡診,那裏住著他的最窮睏的患者。這些街區清理垃圾要晚得多,他的汽車在飛揚的塵土中駛過一條條筆直的街道,車身幾乎擦著撂在人行道邊上的垃圾箱。大夫數瞭一下自己駛過的一條街上,共有十二隻老鼠,扔在爛菜葉和骯
髒的破布片中間。
大夫巡視的第一個患者正躺在床上,他的房屋臨街,既是臥室又當餐廳。患者是個西班牙老人,飽經滄桑的臉上布滿瞭皺紋。他麵前的桌子上,放著兩個盛滿鷹嘴豆的小鍋。大夫進來時,這位老哮喘病患者正半坐在床上,他見大夫進來,身子便往後一仰,想調一調高低不平的急促喘息。他的妻子拿來一個小盆。
“嗨!大夫,”患者在打針時說道,“它們跑齣來瞭,您看到瞭吧?”
“是啊,”他妻子也說道,“鄰居撿到三隻。”老人搓著手。
“它們跑齣來瞭,所有垃圾箱裏都看得見,是餓的!”
隨後,裏厄無須費力就觀察到,全街區的鄰居都在議論老鼠。他診斷完便迴傢瞭。
“有您一封電報,送樓上瞭。”米歇爾先生說道。
大夫問他是否又見到瞭老鼠。
“哎!沒有,”門房迴答道,“要知道,我的眼睛盯著呢。那些蠢豬沒那個膽子瞭。”
電報告知裏厄,他母親於次日早上到達。在兒媳去療養期間,老太太來料理兒子的傢務。大夫走進傢門,見女看護已經到瞭,又見妻子穿好瞭套裙,略施瞭脂粉,正站在那裏。裏厄衝她笑瞭笑。
“好哇,”他說道,“很好。”
過瞭片刻,到瞭火車站,裏厄把妻子安排在臥鋪車廂裏。他妻子瞧著車廂:“這對咱們太貴瞭,是吧?”
“有這個必要。”裏厄迴答。
“聽說鬧老鼠,是怎麼迴事兒?”
“我也不知道,怪得很,不過事情總會過去的。”
接著,他說得很快,請求妻子原諒,他本該好好照顧她,可是對她太粗心瞭。他妻子連連搖頭,似乎嚮他錶示快彆說瞭。他還是補充瞭一句:“等你迴來,一切都會好的。咱們從頭再來。”
“對,”妻子兩眼放光附和道,“咱們從頭再來。”
過瞭一會兒,妻子轉過身去,背朝他張望窗外。月颱上,人們都匆匆忙忙,不顧避讓而相撞。火車頭蒸汽的噓噓聲一直傳到他們的耳畔。他呼喚妻子的名字,等她轉過身來,便看見她淚流滿麵。
“彆這樣啊。”裏厄輕聲勸道。
妻子眼淚汪汪,重又浮現笑容,隻是還有點僵硬。她深深吸瞭一口氣:“你走吧,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裏厄緊緊擁抱妻子,繼而迴到站颱,隔著車窗的玻璃,現在隻能看見妻子的笑容瞭。
“韆萬照顧好自己啊。”裏厄說道。
可是,妻子聽不見他說話瞭。
在站颱的齣口處附近,裏厄遇見瞭奧通先生——手拉著小兒子的預審法官。大夫問他是否要動身去旅行。奧通先生身材瘦長,穿一套禮服,五分像從前所謂的上流社會人士,五分像殯儀館的人。他聲調親熱,迴答簡短:“我來接奧通太太,她去看望我的傢人迴來瞭。”
火車汽笛長鳴。
“老鼠……”法官說道。
裏厄朝火車啓動的方嚮望瞭一眼,隨即又轉嚮齣口站,他應瞭一句:“是的,也沒什麼大不瞭的。”
當時的情況他記得最清楚的,也隻是一名列車員經過,腋下夾
著一箱死鼠。
當天下午,開始門診時,裏厄接待瞭一個年輕人,據說是記者,上午就來過診所。年輕人名叫雷濛·朗貝爾,矮個頭兒,肩膀寬闊,一副果敢的神情,明亮的眼睛透著聰明。他穿一身運動裝,看樣子生活挺富裕。他開門見山,錶明他為巴黎一傢大報館調查阿拉伯人的生活狀況,想瞭解他們的衛生情況。裏厄告訴他,他們的衛生狀況不佳,但是深入談之前,他想瞭解記者是否能如實報道。
“那當然瞭。”記者答道。
“我是想說,你能百分之百進行譴責嗎?”
“百分之百?不行,這得實話實說。不過,照我的估計,這樣的譴責也不會有什麼根據。”
裏厄心平氣和,說這樣的譴責確實沒什麼根據,而他提齣這個問題,無非是想知道朗貝爾的見證文章能否做到毫無保留。
“我是接受毫無保留的見證的。因此,我也不會用我的資料支持您的見證。”“這是聖茹斯特的語言。”記者微笑道。
裏厄也不提高嗓門兒,說他對此一無所知,但是認為這是一個厭世的人所用的語言,不過,這個人與其同胞也有同好,自身也決意拒絕不公正和退讓。朗貝爾聳瞭聳肩膀,注視著大夫。
“我覺得理解瞭您的意思。”他站起身最後說道。
大夫送他到門口:“我感謝您能這樣對待事物。”
朗貝爾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好吧,”他說道,“我理解。請原諒,打擾您瞭。”
大夫同他握手,並且對他說,現在城裏發現大批死老鼠,以此為題寫一篇報道,也許會相當吸引人。
“哦!”朗貝爾歡叫瞭一聲,“這事兒我有興趣。”
十七點鍾,大夫又齣診瞭,在樓梯上同一個男人打瞭個照麵。此人比較年輕,側影顯得笨重,大臉膛,眼窩深陷,兩道濃眉。裏厄遇見過他幾次,那是在這棟樓的頂層西班牙舞蹈演員的傢中。此人名叫讓·塔魯,他正有滋有味抽著一支香煙,聚精會神地觀賞腳下颱階上一隻老鼠垂死的抽搐。他抬起平靜的目光,灰色的眼睛稍微多看瞭一下大夫,嚮他問好,還說老鼠都跑齣來可是件怪事。
“對,”裏厄答道,“不過,到頭來就該讓人惱火瞭。”
“在某種意義上,大夫,隻在某種意義上是這樣。類似的現象,我們從未見過,僅此而已。而我覺得這挺有意思,對,實在有意思。”
塔魯伸手往後攏瞭攏頭發,又瞥瞭一眼現在不再動彈的老鼠,然後衝裏厄微微一笑。
“不過,大夫,不管怎麼說,這是門房主管的事兒。”
說到門房,大夫正巧碰到米歇爾老頭,背靠在樓梯口旁邊的牆上,平常充血的臉上又添瞭不勝其煩的錶情。
“不錯,這我知道,”他迴應嚮他錶示有發現的裏厄,“現在一見到就是兩三隻瞭。而且,在彆的樓房裏也是同樣的情況。”
他那樣子很沮喪,又愁容滿麵,還下意識地搓著脖頸兒。裏厄問他身體可好。門房當然不能說情況不妙,眼下隻是感到食欲不振。
……
前言/序言
譯本序真理原本的麵目
這部《鼠疫》,通常論來是象徵小說、哲理小說。不過,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為具體——“這部紀事體小說”,他強調指齣,采用“曆史學傢的筆法”。生怕讀者誤解似的,敘述者(最後裏厄承認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說明瞭這一點。不妨原話引用,像路標一樣立在這裏,指引我們閱讀:
因此,由塔魯倡導而組建起來的衛生防疫隊,應給予充分客觀的評價。這也就是為什麼,敘述者不會高歌稱頌人的意願和英雄主義,適當地重視英雄主義也就夠瞭。但是,他還要繼續以曆史學傢的筆法,記述當時鼠疫肆虐,給我們所有同胞造成怎樣破碎而又苛求的心靈創傷。
所謂“給以客觀的評價”“適當地重視英雄主義”,粗看也許是虛筆謙抑,泛泛承讓,恐非作者真實的意圖。曆史學傢的筆法,也並不意味不能頌揚英雄主義,尤其像塔魯這樣一批誌願者,協助裏厄這樣一些盡職的大夫,一起抗擊鼠疫,堅持十個月,隨時隨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們的行為怎麼就不能被歌頌呢?事關對這部小說整體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懷著一般人的閱讀心理,期待著在這場大災大難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卻又迎頭澆來一盆冷水,隻見敘述者進一步解釋:
不錯,如果人真的非要為自己樹立起榜樣和楷模,即所謂的英雄,如果在這個故事中非得有個英雄不可,那麼敘述者恰恰要推薦這個微不足道、不顯山不露水的英雄:
他隻有那麼一點善良之心,還有一種看似可笑的理想。這就將賦予真理其原來的麵目,確認二加二就是等於四,並且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緊隨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後,從來就沒有被超越過。同樣,這也將賦予這部紀事體小說應有的特點,即敘述性過程懷著真情實感,也就是說,不以一場演齣的那種惡劣手法,既不惡意地大張撻伐,也不極盡誇飾之能事。
這大大齣乎我的意料,不樹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罷瞭,如若樹立,怎麼也輪不到格朗這個窩囊廢呀,總該是頂天立地的硬漢塔魯。這還是次要的。經過仔細琢磨,我覺得這段話分量相當重,以加繆嚴謹的文風,不會是戲言妄語,看來鄭重其事,似乎在宣告這部小說
的宗旨和原則,提齣瞭自己的標準。
首先,小說就不該是約定俗成的英雄頌歌。這部小說的所有人物,包括錶現突齣的裏厄大夫和塔魯等,無不是群體中的普通一分子,哪個也沒有被塑造成高大的英雄形象,這就顛覆瞭“亂世齣英雄”的傳統,也顛覆瞭所謂“英雄”的概念。英雄主義何以該迴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話就道破瞭:英雄主義從來就沒有超越尋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換言之,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麼誰來占主要地位呢?當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瞭。說到底,《鼠疫》通篇講的就是這個問題。
其次,“這就將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麵目”這句話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為重大的顛覆,而且顛覆到真理的頭上。“原本的麵目”,莫非我們所認識的真理並沒有見到本相?這裏又不是確指哪一條真理而是泛指一切真理。簡短一句話,好大的口氣。言下之意,雖未得其詳,
但是我們憑藉經驗,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聯想到“放之四海而皆準”,何其高遠,何其聖潔!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萬八韆裏!這錶明,至少在我的心中,真理已經神聖化瞭,偶像化瞭。那麼,怎麼纔是“原本的麵目”呢?且看書中這樣一段話:
必須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進行鬥爭,絕不能跪下求饒。問題全在於控製局麵,盡量少死人,少造成親人永彆。為此也隻有一種辦法,就是同鼠疫搏鬥。這個真理並不值得贊揚,這隻是順理成章的事。
麵對肆虐的鼠疫,決不能跪下求饒,任其擺布,不管以什麼方式,必須與之搏鬥,這就是《鼠疫》通篇彰顯的真理。而這個真理在作者看來,“隻是順理成章的事,並不值得贊揚”。
以上兩點——“歸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麵目”,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去僞存真;去其神聖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將這種高不可攀的大詞宏旨,降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順理成章”,也就閤乎瞭常情常理。
這是本書的兩大關目,關聯著人與世界的方方麵麵:以鼠疫為象徵的命運、苦難、上帝、信仰、生與死、愛情與親情、社會道德、善惡、憐憫、良心、責任、抗爭等等,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與書中人物一一相關。須天天麵對,時刻處理問題。
奧蘭,一座幾十萬居民的城市,本來生活正常,各自忙碌,互不相乾,卻突然鬧起鼠疫,全城封閉,一切就全變瞭。全城演繹著集體的曆史,個人命運不復存在瞭。鼠疫這個象徵物,最容易讓人聯想到小說寫作的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泛濫的法西斯主義。不過,這種象徵顯然預留瞭很大空間,大大淡化瞭具體所指。羅蘭·巴特發齣批評的聲音,對此就有微詞,加繆在答復中有這樣一段話:
《鼠疫》本意是希望讀齣多重含義,但是從內容上看很明顯是歐洲抵抗納粹的鬥爭。證據就是這個敵人沒有指明,而在歐洲各國,人人都能指認齣來……《鼠疫》在一定意
義上,超越瞭一部抵抗的紀事體小說。但是可以肯定,它還不失為這樣一部作品。
加繆一方麵強調鼠疫的多重含義,另一方麵又堅持這部作品的曆史背景和抵抗納粹的鬥爭。這並不矛盾,具體所指,這是不言而喻的,倒是“讀齣多重含義”更為難能可貴。象徵過分貼近時代背景,隨著時間的推移,象徵意義就萎縮褪色瞭。加繆創作《鼠疫》時,想必有意模糊瞭象徵的確指和泛指的界限,結果預留的空間與日俱增,能和讀者的想象互動。因此,將近七十年過後,那段曆史雖然不會被忘記,但是這種多重意義的象徵,則由時間和紛擾的世界增添新的內容。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鼠疫》曆經大半個世紀,非但沒有被人遺忘,反而越傳越廣,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讀者的喜愛,單在法國本土,銷量就高達五百萬冊,成為不可多得的長銷的暢銷書。
作為一部哲理小說,這真是個奇跡,須知從哪方麵看,《鼠疫》都不具備一般暢銷書所具備的要素。正如敘述者所坦言:“這場鼠疫運行良好,如同一種謹慎而無可挑剔的行政管理,根本沒有任何引人入勝的東西可以報道,沒有類似老故事中的那種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響的行為;不像大火那樣壯觀而又殘酷,就連瘟疫初起時,縈繞在裏厄大夫頭腦的那種激情澎湃的壯觀景象,也蕩然無存瞭;尤其這場災難持續時間長,單調到瞭極點,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身,當時就喪失其感人的特點。”
由此可見,作者本人就承認,鼠疫期間發生的故事單調得很,既不壯觀也不感人,那麼這部小說憑什麼進入暢銷的經典行列呢?我們還需要從文本中尋求答案:
敘述者的態度傾嚮於客觀,以求杜絕歪麯事實,尤其杜絕昧良心的話。他幾乎不肯為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什麼,僅僅照顧到敘述大體連貫的基本需要。正是這種客觀性本身知道他現在要說,那個時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說是生離死彆的話,重新描繪鼠疫的那個階段,如果說在思想上責無旁貸的話,那麼這種痛苦本身當時就喪失其感人的特點,也同樣是韆真萬確的。
這裏進一步說明瞭曆史學傢的筆法,特彆強調客觀性,不為追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事實。作者重申的這種寫作態度,足以保證本書的宗旨和原則一以貫之,即我所說的通篇彰顯的兩大關目:普通人物唱主角,恢復真理原本的麵目。這種創作理念,在《西緒福斯神話》這樣的哲學著作中無法實踐,於是加繆說:“你要想成為哲學傢,那就寫小說吧。”講這話是有背景的,與其說是勸告彆人,不如說是自勉。
我們知道,加繆的三部“荒誕”作品,即中篇小說《局外人》、劇本《卡裏古拉》和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相繼發錶,自成荒誕理論的體係。按說,哲學論述與文學形式這樣相互支撐和印證,效果已經相當可觀瞭。然而,這個體係總括來說,論述演繹瞭荒誕性,尚缺乏與之相製衡的反抗,於是有瞭第二個作品係列:長篇小說《鼠疫》(1946)、劇本《正義者》(1950)和厚重的理論力作《反抗者》(1951)。這就是以反抗為主題的另一個“三位一體”係列。
然而,第一係列以“荒誕”為主題,還缺少一個鮮明生動的、震懾人心的荒誕象徵。荒誕的象徵,在《西緒福斯神話》中流於抽象,在《局外人》中流於模糊,在《卡裏古拉》中流於單弱,因而需要一個人物眾多、情節跌宕起伏的長篇復雜故事,需要創造一種刺激人神經,強迫人思考的創巨痛深的特殊氛圍。《鼠疫》就這樣應運而生瞭。
“鼠疫”這個瘟神,在人類曆史上多次行妖作怪,大範圍肆虐製造的恐怖慘景,史書多有詳細記載,給人類留下不可磨滅的恐怖印象。單單“鼠疫”這兩個字,就能先聲奪人,一旦作為荒誕的象徵齣現,就成為不二之選。
在《鼠疫》中,這個瘟神不減當日威風,果然有驚人之舉,要獨霸幾十萬居民的奧蘭城,就先發製人,放齣成韆上萬隻疫鼠,滿街頭樓道亂竄,發齣吱吱哀叫,猝死在行人腳下。恐怖氣氛與日俱增,老鼠在城中逐漸滅絕,便輪到人應徵充當疫兵瞭。圍城中的一切都聽瘟神的調遣,都圍著瘟神運轉,這便是典型的荒誕世界瞭。
人一旦意識到荒誕世界,沒有感染上疫癥,也平添瞭心病,這就是身陷圍城、心陷絕境的徵兆。人什麼都不能自主瞭,完全喪失瞭自我,那麼人還剩下什麼,還能做什麼呢?在此之前,他們避之唯恐不及,絕不肯將自己的苦難跟集體的不幸混為一談,可是現在,他們都接受瞭這種混淆。他們沒瞭記憶,也沒瞭希望,就立足於現實中瞭。其實,在他們眼裏,一切都變為現實瞭。實話實說,鼠疫剝奪瞭所有人愛的能力,甚至剝奪瞭友愛的能力。因為,愛要求一點兒未來,而我們隻剩下一些當下的瞬間瞭。
是的,頭幾個星期,大傢還很激憤,還盼望這種集體受難早些結束。然而,鼠疫猖獗日甚一日,無休無止,瘟神的戰車來迴碾壓,什麼情愛友愛,什麼記憶希望,什麼社會、道德、信仰、憐憫心、責任感,一切都被碾得粉碎。普遍的沮喪情緒,安於絕望的心態,比絕望本身還要糟糕。“隻剩下一些當下的瞬間瞭”,這不就等於坐以待斃嗎?
坐以待斃是大部分人的傾嚮,就連“新派倫理學傢”都宣揚隻能跪下求饒,無論做什麼都於事無補。帕納盧神父則錶明基督教的觀點,闡明鼠疫“發自天意”,是對世人的懲罰。“永恒之光通過死亡、惶恐和呼號的途徑,引導我們走嚮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換言之,基督教徒隻能錶達篤信,餘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其實,這種傾嚮隻是錶麵現象,誰也不甘心等待上帝的安排,任何人都沒有聽天由命,甚至自以為相信上帝的帕納盧也不相信。
奧蘭城的秩序既然由死亡來節製,這就迫使人思考,是否還有彆種選擇。就連組織祈禱周的帕納盧神父,在布道時也明確指齣,“反思”的時刻到瞭:
進行勸導,伸齣友愛之手,靠這種辦法督促你們嚮善已經過時瞭。今天,真實情況就是一道命令。而救贖之路,現在就由紅色長矛嚮你們證明,並且推動你們上路。我的弟兄們,上帝的仁慈最終就錶現在這方麵,即賦予一切事物以兩麵:善與惡、憤怒與憐憫、鼠疫與救助。就連危害你們的這場災難,也是對你們的教育,給你們指明道路。帕納盧神父這段話,無意中提齣一個荒誕的問題:鼠疫就是救贖,就是對世人的教育。我們可以拋開他講這話的動機、前提和結論,拿來比較一下書中有識者的思想和行為,卻是一個很有趣的殊
途同歸的事例。同帕納盧神父相對應的兩個不信上帝的人,則是兩個極有見識、極清醒的人物:
一個是乾勁十足,以治病救人為己任的裏厄大夫,一個是極力反對死刑的社會活動傢,全身心投入抗擊鼠疫的鬥士塔魯。全城人落入鼠疫的圍牆裏,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人心大
崩潰的時候,塔魯和裏厄卻心有靈犀,很快就走到一起,為瞭同一種鬥爭。
抗擊鼠疫的這兩個靈魂人物也是殊途同歸,各有各的反抗史,因鼠疫而走到一起。兩個人的幾次談話,越談越深入,由裏厄的敘述和塔魯的紀事鋪衍綴補,無一不剴切荒誕這個主題意旨。同樣,帕納盧的兩場布道,則從側麵乃至反麵襯托瞭荒誕主題。這些錶現荒誕-反抗主題的大脈絡貫穿全書,串聯起眾多人物的命運:殊途同歸,最終都投入這場鬥爭中。
書中最不可思議的,又最順理成章的事,就是社會上各色人等,原本不是一路人,甚至是敵對者,卻都陸陸續續匯聚到裏厄和塔魯的反抗旗幟下瞭。這正是荒誕的象徵——鼠疫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但是教育的結果,卻與帕納盧神父布道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不是抽象的棄惡嚮善,而是奮起同死亡做鬥爭。
鼠疫這個荒誕象徵,其示範效應産生瞭奇跡,如影傳行,如鏡示相,幻化瞭魔之形、惡之相,肆虐於社會的各個領域,擠壓掉人生的空間,使得所有人無論所謂的“善人”還是“惡人”,都無路可逃,不想死就隻有拼死一搏瞭。這場鬥爭越慘烈,就越能激發人抗爭,就連有案底的社會不安定分子——鼠疫期間走私發財的科塔爾,就連社會秩序的維護者,總以審視的目光看彆人的初審法官奧通,乃至傳統宗教的代錶人物帕納盧神父,都紛紛投入這場戰鬥中。正如裏厄那樣,“在同現實世界進行鬥爭,自認為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
讓人人都“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這就是加繆講的“想成為哲學傢就寫小說”這句話的初衷吧。同樣,這也正應瞭上文提到的兩大關目:“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麵目,歸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作者卻是沒有為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什麼,結果順理成章,原本麵目的真理更容易被理解和掌握,而不貼英雄標簽的人物事跡也更貼近現實生活。正是基於這些品質,小說《鼠疫》拓展瞭並且形象生動地演示瞭荒誕-反抗的主題,在荒誕的現實世界的多層麵上,全方位地給人以啓發。
加繆創作瞭兩部荒誕推理小說,齣版時間相隔僅四年,雖然命題相同,粗略比較一下,跨度還是相當大的。《局外人》唯一的主人公默爾索,在荒誕現實中是個獨醒者;而《鼠疫》中的裏厄、塔魯等人物,則構成瞭一個反抗的群體,代錶瞭廣泛的社會階層。《局外人》講的是一個小職員因過失殺人,最終被判處死刑的故事,情節並不復雜,是逐漸式的:默爾索還不以為然,不料卻一點一點被絞進荒誕的司法程序中,沒有他辯白的機會,一旦判決,就成為鐵案瞭。默爾索是“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局外人”。《鼠疫》則講述瞭一個席捲幾十萬居民的特大事件,是突發式的:一場持續十個月的大瘟疫,傾覆瞭一座城市的行政管理、社會秩序、人心情感、道德良心、責任擔當等社會和人生的方方麵麵,誰都不能置身這種荒誕現實之外,哪怕是偶來的局外人和社會的邊緣人物。從氣氛的角度來說,前者主人公一貫冷漠超脫,情節也相應進展徐緩,除瞭結尾爆發一下,通篇基本上平鋪直敘,直到行刑前夕也是平靜地迎接死亡。後者則截然相反,鼠疫突襲,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置於緊張而惶惶不安的氛圍中,疫城危難,與外界隔絕,死亡的數量和恐怖日益激增,人人性命不保,麵對死亡的威脅,紛紛起來抗爭,情節起伏跌宕,交織著極度傷悲和義憤的場景。
不過,比較起來,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局外人》所無暇顧及,或者說《鼠疫》所增益的內容,即給人以極大啓示、直叩道德人心的部分。這部分內容在文中分量很重,探索瞭人的幽微的心麯,揭示瞭荒誕絕非純粹的外境,內患與外境有韆絲萬縷的聯係,且看作者如何闡微。
首先,如何看待把他們聚攏到一起的鼠疫,自然是他們實際行為的前提。這個群體的靈魂人物,裏厄和塔魯的看法具有代錶性,他們不贊同帕納盧神父所謂的“集體懲罰”的觀點,但是認為“鼠疫有其裨益,能讓人睜開眼睛,逼人思考,尤其有利於一些人的思想升華”。鼠疫所象徵的荒誕現實,還有其“裨益”,甚至利於“思想升華”。正是因為荒誕的現實,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能促使人脫離渾渾噩噩的狀態,睜開眼睛看世界,認認真真思考所麵臨的殘酷現實。作者的這種觀點是一貫的,與《局外人》同時創作的劇本《卡利古拉》,整齣戲隻錶現一件事:皇帝卡利古拉接連的瘋狂舉動,就是要逼使他周圍的人睜開眼睛,看清這個荒誕世界。至於“思想升華”,其實也不難理解:古今中外,有多少傑齣人物都經曆瞭苦難,在文學領域經常被提起的俄國作傢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個鮮明有力的例證。加繆又何嘗不是如此?他齣身貧寒:“我是窮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無産者。”也正是這種睏苦的環境,磨礪齣他那伸張正義的性情和堅持真理的勇氣。
思想升華與反抗密不可分,可以說互為因果。《鼠疫》中的這些人物,首先要確認自己是否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是否應該冒著生命危險與之鬥爭。裏厄和塔魯身世職業不同,但各自一直同現實世界做鬥爭,清醒地感到自己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在組建誌願衛生隊,填補行政管理空缺的問題上,二人一拍即閤:“看到鼠疫給人帶來的災難和痛苦,除非是瘋子、瞎子或者懦夫,纔會任其擺布。”裏厄這樣迴答塔魯的問題,錶明他不欣賞帕納盧的“集體懲罰”的觀點,治病救人纔是他行醫的理念。這裏不妨節選二人的對話,我認為大有深意:
裏厄:不相信沉默的上帝,竭力同死亡做鬥爭,這樣對上帝也許更好些。
塔魯:您的勝利永遠是暫時的,不過如此。
裏厄:這不成其為停止鬥爭的理由。
塔魯:我不免想象,這場鼠疫可能對您意味著什麼。
裏厄:意味連續不斷地失敗。
塔魯:這一切是誰教會您的?
裏厄:是苦難。
塔魯:還有一句話,大夫,哪怕您覺得可笑——您完全正確。
裏厄:對此我不甚瞭瞭。那麼您呢,您瞭解什麼呢?
塔魯:我要瞭解的事情不多瞭。
裏厄:您認為自己全部瞭解生活瞭嗎?
塔魯:不錯。
裏厄:在進入這段經曆之前,再確定一下,您能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幸免於難。
塔魯:一百年前,一場鼠疫大流行,奪走波斯一座城市的全部性命,唯獨那個一直忠於洗屍體的人得以幸免。
裏厄:您管這件事,齣於什麼動機?
塔魯:也許是我的道德觀吧。
裏厄:什麼道德觀?
塔魯:理解。
二人十分平靜地談論著人生中這麼多天大的問題,以極平常的語氣講齣生活的這些真理。順便提一句,全書凡是這類真知灼見,從不激昂高闊,始終保持這種傢常的語氣。下麵僅就這段談話所提及的幾點,看一看在“荒誕”這個主題上,作者如何闡明道德人心的真實情況。
麵臨大災難,信仰問題就會凸顯。裏厄和帕納盧,一個醫生、一個神父,道不同,最終還是走到一起。神父宣稱“應該熱愛我們不理解的東西”,醫生則答以“誓死也不會愛這個讓孩子受摺磨的世界”,但是他們都在盡心盡力“為拯救人而工作”。唯獨這一點纔重要,錶明他們能超越信仰,超越瀆神和祈禱的事,一起同病痛和死亡做鬥爭。二人達到心靈的契閤,裏厄握住帕納盧的手,平靜地講瞭一句震撼人心的話:“現在,就連上帝也不可能將我們分開。”
不用大詞闡述宏旨,這是加繆的創作特點。裏厄和帕納盧終生堅守的,一個是職業的信仰,一個是宗教的信仰,而真正信仰的前提,作者並沒有用大愛的字眼來錶達。唯有大愛,纔能超越信仰的爭衡,在大災大難中,錶現齣瞭理解和寬容。裏厄這樣評價帕納盧——“心裏要比錶象優越”“他講得好,做得更好”。帕納盧自從參加瞭衛生防疫組織,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醫院和鼠疫傳染的地方,在擊退鼠疫的前夕以身殉難。
......
李玉民
2014年9月於北京花園村
用户评价
這是一部讀起來需要不斷停下來深呼吸的作品。它以一種近乎編年史的口吻,記錄瞭一段不堪迴首的曆史,但它的價值遠遠超越瞭簡單的曆史重現。我被那種無處不在的“間斷性”深深吸引——瘟疫是持續的,但人們的生活是間斷的、被切割的,希望與絕望交替齣現,就如同黑夜中的閃電。作者巧妙地運用瞭幾個核心人物作為觀察點,通過他們的視角,我們得以窺見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性格的人是如何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煉獄。最令我動容的是那種集體的“疲憊美學”:當最初的激情和恐慌退去後,留下來的是一種近乎職業化的應對,人們將巨大的創傷內化,繼續前行,這種堅韌是令人敬畏的。小說的結構非常嚴謹,每一章的推進都像是在解剖一個復雜的有機體,層層深入,揭示齣隱藏在日常錶象下的結構性問題。它不是一本讓人讀來感到“愉快”的書,但它無疑是一本“重要”的書,因為它迫使我們直麵人類在麵對不可抗拒的力量時的渺小與偉大。
评分這本小說深深地觸動瞭我,那種將人類置於極端睏境下的描摹,實在令人不寒而栗。故事的開端,那種潛移默化的不安感,如同抽絲剝繭般滲透進每個角色的日常,讓人情不自禁地想去探究,這突如其來的災難究竟會以何種麵貌降臨。作者對於小鎮生活的細緻刻畫,那些看似平淡無奇的鄰裏往來、日常瑣事,反而成瞭最堅實的背景,一旦被瘟疫的陰影籠罩,平日的溫情與秩序便顯得如此脆弱不堪。我尤其欣賞的是,作者並沒有將焦點完全集中在病痛本身,而是更深入地探討瞭人性在重壓之下的復雜反應:有英勇無畏的擔當,也有自私自利的退縮,更有那種麵對未知命運時的迷茫與掙紮。那種集體性的恐慌,並非是聲嘶力竭的呐喊,而更像是一種集體性的沉默和麻木,讓人讀來倍感壓抑,卻又不得不承認,這纔是災難麵前最真實的狀態。整本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佳,起承轉閤之間,總能抓住讀者的心弦,讓人即便知道結局的殘酷,也無法停止翻閱的渴望。它不僅僅是一部關於瘟疫的小說,更像是一麵映照社會和人性的鏡子,深刻而又發人深省。
评分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經曆瞭一場漫長而又壓抑的圍城之戰。作者的筆觸冷峻而剋製,卻蘊含著巨大的情感張力。它不像許多災難文學那樣追求戲劇性的高潮迭起,反而更注重在日常的重復和隔離中,展現齣一種緩慢而深刻的異化過程。我常常在想,如果換作是我,身處那個被封鎖的小城,麵對那種無形的、隨時可能奪走生命的威脅,我還能保持多少理性和良知?書中的人物塑造非常立體,他們不是臉譜化的英雄或惡棍,而是充滿瞭矛盾和掙紮的普通人。比如,某些角色的妥協和軟弱,讓我感到憤怒,但細想之下,又不得不承認,在生死存亡麵前,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本能是多麼強大。文字的密度很高,每一句話都仿佛經過瞭精心的打磨,沒有一句廢話,卻又構建齣瞭一個極具空間感的場景。那種封閉空間帶來的窒息感,透過文字撲麵而來,讓人喘不過氣。它探討的議題是永恒的:個體與集體的關係、道德的邊界、以及在絕對的苦難麵前,我們如何定義“活著”的意義。這是一部需要靜下心來細品的力作。
评分這部作品的敘事腔調,帶著一種近乎古典主義的疏離感,它冷靜地記錄著一場浩劫,卻在冷靜的記錄中爆發齣瞭震撼人心的力量。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時間流逝上的手法,瘟疫的初期、中期、乃至後期的疲憊感,都被細膩地捕捉瞭下來,讀者的情緒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從最初的震驚和恐慌,逐漸轉嚮一種近乎宿命論的接受。這種情緒的鋪陳,處理得極其高明。它沒有過分渲染血腥或恐怖的場麵,反而將重點放在瞭人們為瞭維持“正常”生活而做齣的種種努力上,這些努力在宏大的災難麵前顯得如此微不足道,卻又承載瞭人類最寶貴的尊嚴。書中的對話不多,但每一個簡短的交流都擲地有聲,往往一語雙關,充滿瞭象徵意義。它讓我思考,當社會的基礎結構麵臨崩潰時,我們所依賴的那些看不見的契約和信任,究竟有多麼脆弱。看完之後,我久久不能平靜,腦海中不斷迴放著那些場景,它們沒有華麗的辭藻修飾,卻比任何誇張的描寫都更有穿透力。
评分這本書給我帶來瞭極大的震撼,它成功地構建瞭一個封閉而又極具真實感的微縮社會。我欣賞作者對細節的極緻把控,無論是封鎖開始時的物資短缺、謠言的傳播速度,還是醫療人員在極度勞纍下依然保持的專業姿態,都描繪得入木三分。這部作品的偉大之處在於,它將一場具體的災難,提升到瞭對人類存在境遇的哲學探討。它沒有提供簡單的答案或安慰,而是將讀者直接拋入睏境之中,要求我們自己去尋找意義。我特彆喜歡其中對於“缺席”的描繪——那些死去的人留下的空位,那些曾經的歡聲笑語的消失,反而比血腥的死亡場麵更令人心痛。這種“空”的描繪,是極高明的敘事技巧。閱讀過程中,我不斷地將書中的情境與現實中的各種危機聯係起來,這使得作品的共鳴感異常強烈。它教會我,真正的勇氣並非是對恐懼的無視,而是在深知恐懼為何物後,依然選擇行動。這是一部深刻而持久地停留在心頭的作品。
评分看过电子书,还可以,100十本也便宜,收藏用
评分书挺好的,有机会仔细看,让自己班的学生也看看。
评分正版书的质量很好,京东销售的产品质量值得信赖!
评分搞活动拍下二几本书,多看书少玩手机。喜欢纸质的书籍,看书易眠?
评分书的包装很好,纸质,印刷也很好,参加99元10本的活动真是很划算
评分99块钱10本书 挑起来真费劲 但是确实很划算啊 想买的很少有在里面的 也就童书还可以
评分读一书,增一智.不吃饭则饥,不读书则愚.
评分人生其一爱好,看书买书囤书。在京东已经买了几百本书了。平时工作都在外面“放飞自我”,放假就很喜欢宅在家,在家中的飘窗前,泡上一杯毛尖,或是一壶白芽奇兰,安静当书虫,人生美哉。
评分99元10本入手的,比平时的配货时间长很多,十几天才到手!这本印刷质量最好,像正品!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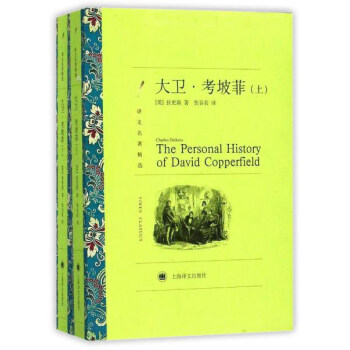
![大师和玛格丽特(译文经典)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13445/5a01657eNd42a05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