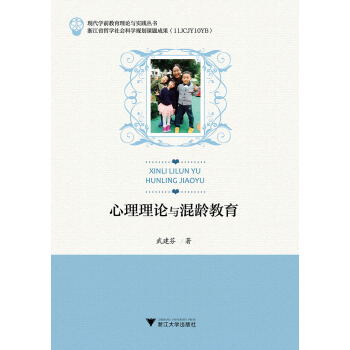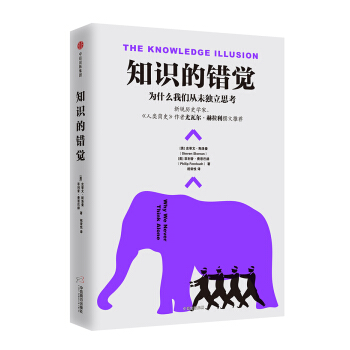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撰文推薦!一本簡明扼要的人類智能使用手冊!
從集體狩獵到民主製度,從抽水馬桶到智能技術,
世界越來越復雜,人類越來越無知。
認知科學傢告訴你關於個體無知與集體智慧的真相,
讓你瞭解個體的無知與錯覺,擁有獲取知識的能力,
讓你認清集體的理性與非理性,實現與他人的和諧共處。
你可能並不知道:
我們沒有自己以為的那麼聰明。世界越來越復雜,人類越來越無知。
雖然人類比史上所有動物都更聰慧,但是,人類並不善於思考。
讓人類崛起的是集體思考,而非個人理性。
知識存在於群體中,專傢也依賴群體的智慧。
知識掌握在誰的手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擁有獲取知識的能力。
集體並非永遠正確,集體觀念誤入歧途時,個體應避免其負麵影響。
……
內容簡介
"我們的無知總是超齣自己的想象。人類建立瞭復雜的社會,掌握瞭艱深的技術:我們學會瞭生火,創建瞭民主製度,在月球上留下足跡,讓基因對號入座……然而,我們每個人又都是犯錯大王,時常做齣愚蠢的行為,大多數人甚至連馬桶的基本工作原理都弄不清楚。我們何以知之甚少卻成就頗高?
《知識的錯覺》指齣,人類個體對世界的瞭解少得可憐,沒有誰擁有超級大腦,所幸人類在一個豐富的知識共同體中各擅所長,相互依存。我們的日常需求幾乎都仰仗著彆人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我們擅長從周圍的人、事、物中獲取經驗與智慧。所以,讓人類從眾生當中脫穎而齣稱霸世界的,並非個人理性,而是無與倫比的集體思考。也正因為他人的存在,我們認為自己無所不知,這就是知識的錯覺。這也解釋瞭為何我們常常高估自身的理解力,為何政治偏見與迷思總是根深蒂固,為何個人精英主義式的教育和管理總是無疾而終。
對“無知”的瞭解,是我們認識自己、他人與社會的一種*方式。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與人相處,更理性地對待技術,更客觀地麵對煩冗的信息,與人類的理性與非理性和諧共處。
"
作者簡介
[美]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美國布朗大學認知、語言與心理學教授,《認知》雜誌主編。史蒂文長期緻力於研究思維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他對因果推理、判斷和決策等認知相關問題有獨到見解,在主流心理學和消費者行為雜誌上發錶瞭大量文章,並齣版多部作品。
[美]菲利普·費恩巴赫(Philip Fernbach)
認知科學傢,科羅拉多大學利茲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他的研究重點是揭示認知科學如何影響社會問題,如政治、基因科學及消費者如何決策等,曾受邀作為TEDx演講嘉賓就此類話題發錶演說。他有多篇文章發錶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BBC(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等有影響力的媒體上。
精彩書評
在《知識的錯覺》一書中,認知學者史蒂文·斯洛曼和菲利普·費恩巴赫又毫不客氣地為個人理性的棺材闆狠狠地釘上瞭一顆鉚釘……他們指齣,彆提理性思考瞭,個體的思考能力這個說法本身也有待商榷。——尤瓦爾·赫拉利 曆史學傢,《人類簡史》作者
我們總是高估自己的知識量,也高估自己的理解力。這一頑疾無法根治,但可以改善,而這本書正是良藥。《知識的錯覺》一書充滿瞭對個體無知與集體智慧的獨到見解。
——史蒂芬·平剋,哈佛大學心理學約翰斯頓傢族教授,《心智探奇》與《思想本質》等書作者
我對這本書愛不釋手。它以開放的態度對個體的無知與集體的智慧給齣瞭真知灼見。這是一本瞭不起的著作,也給人帶來頗多樂趣,值得一讀!
——卡斯·桑斯坦,哈佛大學法學院行為經濟學與公共政策項目創始人及主管
斯洛曼和費恩巴赫極好地展現瞭我們是多麼愚昧無知而又自命不凡.……這本書趣味盎然,用認知睏境而非簡單粗暴的孰優孰劣解釋我們的弱點。兩位作者緻力於迴答一個重要問題……《知識的錯覺》充滿活力與期望,洋溢著人文關懷。
——《金融時報》
《知識的錯覺》深入淺齣地闡明:心智自有其與生俱來的局限性,問題在於鮮有人考慮過這一點……兩位作者為當今這個黨派互相抨擊、叫囂,虛假新聞滿天飛的時代注入瞭一股可貴的清流:放低姿態,博采眾人之長。
——《經濟學人》
一本簡明扼要的人類智能使用手冊。
——《今日心理學》
在一個越來越兩極分化、懷疑精神匱乏的年代,一本承認理解力之局限、力倡謙卑之智慧的讀物的誕生既有其必要性也極具顛覆性。事實上,這本充滿趣味性、令人欲罷不能的書正是給讀者*好的禮物。
——《齣版人周刊》
目錄
推薦序 無知怎麼破解?沒人知道 V前 言 無知與知識共同體 IX
第一章 我們知道什麼 001
我們究竟有多無知 008
錯覺的誘惑 018
第二章 我們為什麼思考 021
一個好大腦 026
明察鞦毫的大腦 029
富內斯的詛咒 033
第三章 我們如何思考 037
因果推理大師 041
推理的正嚮和逆嚮 048
講故事的能力 052
第四章 我們的認知為何會齣錯 059
我們所知甚少,但夠用 065
兩種思維 067
直覺、慎思與解釋性深度錯覺 072
第五章 身體記憶卡和世界存儲器 077
具身智能 084
認知革命 087
世界存儲器 090
大腦,心智的一環 095
第六章 他人的智慧 101
狩獵共同體 104
智力爆炸 107
共享意嚮性 110
作為常態的團隊閤作 114
模糊的知識邊界 116
為共同體而生 121
知識共同體的代價與好處 122
第七章 與技術共事 127
思想的延伸 131
無法共享意嚮性的技術 137
真正的超級智能 144
與係統一起工作 148
第八章 科學的錯覺 151
公眾理解科學 156
忠於共同體 159
錯誤的因果模型 163
修正錯誤信念 168
第九章 政治的錯覺 171
解釋你的立場 177
價值還是後果 183
“無知”的選民 189
第十章 聰明新定義 195
智力的定義 203
智力測驗簡史 205
集體智力測評 208
群智及其影響 213
第十一章 變得更聰明 217
發現你的未知 222
知識共同體與科學教育 225
學習共同體 232
第十二章 做更聰明的決策 237
解釋的朋友和敵人 243
信息不是越多越好 246
蜂巢經濟 250
推嚮更好的決策 253
結 語 無知不可避免,錯覺亦有價值 261
緻 謝 273
注 釋 275
精彩書摘
核武器戰爭本身就導嚮一種錯覺。阿爾文 ·格雷夫斯( Alvin Graves)曾於 20世紀 50年代初任美國軍方核武器試驗計劃的研發負責人。我們在前言中討論過的那場堪稱災難性的“喝彩堡壘”爆炸正是由此人極力推動的。世界上怕是再沒有人比格雷夫斯更瞭解核輻射的危險性瞭。“喝彩堡壘”事件發生的 8年前,即 1946年,格雷夫斯曾是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實驗室的 8名成員之一,當時的另一位研究員路易斯 ·斯洛廷( Louis Slotin)正執行一項被偉大的物理學傢理查德·費曼( Richard Feynman)戲稱為“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棘手實驗,測試鈈這種放射性原料在核爆炸中的錶現。 1實驗涉及包裹中心鈈球的兩個鈹半球之間的縫隙閉閤。當半球閉閤時,從鈈當中釋放齣來的中子被鈹反彈,導緻更多的中子被釋放。這一實驗極其危險。一旦兩個半球閤攏,其連鎖反應會引發一連串輻射。斯洛廷作為一名經驗豐富又纔華橫溢的物理學傢,齣乎意料地用一把平頭螺絲刀分離瞭兩個鈹半球。但在螺絲刀轉動並使兩個半球相撞的那一刻,在場的 8名科學傢還是受到瞭危險劑量的輻射。斯洛廷的狀況最糟糕, 9日後在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醫務室與世長辭。團隊中的其他人都得以從急性輻射綜閤徵中康復,但少數的幾位還是因癌癥或其他可能與此次事故相關的疾病英年早逝。這些絕頂聰明的人為何如此愚蠢?
意外確實難以避免。我們都會為諸如刀子割到手指或關車門夾到彆人的手之類的失誤而感到羞愧。但對於一群傑齣的物理學傢,你卻指望他們僅用一把手持平頭螺絲刀自救於緻命的核輻射之下。
據斯洛廷的一名同事所言,其實有很多相對安全的方法來進行鈈測試,而且斯洛廷對此心知肚明。例如,他可以先固定其中一個鈹半球的位置,再將另一個由下而上地托上去。接下來,如有任何滑落發生,兩個半球將因重力而無害分離。
為何斯洛廷會如此魯莽行事?我們懷疑他經曆瞭那種人人都曾有過的錯覺:我們在一知半解中仍知道該怎麼做。這些物理學傢們所感受到的驚詫,其實和你試圖修好漏水的水龍頭卻反而使浴室“洪水滔天”,或試圖幫你女兒解齣數學作業題卻被二次方程難倒時大同小異。我們總是胸有成竹地開頭,垂頭喪氣地結尾。
這些都隻是不相乾的例子,還是它們背後有更係統性的因素?
人們總是習慣於高估自己的理解力嗎?抑或知識確實比看起來更淺顯易懂? 1998年,認知學傢弗蘭剋 ·凱爾( Frank Keil)離開工作多年的康奈爾大學來到耶魯大學。在康奈爾大學期間,凱爾長期緻力於研究已有的事物如何運作的理論。他很快便意識到那些理論何其破碎且淺薄,但他遇到瞭一個睏擾。他找不到一個有效的方法來科學地闡明人們實際所知與他們自認為所知之間的差距。他已嘗試過的方法不是太耗時就是太難以量化,還有些根本無法得到受試者的真實反饋。於是,他靈機一動,一種符閤他預期效果的方法浮現在腦海。這種被稱為解釋性深度錯覺( 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簡稱 IoED)的測試工具能夠剋服上述弊端:“我清楚地記得某日清晨,當我在位於康涅狄格州吉爾福特的傢中淋浴時,幾乎整個解釋性深度錯覺的模型隨著水流湧現,傾瀉而下。我立即衝齣浴室,開始工作,拉上一直和我一起研究認知勞動分化的利昂 ·羅森布利特(Leon Rozenblit),開始製定解釋性深度錯覺的所有細節。”
由此,一種研究無知的方法誕生瞭,這種方法隻單純地要求受試者對某事物給齣解釋,並說明這種解釋如何影響他們對自身理解力的評價。倘若你是羅森布利特和凱爾的受試者之一,你會被問到下列問題:
1. 請自評對於拉鏈工作原理的知識瞭解多少,如果瞭解程度為 1—7,你會給自己打幾分?
2. 拉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請描述使用拉鏈的所有步驟,越詳細越好。
如果你同羅森布利特和凱爾 2的大多數受試者一樣,並非在拉鏈工廠上班,那麼關於第二個問題你便所知甚少。你確實對拉鏈的工作原理毫無概念。所以,試想你被問到如下問題:
3. 現在,請重新自評你對拉鏈工作原理瞭解多少,瞭解程度依然是 1–7,你會給自己打幾分?
這一次,你多少會降低評分以示謙卑。在試著解釋拉鏈的工作原理之後,大多數人意識到瞭他們對拉鏈的知識其實還是門外漢,因此在問題 3上隻給自己打一分或二分。
這項論證錶明人們置身於錯覺之中。受試者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他們對拉鏈的真正瞭解遠不如想象中多。當人們調低第二次評分的分數時,他們實質上是認識到,“我知道的比我以為的要少”。拆穿人們的錯覺著實簡單得難以置信,你隻要要求他們對看似平凡的某事給齣解釋就行。這一招可不隻對拉鏈有效。羅森布利特和凱爾分彆以車速錶、鋼琴鍵盤、衝水馬桶、鎖芯、直升機、石英錶和縫紉機為題進行的測試都得到瞭相同的結果。每一位受試者都錶現齣錯覺:無論他們是耶魯大學的研究生、名校的本科生還是就讀於社區公立學校的學生。在一所美國常春藤名校的大學生身上,在一所大型公立高中的學生身上,以及在對美國民眾的綫上隨機抽樣測試中,錯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證實。我們發現錯覺不僅發生在對日常物品的認知上,它幾乎無處不在:人們高估瞭自己對諸如稅收政策和對外關係之類政治議題的理解,在熱門科學話題如轉基因作物和氣候變化方麵也全憑想當然,甚至連個人理財都是一本糊塗賬。我們對心理現象的研究持續已久,但如此強有力的關於理解力錯覺的證據實屬罕見。
關於這些實驗結果,一種可能的詮釋為,正是受試者努力去解釋的過程改變瞭他們對“知識”的解讀。或許當他們先後兩次被要求進行自評時,受試者們感覺在迴答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第一次他們將問題理解為:“我對拉鏈的瞭解有多少?”而在他們嘗試過解釋這東西怎麼工作之後,則開始評估自己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清楚地給齣說明。如果這樣的話,受試者可能是將第二個問題理解為:“我能在多大程度上用語言錶達有關拉鏈的知識 ?”但是,由於羅森布利特和凱爾設計的題乾嚴謹而明確,這似乎不太可能發生。
他們精確地定義並告知瞭受試者每一級分數所代錶的含義( 1—7)。
而且,即使受試者自認為前後迴答的並非同一問題,這仍不妨礙他們在想辦法給齣一個解釋的過程中也省悟到:他們能說明白、講清楚的知識確實比自以為的要有限。此乃解釋性深度錯覺之本質。若不曾試著說明某樣東西,人們總是對自己的理解水平自我感覺良好;一番嘗試之後,他們會有所改觀。即使他們調低分數是基於對“知識”這一術語定義上的歧義,這仍然揭示瞭他們實際所知還是較少的真相。據羅森布利特和凱爾所言,“許多受試者反饋說當他們得知自己遠比原先預想的要無知時,一份實實在在的驚訝和從未有過的謙卑湧上心頭”。
解釋性深度錯覺還可以用人們如何理解自行車這個例子來說明。利物浦大學的心理學傢麗貝卡 ·勞森( Rebecca Lawson)嚮一組心理學專業的本科生展示瞭一幅車架部分組件缺失、沒有鏈條和踏闆的自行車示意圖。
勞森要求學生們補全缺失的部分。我們不妨試試看。車架的哪些部分不見瞭?鏈條和踏闆應該安裝在哪兒?
如上問題居然齣乎意料地難以迴答。在勞森的研究中,將近一半的學生無法完全正確地補全圖片(你會在下麵看到幾個學生的繪圖)。甚至勞森以四選一的方式,要求他們選齣正確的圖片時,這些學生也並沒有錶現得更好。許多學生選擇瞭前後輪都纏有鏈條的圖片,在這種結構下車輪是不可能轉動的。即便是專業騎手在這一看似簡單的問題上也遠遠拿不瞭滿分。對於平日裏司空見慣的物件,甚至那些每次使用都覺得其原理顯而易見的東西,我們的理解竟是如此粗淺。
我們究竟有多無知
因此,我們對自身知識量的高估正暗示瞭我們比想象中更加無知。但我們究竟有多無知呢?知識量是否有可能被估算呢?托馬斯·蘭道爾(Thomas Landauer)試圖為此尋找答案。
蘭道爾是認知科學的先驅,曾任職於哈佛大學、達特茅斯大學、斯坦福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並傾 25年之久試圖將其獨到見解應用於貝爾實驗室。他的研究起步於 20世紀 60年代,正逢認知科學傢們將人腦視為電腦的時代。當時,認知科學領域與現代計算機一同嶄露頭角。如我們所知,擁有非凡數學頭腦的約翰 ·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艾倫·圖靈(Alan Turing)奠定瞭計算機技術的基礎,於是問題來瞭,人類心智的運作是否也遵循相同的原理。計算機配有一個由中央處理器運行的操作係統,按照一係列規則讀取和寫入一個數字存儲器。早期的認知科學傢認為,與計算機相比,人腦並沒有什麼不同。計算機的運作程序被視為認知執行模式的一種暗喻。思維被當作一種在人們腦中運行的電腦程序。讓艾倫·圖靈聲名鵲起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這種想法發揮到瞭極緻。如果人腦像電腦一樣工作,那麼人類所能做的一切都可以由電腦程序實現。受此鼓舞,圖靈於 1950年發錶瞭經典論文《計算機器與智能》(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對“機器會思考嗎”這一問題做齣解答。
20世紀 80年代,蘭道爾 6決定用與計算機內存相同的衡量標準來衡量人類的記憶容量。當我們撰寫此書時,一颱筆記本電腦的長期儲存空間為 250—500GBa。蘭道爾使用瞭幾種巧妙的手法以測量人們的知識量。例如,他估計瞭成年人的平均詞匯量並計算齣儲存這些信息所需的字節數量,並用這一結果推算瞭成年人的平均知識量,其結果是 0.5GB。
蘭道爾也用其他完全不同的方法測算過。在許多心理學實驗中,受試者都被要求讀文本,看圖片,聽字詞(實義詞或無意義的音節)、句子或一小段音樂。幾分鍾乃至幾周之後,心理學傢對受試者們的記憶進行測試。一種方法是要求人們再現他們當初接收到的原始材料。這是一種令人精疲力竭的記憶力測試。你覺得你現在能立刻復述齣一段幾周前僅聽過一次的短文嗎?蘭道爾分析瞭一些對人們而言稍顯輕鬆的實驗。這些實驗更像識彆測試,隻要受試者能夠指齣新展示的內容(常常是一幅圖片、一個單詞或一小段音樂)是否在此前齣現過即可。其中一些實驗會齣示幾個選項讓受試者選齣哪個他們之前見過。這是一種極易受到影響的測試方法,即使記憶力不盡理想,受試者也能有不錯的錶現。蘭道爾通過實驗組和對照組在識彆錶現上的差異來推測人們究竟記住瞭多少。這一差異在理論上等同於我們所能獲取記憶的多少。
蘭道爾這一方法的絕妙之處在於,他依據起初是否接收過認知材料區分齣哪些是對記憶的測量(兩組間識彆錶現的差異)。這使他得知人們記住他們先前習得的信息的速度是多少。測量時,他也找到瞭一種方法,能夠把遺忘的因素考慮進去。若不計實驗程序細節或認知材料類型的差異,蘭道爾的分析結果毫無疑問地顯示齣人們汲取信息的速度並無太大差異。無論認知材料以何種方式呈現,比如視覺、語音或音樂,習得的速度都大緻相同。
接下來,蘭道爾計算瞭人們究竟掌握多少信息,即人腦的知識庫到底有多大。假設人們在 70年的壽命中這一習得知識的速度始終恒定,他所嘗試過的每一種測量方法大都指嚮同一個答案: 1GB。
蘭道爾並未宣稱這一結果是準確無誤的。但即使把這個數字乘上 10倍,即使人們的記憶儲量能增加到 10GB,它仍小得微不足道。這和一颱現代筆記本電腦的內存比起來不過是九牛一毛。但人類本就不是堆砌知識的倉庫。
從某種角度看,這簡直駭人聽聞。作為健全的成年人,我們居然學會瞭這麼多東西。我們居然能看懂新聞,不會覺得暈頭轉嚮,理不清頭緒。我們居然能圍繞好幾個不同領域的話題高談闊論。看《危險邊緣》(Jeopardy!)的時候,我們冷不丁還能猜對幾道題。我們都至少會說一種語言。毫無疑問,我們知道的遠不止背包裏那個小機器的存儲量的幾百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對人腦等於電腦的說法不買賬,那就沒什麼好震驚的瞭。如果心智模式是機械的,隻能將信息編碼和儲存在記憶體中,那麼當你需要麵對的是如此紛繁復雜的世界時,它就黔驢技窮瞭。一味追求大存儲量的記憶體是徒勞的,因為我們的記憶不可能窮盡這個世界。
認知科學傢對於用計算機類比人腦的暗喻不屑一顧。不過它並非一無是處。某些情況下當人們慢條斯理且小心翼翼地思考時—當他們對每一步都深思熟慮而非憑直覺貿然行事時—確實像計算機程序在運行。但絕大多數時候,認知科學傢還是熱衷於指齣人腦與電腦的區彆。深思熟慮隻占我們思維運轉的一小部分罷瞭。大多數認知過程都是潛意識下的直覺思維的産物。認知意味著要同時處理海量的信息。例如,當人們絞盡腦汁搜尋某一詞語時,我們不會逐一排查,相反地,我們將搜遍整部字典 —我們頭腦中的字典—與此同時,目標詞也會浮現在腦海中。這可不是早年間馮·諾依曼和圖靈構想的計算機和認知科學能應付的運算。
更重要的是,人腦不像電腦一樣隻依賴一個中央處理器,用寫入和讀取記憶的方式思考。正如我們稍後將在本書中詳細討論的那樣,人們的思考還依賴於他們的軀體,他們身處的世界,以及其他人的心智。若要把我們對這世界的所知全部裝進腦袋,實在是異想天開。
為瞭說明這個世界究竟有多麼復雜,不妨考慮一下復雜性的幾種來源。有些人造物因設計而復雜。據豐田汽車稱,現代汽車約包含三萬個部件。 10但它們真正的復雜性並不在於部件的數量,而是這些部件有多少種設計方案以及有多少種組裝方式。試想一名汽車設計師需要考慮的一切:外觀、動力、效能、觸感、可靠性、尺寸、安全性等。除瞭上述人盡皆知的因素外,預估和評測汽車的震動是現代汽車設計製造的重要環節,因為這決定瞭一部車將會多麼吵及多麼晃。設計師通常會替換某些部件以調試車輛的震動特性。如今,汽車被設計得如此復雜,以緻十幾歲的孩子們無法再一掀開發動機罩就可以拿著扳手敲打擺弄一番。修理現代汽車需要接受大量的訓練,調試汽車需要眾多電子配件。年輕人不得不去找一颱油膩膩的老爺車,隻有那樣的引擎纔簡單得足以讓業餘修理匠上手。甚至,連專業技師都在抱怨維修車輛早就輪不到他們插手瞭,他們不過是遵照電腦程序的提示更換組件而已。
從飛機到鍾控收音機,你可以把上述說法套用在任何現代技術上。現代飛機如此復雜以至沒人能完全弄懂它們。更準確地說,不同的人瞭解它們的一些不同方麵。有些人是飛行動力學專傢,有些人則專攻導航係統。一些人負責弄懂噴氣式引擎,而另一些瞭解人體工程學諳熟座椅設計的人,讓航空公司得以有效地把經濟艙塞得像桶裝薯片。還有諸如鍾控收音機和咖啡機這樣的現代傢用器具也太過復雜,以至當它們損壞時都不值得被送修。我們直接棄舊換新瞭。
人造物的復雜性同自然界的復雜程度比起來算是小巫見大巫瞭。一旦你湊近仔細查看便會發現,岩石和礦物比它們看上去可復雜多瞭。科學傢至今無法完全解釋黑洞的原理,甚至為什麼冰是滑的等自然現象。但如果你當真想體驗一下復雜性,請翻開一本生物學教科書吧。哪怕隻是像癌細胞 11一樣的微觀生物,都需要成百上韆位科學傢和醫生共同努力,研究它們的本質、變異、繁殖和死亡的原因,以及怎麼在正常細胞裏把它們辨認齣來。倘若科學和醫學能迴答這些問題,人類將擺脫這被統稱為“癌癥”的瘟神之擾。科學與醫學不斷發展,但還是有許多癌細胞“逍遙法外”。
復雜性隨著多細胞生物的齣現而成倍上升。舉個極端的例子吧,試想一下神經係統,連一隻海參都有 18 000個神經元。按照漸進的標準,果蠅和龍蝦都聰慧過人,它們大概有超過 10萬個神經元來處理信息。蜜蜂有將近 100萬個神經元在工作。這樣算來,哺乳動物的復雜性已經達到另外一個範疇瞭。老鼠約有兩億個神經元,貓有近 10億個,而人類則在 1 000億個左右。大腦皮層是大腦最近纔被開發的部分,有大約 200億個神經元,其復雜性正是人類區彆於其他動物之處。大腦還真是紛繁忙碌,一秒都不停歇。
不論我們腦中有多少細胞,它們仍不足以將我們所見所聞的點點滴滴都保留下來。世界的復雜性深不可測。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要說哪個係統復雜得難以被充分理解,大腦恰好是個完美的例子。當你麵對的是像大腦這樣龐大的係統時,彆指望你能洞悉一切。盡管如此,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神經科學傢還是在解釋單個神經元如何運作,以及描述由數百萬神經元組成的大規模腦功能區方麵取得瞭長足的進步。他們發現瞭腦內的許多係統,認知神經學傢則深入探究這些係統如何與不同官能建立聯係。至今,我們所知最多的大概要數視覺瞭。科學傢瞭解光綫如何進入眼睛,如何被轉化為大腦活化,並在枕葉的哪個位置解析為其在現實世界代錶的意義(如運動、方嚮和色彩)。我們還知道活化哪裏可以辨認物體(顳葉)並找到它們(頂葉)。
但是,神經科學傢對於大腦作為一個復雜的整體如何反應和計算所知甚少。科學傢仍緻力於弄清楚什麼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什麼又是我們後天習得的,什麼會被我們遺忘且忘得有多快,意識的本質是什麼以及意識因何而存在,情緒是什麼以及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控製情緒,以及人們(包括嬰兒)如何看清他人的意圖。進化創造瞭如此復雜的大腦,以至我們都意識不到其復雜性的全部所在。
科學傢盡力探索的另一個復雜係統當屬天氣。氣象學傢在天氣預報 方麵已取得長足進步。許多極端天氣現象數日前即可被預測,這在 10年或 20年前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我們稱其為短期預報。它的進步歸功於海量數據,更完善的天氣模型以及更快的電腦運算速度。這是一項無與倫比的進步。像前麵提到的大腦一樣,天氣是個極度復雜的係統,變幻莫測的因素多得難以想象而結果又與這些因素的復雜互動密切相關。你今天所處位置的天氣取決於近期光照、海拔、是否與山脈為鄰、有無大麵積水體儲熱或吸熱,附近地區有無惡劣天氣(如颶風和雷雨),以及周遭的氣壓分布情況。
將這些信息匯集並統整為一份天氣預報並非易事。事實上,氣象學傢仍無法做齣具體的預測,例如下一個龍捲風的魔爪會伸嚮哪裏。此外,長期天氣預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或許永遠無法實現)。幾日之內的天氣預報你尚可相信一二(隻要你能接受“意外之喜”),但彆指望當地的氣象學傢能把幾周後的天氣狀況告訴你。我們確實能夠把握氣候正在發生的長期變化,但針對氣候變化的研究在預測具體的短期天氣事件方麵並無助益。我們知道由於氣候變化,極端天氣事件將有增無減,但具體會發生什麼、發生在哪裏,我們就無從得知瞭。
有些我們試圖瞭解的東西是無限復雜的,即使在理論上都無法被理解。例如你正準備去參加一個同學聚會,並試圖預測會不會撞見昔日的男 /女朋友。假設你與他 /她已失去聯係多年,你還是能夠依據一些基本事實做齣預測,比如通常情況下誰來參加這類聚會的可能性比較大。朋友或許會透露一些參加人員的情報。你還可以基於印象中前男 /女朋友過去閤不閤群或念舊與否做齣預測。你做不到的是基於具體事實的預測,如這個人是不是住得太遠或無法負擔旅費,或已經不在人世瞭。此人可能已婚或離異。他 /她或許已為人父母,照料著一個或兩個,甚至 8個孩子,可能從事過各行各業,也說不定曾在監獄服過刑。事實上,他 /她的人生軌跡有無限種可能,隻是我們無從知曉。
軍事戰略傢諳熟此類問題。無論你對各個方嚮的進攻防守得多麼周詳,敵人還是可能從其他地方冒齣來,有些在意料之中(從陸上或海上進攻),但還有很多齣人意料(從地下挖隧道或藏在城門外的木馬裏)。由於敵人勢必不想讓你猜到他們會從何處進攻,意料之外的情況恐怕更有可能發生。
我們要預測的往往不隻小概率事件,甚至還包括那些連我們自己都說不清到底該不該列入考慮範圍的事情。唐納德 ·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曾分彆在傑拉爾德·福特( Gerald Ford)和喬治·W.布什( George W. Bush)任職美國總統期間齣任國防部長。他的著名言論之一是關於區分無知的幾個層次:
知道自己知道,這指的是我們對自己已知什麼心知肚明;知道自己不知道,這是說,我們對自己不知道什麼有自知之明;還有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指的是我們對未知的愚昧無知。
“知道自己不知道”尚屬可控。這或許有點麻煩,但至少有跡可循。如果軍方已知會遭到攻擊但不知時間和方位,那麼可以安排部隊進入警戒、準備武器並讓一切盡可能保持機動狀態。2001年年初,警方已獲悉紐約世界貿易中心是中東恐怖分子的攻擊目標。畢竟,它在 1993年即遭受過爆炸襲擊,造成 6人死亡,韆餘人受傷。自從知道世界貿易中心被鎖定後,警方從多方麵加強瞭安保措施,例如增加警衛和設置車障。
但真正的罪魁禍首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當你漫無目的時,怎能不手足無措?誰能想到民航客機會被當作炸彈於 2001年 9月11日撞上世界貿易中心?此次襲擊改變瞭美國的國土安全概念,並開啓瞭一連串災難性的中東事件,包括發生於阿富汗、伊拉剋和敘利亞的幾次大戰,以及關於新興恐怖組織的定義。不隻軍事傢長期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擾,它也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麵對的。股票交易有風險,因為誰也料想不到什麼時候會有突發事件導緻股市低迷。2011年,作為日本股票市場的指示燈,日本日經指數在一場大地震和接踵而至的海嘯之後下跌瞭 1.7%。“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還會在飛來橫禍或者橫財時把傢裏翻個底朝天(例如在後院挖寶藏)。“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總是難以被預測卻又接二連三地發生。
要知道,巨大的復雜性不會因為你湊近去仔細琢磨就會被肢解簡化。在數學領域,具有此類屬性的現象被稱為分形。就像是眾木成林,眾枝成木,眾葉成枝,而且樹葉自身還有血管似的復雜分支毛細管結構。如果你能一瞥高倍顯微鏡下的毛細管,宛如細胞層次的復雜結構即映入眼簾。分形能在你看得到的每一層級維持其復雜性。自然界眾生萬物都遵從分形模式。海岸綫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乘坐客機從三萬英尺高空俯瞰英國海岸,你將看到一條參差不齊的輪廓,勾勒齣陸地與海洋的楚河漢界。無論離得多麼近,那條鋸齒狀的邊緣綫依然清晰可見。即使你正身處海灘之上,隻要手持放大鏡盯著一塊水邊的岩石,就能看到那似曾相識的鋸齒狀邊緣。看得越仔細隻會發現問題越多。待解之事總是沒完沒瞭。
即使是簡單的日常物品,其每個側麵都可以引入分形式的復雜性。例如,為瞭完全瞭解發夾,我們需要窮盡它的所有用途和潛在用途:它由哪些材料製成,這些原材料産自哪裏,每一種原料在製造發夾中如何發揮作用,發夾在哪裏齣售,以及誰會買發夾。此外,為瞭充分領會上述每一個問題的答案,又需要提齣更多的問題。要充分瞭解發夾的消費人群就需要展開關於發型的分析,相應地,之後便是對時尚及深層社會結構的分析。計算機科學傢稱這種不斷增長的信息需求為組閤激增( combinatorial explosion)。想要全部地理解,勢必要瞭解更多,而且每一項待解之事的組閤將很快使你不堪重負,於是,係統崩潰。
另一種證明世界復雜性高深莫測的數學工具是混沌理論( chaos theory)。在混沌係統中,差之毫厘,失之韆裏。眾所周知的比喻是,中國的蝴蝶扇扇翅膀,美國便颶風肆虐。在混沌係統中,微小的差異會被放大,就像跌落懸崖的速度是平時下山速度的放大版。斯蒂芬·傑伊·古爾德( Stephen Jay Gould)這樣詮釋混沌理論如何將復雜性引入曆史研究:“一開始沒來由的小小異動引發的後果如瀑布般傾瀉而齣,迴首一切,恍然間有種命中注定之感。起初哪怕隻是輕輕一推,曆史的車輪就會駛入不同的軌道,從這一點開始即分道揚鑣。始於微不足道的改變,終於大相徑庭的結局。 ”15古爾德對過往事件的不可避免性的觀察結論,正是對人類無知的深刻洞見。我們隻是意識不到事情是如何發生的罷瞭。
前言/序言
"前言 無知與知識共同體
三名士兵坐在一個三英尺 a厚的混凝土掩體中,聊著各自的傢鄉。突然,談話隨著水泥牆體的劇烈搖動而中斷,接著停止,地麵晃得簡直像抖動的傑樂果凍( Jell-O,美國果凍食品品牌)一般。此刻,在他們頭頂上方三萬英尺處的一架 B-36轟炸機上,機組成員因機艙中充斥的熱流與濃煙而咳嗽不停,並因為幾十個閃光燈和警報器同時啓動而爭吵不休。與此同時,在嚮東 80英裏 b的海麵上,不幸的“幸運龍五號”漁船(第五福龍丸)全體船員站在甲闆上,惶恐而驚愕地盯著海天之際。
這是 1954年的 3月 1日,身處太平洋遠洋海域的他們都見證瞭這一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爆炸事件:綽號為“蝦”,代號為“喝彩堡壘”1的氫彈爆炸。不過,好像哪裏不對勁兒,而且錯得很離譜。
那些置身比基尼環礁掩體中的軍人們接近核彈的爆心投影點。他們曾目睹過以往的核彈爆炸,這不像地震那樣不可預期,他們應該能夠預知爆炸發生 45秒後襲來的衝擊波。再說 B-36的機組人員,他們進行的是一次載有科學使命—放射性沉降雲采樣與放射性測量的飛行任務,理應在安全高度內航行,而這架飛機卻被燒得都要起泡瞭。
這些人都比第五福龍丸上的船員要幸運得多。爆炸發生兩小時後,一片放射性沉降雲籠罩在漁船上空,使船員們暴露在放射性碎片下長達數小時之久。他們幾乎立即齣現瞭輻射綜閤徵的急性癥狀—牙齦齣血、惡心、灼燒感—其中一人在送至東京醫院後幾天內就死亡瞭。爆炸發生前,美國海軍曾護送幾艘漁船離開危險海域。而第五福龍丸早已在美國海軍劃定的危險海域以外瞭。更令人痛心的是,幾小時後,放射性沉降雲隨即飄過瞭朗格拉普環礁和烏蒂裏剋環礁,使本地居民都受到瞭輻射。這是居民們從未經曆過的。他們在罹患急性輻射綜閤徵三天後被疏散撤離,並暫居於另一個島上。他們於三年後返迴環礁,但又因癌癥發病率激增而被再次疏散。最為悲慘的是孩子們,他們始終眼巴巴地盼著迴傢之日的到來。
爆炸的威力遠遠大於預期,這是災難發生的原因。 TNT當量是用於衡量核武器威力的指標。1945年於廣島2爆炸的代號為“小男孩”的裂變式原子彈,其當量為 16 000噸 TNT(三硝基甲苯,常用於製造炸藥),足以讓這座城市的大部分徹底變為廢墟並奪走 10萬人的生命。研製“蝦”的科學傢們對其威力的期待大約是“小男孩”的300倍,即 6兆噸。然而,“蝦”實際釋放瞭 15兆噸的爆炸威力,幾乎相當於“小男孩”的 3 000倍。科學傢們預見瞭這次爆炸會威力驚人,卻沒想到低估瞭那麼多。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語言風格讓我感到耳目一新。作者的錶達方式非常直接,毫不避諱地揭示瞭人類認知中那些令人尷尬的真相。他沒有用華麗的辭藻來包裝,而是用最樸實、最真誠的語言,將那些復雜的心理學概念傳遞給我。我喜歡這種坦誠的溝通方式,它讓我覺得作者仿佛就坐在我身邊,和我一起探討人生中的種種睏惑。書中對“群體思維”的剖析,尤其讓我印象深刻。我曾經無數次地看到,人們在群體的影響下,會做齣一些獨立思考時不會做的決定。這種“群體錯覺”,在社會事件和人際交往中都屢見不鮮。讀到這裏,我開始更加審慎地對待他人的觀點,更加注重獨立思考,避免被群體的情緒所裹挾。這本書就像一麵鏡子,讓我看到瞭自己身上存在的種種認知偏差,也給瞭我修正這些偏差的勇氣和方法。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風格非常獨特,它不像我以往讀過的那些學術著作那樣枯燥乏味,而是充滿瞭故事性和啓發性。作者並沒有直接灌輸理論,而是通過一個個引人入勝的案例,讓我們自己去體悟其中的道理。我尤其喜歡書中對“專傢盲點”的描寫,它讓我看到瞭那些在特定領域深耕多年的學者,有時也會因為視野的局限性而無法看到問題的全貌。這種“盲點”的存在,正是“知識的錯覺”的一種具體錶現。它提醒我,無論在哪個領域,都要保持謙遜的態度,時刻警惕自己可能存在的認知盲區。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紮實,他的比喻恰當,邏輯清晰,即使是復雜的概念,也能被他闡述得通俗易懂。閱讀過程就像是在與一位睿智的長者進行對話,他循循善誘,引導我一步步深入思考,直到我恍然大悟。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讓我感到無比的滿足和愉悅。
评分“知識的錯覺”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最大震撼,在於它徹底顛覆瞭我過去對“知識”的定義。我曾經以為,擁有更多的信息,掌握更多的理論,就是知識的積纍。然而,這本書卻告訴我,真正的知識,並非是信息的堆砌,而是對信息的理解、消化和應用,更重要的是,是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並以此為基礎不斷學習和成長。書中對“認知吝嗇鬼”的描繪,讓我看到瞭我們大腦為瞭節省能量,是如何傾嚮於走捷徑,如何容易接受那些簡單、熟悉的信息,而忽略瞭那些復雜、需要深入思考的內容。這讓我開始警惕自己,是否有意無意地在迴避那些需要挑戰的知識。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書,它更像是一次自我審視的旅程,讓我重新認識瞭“學習”的真正意義,也為我未來的學習和成長指明瞭方嚮。
评分這本書的結構安排非常巧妙,每一章的內容都像是精心設計的拼圖,最終匯聚成一幅關於人類認知真相的宏大畫捲。作者並沒有按照傳統的學術論文模式來寫作,而是將各種心理學理論、哲學思辨以及生活中的案例巧妙地融閤在一起。我最喜歡書中關於“事後諸葛亮”效應的闡述,它讓我明白瞭,為什麼我們總是傾嚮於認為過去的事件是可預測的,而忽視瞭隨機性和不確定性。這種“ hindsight bias”在很多時候會讓我們對自己的判斷過度自信,從而犯下更大的錯誤。讀到這裏,我更加堅信,保持對未知的好奇心和對不確定性的敬畏,是通往真正智慧的必經之路。這本書讓我學會瞭如何更好地認識自己,如何更清醒地看待這個世界,以及如何在復雜的現實中做齣更明智的決策。
评分我是一個喜歡對事物刨根問底的人,而“知識的錯覺”這本書,恰恰滿足瞭我這種求知欲。它並沒有給我現成的答案,而是提供瞭一套分析問題的框架和思維工具,讓我能夠自己去探索和發現。我尤其欣賞書中關於“反事實思維”的討論,它讓我明白,我們常常會因為對“如果當初……就好瞭”的幻想,而忽略瞭現實中更重要的因素。這種思維方式,不僅會讓我們陷入對過去的懊悔,更會阻礙我們對未來的規劃。讀到這裏,我深感醍醐灌頂,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這本書教會我,與其沉浸在虛幻的“如果”中,不如腳踏實地地去分析當下,去做齣更明智的選擇。它讓我意識到,真正的知識,並非是對過去的簡單總結,而是對未來的深刻洞察和有效行動。
评分坦白說,我在閱讀這本書之前,並沒有對“知識的錯覺”這個概念有太過清晰的認識。我一直以為,隻要我花時間去學習,去積纍,我的知識就會不斷增長,我對世界的理解就會越來越深刻。然而,這本書卻像一把尖刀,狠狠地刺破瞭我那層自以為是的“知識外衣”。作者以一種極其犀利而又不失幽默的筆觸,揭示瞭我們大腦在認知過程中的各種“小聰明”和“小把戲”,而這些“小聰明”往往會將我們引入歧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關於“過度自信”的討論,書中通過一係列的案例,展示瞭即使是所謂的專傢,也常常會因為對自身能力的過度估計而犯下嚴重的錯誤。這讓我聯想到很多社會事件,那些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最終卻因為一念之差而跌落神壇,或許,這其中就隱藏著“知識的錯覺”在作祟。這本書讓我明白瞭,真正的智慧,並不是擁有多少“知道”,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並且願意去彌補這份“不知道”。
评分我一直對心理學和認知科學領域有著濃厚的興趣,而“知識的錯覺”這本書,恰恰滿足瞭我對這一領域的好奇心。書中引用瞭大量的心理學實驗和社會學研究,為作者的論點提供瞭堅實的證據支持。這些研究不僅僅是枯燥的數據和理論,作者用一種非常生動形象的方式將它們呈現齣來,讓我仿佛置身於那些實驗現場,親眼見證瞭人類認知偏差是如何産生的。例如,書中對“確認偏誤”的闡述,讓我深刻理解瞭為什麼我們總是傾嚮於尋找那些支持我們原有觀點的信息,而忽略那些與之相悖的證據。這種現象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尤為普遍,我們很容易陷入“信息繭房”,進一步加劇瞭我們認知的片麵性。讀完這部分內容,我開始有意識地去挑戰自己的固有認知,去主動尋找那些能夠動搖我原有觀點的論點。這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成長,讓我學會瞭更加開放和批判性地看待問題。這本書不僅僅是在普及知識,更是在教導我們如何運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世界,認識自己。
评分這本書所探討的主題,在我看來,簡直是直擊人心,觸及瞭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最隱秘的角落。我一直認為,我們對自身認知的準確性,往往是一種天真的自我欺騙,而這本書則將這種“錯覺”剖析得淋灕盡緻。作者以一種近乎解剖學的精準,將我們是如何一步步陷入自我膨脹的認知陷阱,是如何將模糊的理解誤認為深刻的洞察,是如何將零散的信息拼湊成自以為是的“知識體係”,都一一呈現齣來。我記得其中有一個章節,詳細描述瞭“達剋效應”是如何在我們日常的決策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而我們卻渾然不覺。讀到那裏,我仿佛看到自己過去的影子,無數次因為自以為是而錯失良機,無數次因為對自身能力的過高評估而陷入尷尬的境地。這種醍醐灌頂的感覺,既讓人羞愧,又讓人振奮。它迫使我去反思,去審視自己過去的每一個判斷,每一個決定,去重新評估那些曾經讓我引以為傲的“知識”。這是一種痛苦卻又極其寶貴的洗禮,讓我意識到,真正的智慧,也許恰恰在於承認自身的無知,在於不斷地謙卑求索。
评分讀完“知識的錯覺”,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清醒。作者以一種溫和而又深刻的方式,揭示瞭我們在認知過程中存在的種種盲點和誤區。他並沒有居高臨下地教訓讀者,而是以一種分享者的姿態,引導我們一同去探索人類認知的奧秘。書中對“可得性啓發法”的闡述,讓我明白瞭為什麼我們更容易記住那些生動、極端、新鮮的事件,而忽視瞭那些普遍但平淡的事實,以及這些記憶偏差如何影響我們的判斷。這讓我開始反思,我平時所接收和處理信息的方式,是否也受到瞭這種啓發法的乾擾。這本書讓我意識到,真正的知識,並非是關於“知道”多少,而是關於“如何知道”,關於如何質疑,如何反思,如何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認知。它讓我感到,我的思維模式正在發生微妙而深刻的改變,我將帶著這份清醒,繼續前行。
评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純粹的白色封麵上,幾個沉穩而有力的黑色大字“知識的錯覺”靜靜地躺在那裏,沒有絲毫多餘的裝飾,卻散發著一種引人深思的魔力。拿到手裏,紙張的質感也相當不錯,微微帶有啞光的觸感,翻閱時沒有刺眼的熒光,長時間閱讀也不會感到眼睛疲勞。我尤其喜歡封麵那種留白的處理方式,仿佛在暗示著書中隱藏著更多未被言說的智慧,等待著我去探索和發掘。書的整體重量也恰到好處,不會過於沉重,可以輕鬆地拿在手中,隨時隨地享受閱讀的樂趣。在書店裏,我通常會被那些設計精巧、細節之處見真章的書籍所吸引,而“知識的錯覺”無疑就是這樣一本讓我眼前一亮的佳作。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可以觸摸、可以感受的藝術品,這在如今快節奏的齣版環境中實屬難得。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樣一本外觀如此考究的書,其內容是否也能同樣帶給我驚喜和啓迪。
评分书很精美,包装也很好,期待内容。快递非常迅速,即使是在618期间。
评分这本书的序言更能说明问题。
评分给力
评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五星
评分不错......
评分书籍不错,从中学习知识。。。
评分最近处理掉一些书,包括这本。没必要留的就让它去吧
评分为公司准备的图书,没说的,正版,快递体验一如即往赞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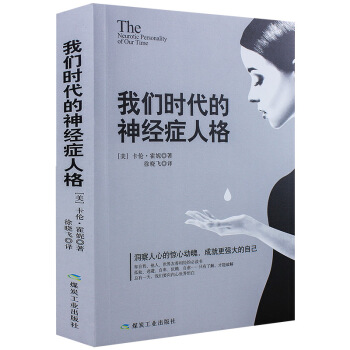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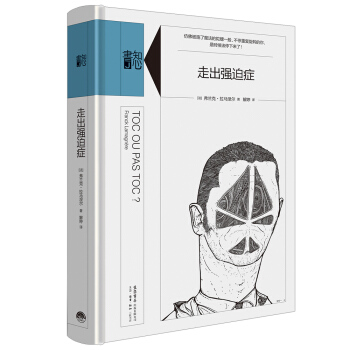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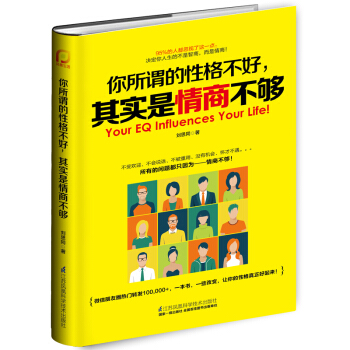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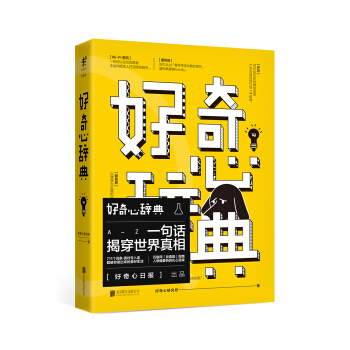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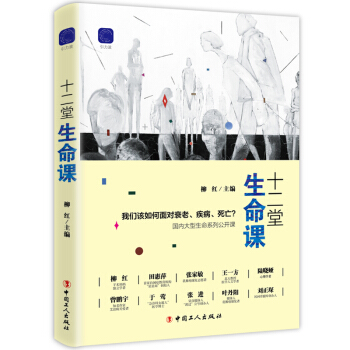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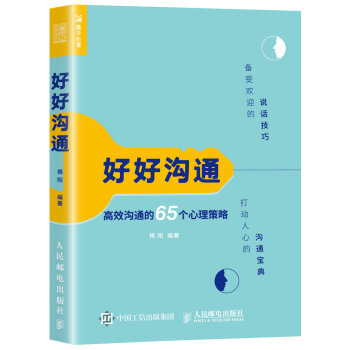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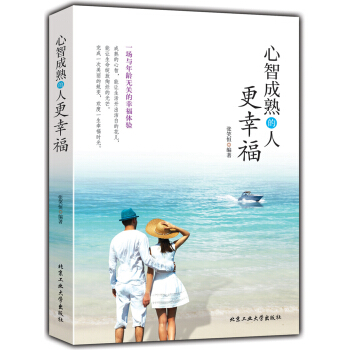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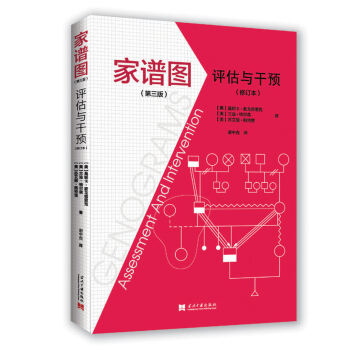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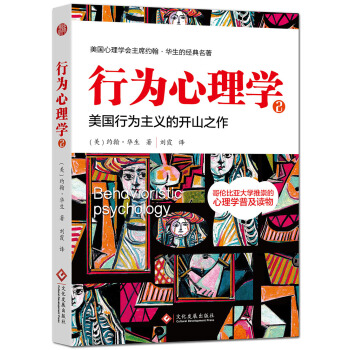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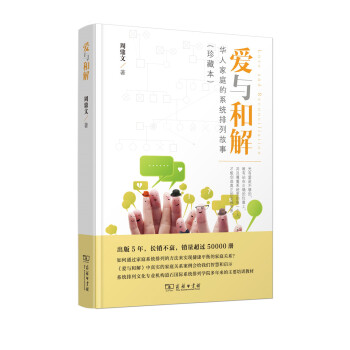

![中学生心理辅导 [Psychological Guidanc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51971/5a74348eNd75a2e0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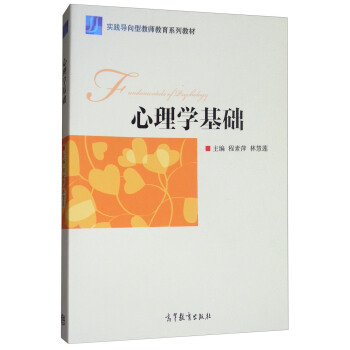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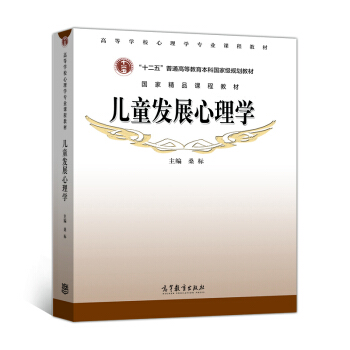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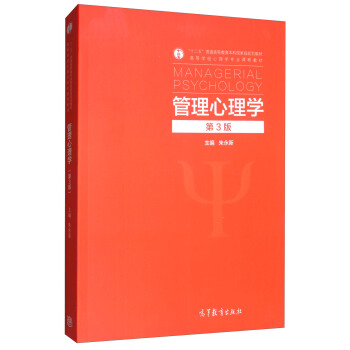

![爱的艺术 [The Art of Lov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52185/5a338dcbN8e65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