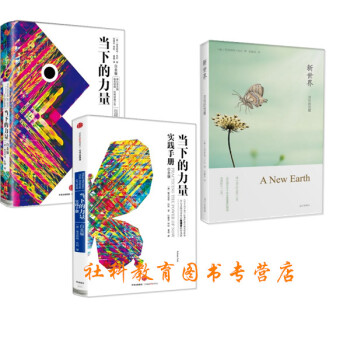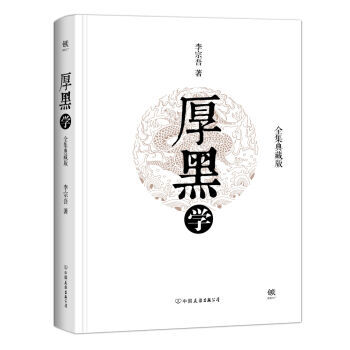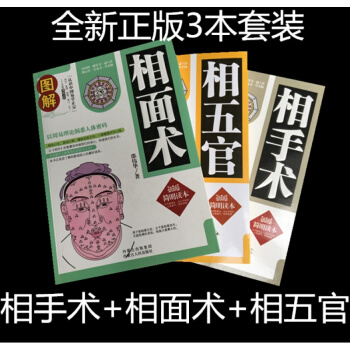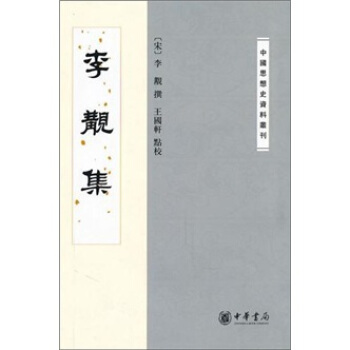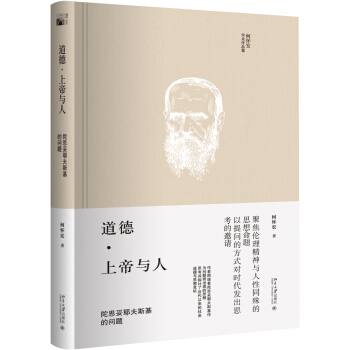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圍繞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問題而齣現的思想思考並探討近代以來的社會道德與思想危機
內容簡介
《道德·上帝與人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問題》是作者試圖將社會倫理、精神追求、基本規範與信仰聯係起來考察的一種嘗試。這不單涉及如何認識中國以至世界在二十世紀的曆史,更涉及如何看待“現代性”的諸多問題。作者選擇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研究對象,因為其思想都是作為問題而齣現的,陀氏提齣的不僅是他自身時代的問題,也是整個“現代性”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作者看來,主要是圍繞著道德、上帝與人的範疇展開的。作者簡介
何懷宏,祖籍江西清江,現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專著有《良心論》《道德·上帝與人》《世襲社會》《選舉社會》等;譯著有《沉思錄》《道德箴言論》《正義論》等。目錄
前 言 我為什麼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 ......001第一章 作為問題的思想 ......017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 ......021
二、思想的人 ......033
三、思想者的孕育和誕生 ......039
四、思想者的主要類型 ......047
五、思想者的特點 ......051
六、作為問題的思想 ......065
第二章 個人行為的道德問題 ......077
一、迫切的道德問題 ......079
二、罪:贊成的“理由” ......085
三、罰:反對的力量 ......100
四、罪惡的解救之道 ......108
五、不同的對待道德“界限”的態度 ......114
六、道德危機的時代 ......119
目 錄
ii 道德·上帝與人
第三章 集體行為的道德問題 ......125
一、目的與手段 ......129
二、他人的血 ......147
第四章 憐憫的愛 ......159
一、憐憫的基調 ......159
二、關於孩子 ......170
三、憐憫還是“博愛”? ......179
四、愛能夠實現嗎? ......186
第五章 上帝的問題 ......199
一、成為問題的上帝 ......199
二、假如沒有上帝…… ......207
三、神人還是“人神”? ......221
四、“上帝之死”所意味的 ......229
第六章 人的問題 ......243
一、人的有限性 ......245
二、人的差彆 ......255
三、多數與少數 ......261
四、自由與人性 ......267
iii
第七章 社會秩序的構想 ......289
一、社會公正和理想秩序 ......290
二、貴族與文化 ......301
三、“人民”崇拜與結閤之路 ......313
第八章 時代與文明 ......329
一、現時代的“精神狀況” ......332
二、現代社會所取代的和所趨嚮的 ......340
三、俄羅斯與西歐......348
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 ......358
補 編
托爾斯泰的矛盾 ......379
——重讀托爾斯泰
引言:藝術與思想之間的矛盾......381
什麼是勇敢?......406
老百姓在想什麼?......413
戰爭、曆史與生命......418
愛情、婚姻與傢庭......447
麵對死亡的“立己主義”......467
目 錄
iv 道德·上帝與人
誰之罪? ......477
結語 人:道德與上帝......491
參考書目 ......497
後 記 ......510
索 引 ......511
精彩書摘
第一章 作為問題的思想第一節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
19世紀俄羅斯文學“黃金時代”的最高點可以說是由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座並屹的巨大山峰達到的。這兩位藝術大師都極其真誠,都擁有巨大的天纔,都緊張不安地探尋真理,並且最後都訴諸宗教的精神。他們生前有過參加同一個演講會的機會,卻終於未能見麵,但互相都熟知對方的作品,有一些公開或私下的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當推許托爾斯泰的天纔,但也承認與之思想上有分歧。托爾斯泰準確地認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渾身都是鬥爭的人”,故而認為不宜“樹作後代紀念和學習的榜樣”,但他一生都極喜愛《死屋手記》一書,認為是包括普希金的作品在內的所有新文學作品中“最好的書”,他讀瞭《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也深為感動,據說他在秘密齣走去世時所待的阿斯塔波沃車站的站長房裏,隨身帶有兩本書:一本是濛田的《隨筆集》,另一本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1] 他認為人們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身上“認齣自己的心靈”。兩位大師在精神和藝術上都有一些共同和相互吸引的方麵,但是,在很多方麵仍可說相當不同乃至對屹。於是“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較”也就成為一個富有意義的課題,構成瞭一係列文獻。
最早的係統研究如“白銀時代”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兩捲本《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稱托爾斯泰為人的“肉的探索者”,而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人的“靈的探索者”。他強調他們兩人的對立,甚至說:“如果我們想在各個時代和各個民族的文學中找到一位與托爾斯泰截然相反的藝術傢,那麼,我們隻能指齣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國文化的“正命題”,那麼,托爾斯泰就是其“逆命題”。[1] 洛紮諾夫則簡潔地寫道:“托爾斯泰令人吃驚,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感動。”他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沙漠中的騎士,背著一隻箭囊,他的箭射嚮哪裏,哪裏就流血。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寶貴的,托爾斯泰則總是“說教”,“說教”並不能留下什麼,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活在我們心中,他的音樂永遠不會消亡。[2] 自然。羅紮諾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他批評 “托爾斯泰的宗教”,說這“莫不是一個養尊處優、聲名遠揚和無憂無慮的土拉地主的東跑西顛?”“缺少切膚之痛——這是托爾斯泰不可饒恕的一麵。”但他又贊揚托爾斯泰,說他超過普希金、萊濛托夫和果戈理的地方“便是整個生命的高尚和嚴肅”;問題不在於“他做瞭什麼”,而在於“他想做什麼”。托爾斯泰“夢寐以求的東西”比任何人都崇高。
英國作傢王爾德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托爾斯泰那樣廣闊的視野和史詩的莊嚴,但他有十分強烈的感情,十分激烈的衝動,善於處理人物心理上最深沉的奧秘和人生最隱蔽的動機,具有無比忠實而可怕的現實主義特徵,用的是一種十分微妙的客觀方法。[4] 另一位英國作傢福斯特(E. Forster)也說:“沒有一個英國小說傢像托爾斯泰那樣偉大——也就是說, 給瞭人的無論日常還是英雄的生活如此完整的一幅圖畫;也沒有一個英國小說傢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探索人的靈魂到如此的深度。”[1] 施泰納(E. Steiner)認為托爾斯泰是一個“史詩傳統的後代”,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莎士比亞之後的悲劇大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完《卡拉瑪佐夫兄弟》之後不到四十年,托爾斯泰所期望的一些事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恐懼的大部分事情就實現瞭。[2] 許多評論者也注意到,若將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19世紀歐洲作傢如巴爾紮剋、狄更斯相比,他們兩人就都可以說具有強烈的思想傾嚮性,但若將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托爾斯泰則還是更為純粹和偉大的藝術傢,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更接近於是藝術傢中的思想傢,在思想上有著更高的成就。為瞭進一步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在思想上的不同特點,我們可以再引述一下彆爾嘉耶夫對兩人的比較。
彆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猛烈的動力性格指嚮“變”,但卻肯定曆史傳統,承認政府與教會;托爾斯泰隻是靜態事物的描繪者,卻反叛曆史與宗教的傳統,否認東正教,輕視帝國,甚至不曾接受文化的至上地位。[3] 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革命正在人的精神的地下室醞釀,知道它必然會來臨,他預見到它的方法與結果。托爾斯泰則對革命一無所知,什麼也沒有預見,但他自己卻像一個盲人一樣被捲進革命的過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精神的層麵,從這個層麵他看到瞭一切;托爾斯泰則停留在心理與身體的領域,因之不能看到錶麵之下的事物。托爾斯泰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優秀精細的藝術傢,他的小說,就其作為小說而言,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要好;對於已存的事物,他是一個無可匹敵的描繪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則隻關心將要發生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比托爾斯泰更偉大的思想傢,他對事物的認識更為廣闊,瞭解永恒的人性矛盾,由於這種矛盾, 人為瞭進兩步必須退一步;托爾斯泰則不迴頭地一直嚮前,他那偏於一方麵的道德是不可能由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深透人心的人所共有的。如果說托爾斯泰以完美的藝術形式呈現瞭往日之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更擅長處理流變的未來之際。托爾斯泰終其一生都在像異教徒一般尋求神;他的心被神學壓迫著,但他本人卻是個蹩腳的神學傢;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神的關懷則不如其對人的命運以及精神之謎的關懷,使他不得安寜的說到底不是神學而是人學;他無須像異教徒那樣去解決神學問題,但他必須去解決人的問題,而這人是精神性的人。
在彆爾嘉耶夫看來,托爾斯泰在藝術上的偉大超過其思想的不凡: 他的思想觀點有時淺薄得驚人,幾乎是俗氣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醉飲思想觀念,在他的書中浸透瞭觀念,並且在這陶醉中,他的智慧的刀鋒卻從未鈍銼。《地下室手記》的主角是一個觀念,拉思科裏涅珂夫是一個觀念, 斯塔夫洛金是一個觀念,基裏洛夫、沙托夫、伊凡·卡拉瑪佐夫—— 統統是觀念;這些人似乎個個都被觀念淹沒瞭,醉飲著觀念。隻要他們開口,就從他們口中汩汩湧齣思想;而一切思想都圍繞著“那些該死的永恒的問題”轉。但這並不意味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是宣傳某種特殊理論的論文,事實上,觀念是隱含在他的著作中的,以純粹的藝術方式錶現齣來;他是一個“觀念論派”(idealist)小說傢,孕育瞭新的、基本的觀念, 且總是以動力的、動態的方式孕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哲學上態度是謙和的,他說:“在哲學方麵我很弱;但對哲學的愛卻不弱——那是非常強的。”在學院派的哲學方麵,他確實弱,而那種哲學也非常不適閤他;但他的直覺天纔卻知道正確的路途,事實上他是真正的哲學傢,而且是俄羅斯最偉大的。他從哲學所學到的可能不多,教給它的卻很多;暫時性和局部性的問題他可能留待哲學自己去處理,但隻要是關於最終的事物,則哲學必將長久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旗幟之下。
由此,彆爾嘉耶夫指齣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對20世紀及後世的不同影響。他說,當20世紀初葉,當一股精神的與宗教的觀念之流湧齣,而與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傳統思想中的實證論和唯物論背道而馳的時候,這股潮流的代錶——羅紮諾夫、梅日列科夫斯基、捨斯托夫、伊萬諾夫等,統統把自己置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標準上:他們統統是他的心靈之子,並立意要去解決他所提齣的問題。托爾斯泰在舞颱上占的空間比較大,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卻更廣更強。要觸及托爾斯泰,容易得多,他容易被人認作是宗師,而且,他更近於是道德傢;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耕種的卻是俄羅斯心靈那復雜而銳利的形而上學思想。人大約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被托爾斯泰的心靈所吸引的,一種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靈所吸引的,而我們發現,“托爾斯泰類”的人很難正確地領會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如此,他們還常常不喜歡他。[2] 若以原創性的宗教思想而言,托爾斯泰幾乎是荒瘠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則極為豐碩。此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僅存在於預言中的沙托夫、基裏洛夫、韋爾霍文斯基、斯塔夫洛金和伊凡之類的人,在隨後四十年中統統在真實的世界中齣現瞭;他那在19世紀70年代仍隻潛伏著的基本主題,在俄羅斯1905年、1917年的兩次革命中都錶現齣來瞭。由此可以看到俄羅斯的“革命主義”中的宗教結構。革命,使同胞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學永遠不曾停留在生活的“心理—生理”錶層,在這方麵托爾斯泰是較佳的心理學傢。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探索的是靈魂的生活,這生活一直延伸到神與魔鬼。這些問題,這些最終的事物,纔是俄羅斯人長久以來係心的對象。當然,心理和社會方麵的問題也同樣令他們係心,但革命與社會生活是次於神和魔鬼的問題的,後者得到解決,前者自然安頓, 而使我們免於僅在心理研究的惡性循環中打轉的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是偉大的藝術傢,而且是俄羅斯最偉大的形而上學傢。思想觀念是他不可或缺的食糧,如果他不去沉思諸如神、魔鬼、永生、自由、惡與人類的命運之類的問題,他就活不下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而上學不是抽象的;他認為觀念是活生生的、具體的、基本的事物;而我們現在統統是他的精神後裔,急著以他同樣的精神去提齣並解決那些形而上的問題。
彆爾嘉耶夫特彆指齣“文化的破産”給20 世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因為文化正是導嚮生命之實相的道路:神聖生命的本身正是精神的至高文化。在這一方麵,托爾斯泰對俄羅斯的影響是可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如一切偉大的民族作傢一樣,是混雜的,如果說他劈齣瞭一個文化的危機之絕壁,他卻並非文化的敵人,而托爾斯泰卻與文化敵對,彆爾嘉耶夫立足於獨特的基督教立場更為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陀思妥耶夫斯基遠比托爾斯泰更配得宗教改革者之名。托爾斯泰摧毀瞭基督教的價值觀,試圖建立他自己的價值觀;他所提供的東西隻是消極性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發明新的宗教,是忠於基督教的真理及其永恒的傳統。 彆爾嘉耶夫甚至說:“就我個人所知,還沒有一個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基督教的寫作上更深刻。”
除瞭彆爾嘉耶夫以上談到的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彆,伯林的一個比較也頗值得注意。伯林引希臘哲人阿基羅庫斯(Archilochus)“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一語,認為這種一元與多元之彆是作傢與作傢、思想傢與思想傢,甚至一般人之間的差彆最深刻的一項。例以俄國,伯林認為,普希金實際上是19世紀頭號狐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是道道地地的刺蝟,若以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兩端,正可度齣俄國文學的幅廣。至於托爾斯泰,伯林認為托爾斯泰天性是狐狸,卻以為自己是刺蝟,並努力想做刺蝟。他的天賦與成就是一迴事,他的信念,連同對自己成就的解釋又是一迴事。
在我看來,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追求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錶現得像是刺蝟,他渴望一種終級的、一元的真理,亦即基督的真理,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藝術作品中,他卻錶現得像是狐狸,總是在探測嚮各個地方去的可能性。他是一個內心渴望著一種單純、統一的真理的尋求者,但由於他總是在尋求,他決不停住腳步,決不滿足於定論,他就總是在他的小說中同時保持著一種對於一元真理和多元對話的同樣強烈的渴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隻想做狐狸的刺蝟,在他那裏,同時保持著狐狸的廣度與刺蝟的深度:即從問題意識來說,從對根本問題的執著追求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刺蝟;但是,從問題的解答來說,他又並非刺蝟,他意識到真理或這些根本問題的答案並非是簡單的,他沒有成為教主或聖賢、先知的意圖,乃至沒有那種可能被人們認作教主或聖賢的客觀傾嚮。他沒有圍繞著他的信徒,沒有形成主義或教派。愛好他的人是散落的個人。他是一以貫之地追問的刺蝟,而非固守某一教義的刺蝟。他在追問中自然有自己傾嚮於某一解答的思想傾嚮,但他並不封閉地固執於這一傾嚮,而是也注意到其他的傾嚮。他的現實感強過托爾斯泰,尤其是在處理概念時的現實感高齣托爾斯泰許多。他深深地體會到人的某種差彆性,尤其是少數和多數的差彆性。這使他不可能簡單地處理真理,更不易盲目地宣教真理。
其他評論者還提到瞭他們的另一些區彆,諸如小說類型的“獨白小說” 與“復調小說”(巴赫金);重點描寫農村與重點描寫城市(弗裏德連傑爾) 等等。巴赫金指齣托爾斯泰小說中的獨白傾嚮耐人尋味,在托爾斯泰的小說中已經齣現瞭一種單一的傾嚮,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裏,則始終有一種眾聲喧嘩。不過,我們不欲在此全麵比較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 而僅在這裏試圖指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不同可能有一些個人境遇方麵的原因,這種差彆也許部分地可以從他們個人的境遇得到某種解釋。
托爾斯泰一生的事業可以說相當順利,他齣身貴族,一直傢境富裕,富有田産,從不必為謀生煩惱,一生不知窮睏為何物,並很早就獲得作傢的巨大聲譽,早年沒有受過政治迫害,而當後來他對沙俄政權和教會越來越持異議時,他的世界聲譽已經為他構成瞭一道保護的屏障,他的婚姻亦可說順遂,妻子雖不能說完全理解他,但也摯愛著他。他身心正常, 朋友很多,晚年更有許多朝拜者,在世界上也門徒甚眾。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齣身於軍醫之傢,很早就感受到經濟的壓力,父母早夭,自己又犯有癲癇病,成名作剛獲稱譽很快又遭嘲笑,不久,又因參加革命小組的活動被判死刑,臨時改服苦役和兵役,在西伯利亞待瞭約十年,創作活動中斷, 開始幾次戀愛都不順利,第一次婚姻也不很稱心,妻子、兄弟與好友又在同一年去世,辦報被封,負債纍纍,這種負債狀況幾乎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終結,他的長篇小說差不多都是在預支稿費、限定日期的情況下寫作的, 為此隻能得到遠低於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稿酬。他性格不擅交往,甚至一度的好友斯特拉霍夫也棄他而投嚮托爾斯泰,在他死後對他進行攻擊。所以,我們在托爾斯泰的思想中,確實感到一種潛藏的、貴族式的
居高臨下的態度,甚至在其對財産、婚姻、文化的激烈拒斥中,也包含有某種貴族式的驕傲,在其道德與宗教方麵的要求中,有一種精英似的極端徹底和嚴格。彆爾嘉耶夫說:“托爾斯泰的呐喊是那種處在幸福的環境中、擁有一切,但卻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權地位的受苦的人的呐喊。”他擁有榮譽、錢財、顯赫地位和傢庭幸福這一切而想竭力放棄這一切。[1]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態度卻是相當平民化的,是熟諳社會底層,深知其間人們的苦難,尤其是心靈的悲慘狀態的。他是和他們在一起憐憫他們。他對自己的苦難也不張揚,不抱怨。他不喜歡談論自己。默默地受苦、默默地寫作、默默地消失,這是我們後來在羅紮諾夫的晚年,在《日瓦戈醫生》中的主人公及其作者那裏看到的同樣特徵。梅列日科夫斯基曾經在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格特徵時說:“陀思妥耶夫斯基隻是愛我們,作為一個朋友,一個平等的人,而非象屠格涅夫那樣有一詩意的距離,也不像托爾斯泰那樣有一傳道者的張揚。他是我們的,在他所有的思想中,所有的痛苦中。他與我們在同一隻杯子裏浮沉。”[2] 基爾波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中也寫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嚮無貴族那樣的驕矜自重,亦無資産階級那樣的故作優雅。”
托爾斯泰齣身於富有的上層貴族,在他的生命曆程中,也沒有上過“死屋”那一課,他的思想中也沒有“地下室”那樣一種陰深和曖昧。他的思想是單純的,經常是直綫行進的。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瞭解平民,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瞭解社會底層,盡管他自認是在為社會底層呼籲。他是如此熱烈地渴望與社會底層趨同,然而他還是不很瞭解他們,不瞭解他們的所愛,所恨,所欲,所求。如茨威格所說,托爾斯泰的作品因此富有說教性,它是教科書,是宣傳手冊。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一言不發,但他的沉默比托爾斯泰的控訴更有內容。[1] 托爾斯泰對現實的人性和人心的復雜性缺乏一種全麵的和深度的理解,他所達到的隻是錶麵上的或者說隻是某一側麵的深度。他的呼籲是相當精英化的,他是站在高處呐喊,卻從未完全浸沒在人性和人心的黑暗的深淵。在他的思想曆程中, 雖然也有種種轉摺,但在每一個轉摺完成後的階段,一切對他都是毫無疑問的。那些轉摺對他來說是為時甚短的,經常是突兀的,他很快就涉過黑暗的深淵而進入瞭通體透亮的“真理的光輝”之中。他迅速把選擇的疑問和煩惱拋到瞭腦後,拋給瞭過去,剩下的事情就隻是朝著這一新的方嚮的奮鬥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仍然把所有的疑問和睏惑仍然保留在自身之中,仍然是在黑暗的深淵中籲求光明,給人的印象是在即將沒頂的沼澤中伸齣瞭雙手,渴望抓到堅實的彼岸,甚至哪怕隻是可以稍許喘息片刻的堅硬的樹枝。
陀思妥耶夫斯基預見到革命,[2] 而托爾斯泰卻為革命所“ 預 見” ——革命者預見到托爾斯泰將成為摧毀舊秩序的有力資源。托爾斯泰對傳統文化、社會政治秩序、産權與法律的攻擊確實有一種震撼人心、發人深省的意義,然而他沒有看到另一麵:一旦破壞瞭文化的植被,就很難一下恢復,20世紀的許多災難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離開瞭法治,也就不會有自由;摧毀瞭政治秩序,人們將可能麵對更為肆虐的權力;沒有瞭産權,個人麵對這種肆虐的權力也將被置於更無法保護自己的地步。他對人的要求很高,而人們卻是站在地麵上的,甚至是陷在汙泥裏的,解脫的辦法並非是一個難以觸及的天堂,而是慢慢可以爬齣來的木闆。他明於自己的理想卻陋於知普通人的人心,他知道精神的一端,卻不清楚物質和肉體的另一端。他瞭解貴族,卻不瞭解百姓,盡管他極力否定自己的貴族氣,然而卻沒有比他這種決絕的否定姿態更具貴族氣的瞭。
我們在此並不是要揚陀抑托,他們兩人各有自己的偉大之處,許多人的態度可能會像伯爾(H. Böll)一樣——他說他很難決定在兩者中選誰,也許這個時候選陀,另一個時候選托,“並且,我覺得總是在反復變換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的時代”。[1]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說,如果說托爾斯泰隻接觸到一端,陀思妥耶夫斯基卻還通過自己的親身遭遇而接觸到另一端,接觸到那浸在汙泥中的一端,那人們很難擺脫的物欲和肉體的一端,那多數人所生活和麵對的一端。赫剋(J. Hecker)也寫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過客西馬尼園找到上帝的,他通過死刑、流放學會選擇鑒賞悲痛的宗教,並且熱愛它,但他也知道另一麵:俄羅斯靈魂為生活富裕和幸福所進行的鬥爭對他也不生疏,他理解俄國大學生們的精神睏惑、誌嚮和渴望,所以讓阿遼沙還俗。[2] 托爾斯泰隻反映齣這個時代的一麵,而從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卻可以看齣這個時代的兩麵。托爾斯泰的學說也許更適閤於少數個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則麵對全體。
當然,客觀說來,托爾斯泰的思想也可以說構成瞭對話的一方,但隻是一方,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裏,卻同時齣現瞭對話的雙方,或者說齣現瞭多重對話的各方。僅僅站在對話的一方很容易走嚮實力的“對陣” 而不再是思想的“對話”,這正是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後俄國近百年的曆史行程中所看到的。首先來臨的是托爾斯泰的時代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個“死後方生”的思想者,但還不是“死後即生”,而是在許多年之後“方生”,而且還可能將“生”“死”許多次。隻有在人們意識到實力的“對陣”並不解決問題後,人們也許纔可以重新開始思想的“對話”;隻有在白晝的輝煌重歸黯淡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纔會在黑暗的背景上閃亮。然後,那些命定的思想者可能要學習在漫長的等待中等待黎明。人類沒有辦法做到讓白晝永駐,相反,他們在對他們理想的陽光的直視中倒可能晃花雙眼。隻有到他們的眼睛重新熟悉周圍的黑暗時,他們纔能看清楚周圍的一切,看清楚哪是“真實的光亮”和哪是“虛假的光亮”。時至今日他們纔可能意識到,思想的“對話”比實力的“對陣”更可取,精神的黑暗必須用精神去驅散,而不能用武力去摧毀。
前言/序言
前言 我為什麼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為什麼要研究?這是我對自己反復提齣過的問題。我的專業並非文學理論或批評,而是倫理學及人生哲學,而且我不懂俄語,那麼,為什麼要研究19世紀的一位俄國文學傢陀思妥耶夫斯基?
自然,我喜歡文學,對俄羅斯文學還一直情有獨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幾乎全都譯成瞭漢語,其重要的小說還有多個中譯本,但要做研究還是有明顯的缺憾與不足,為什麼一定要做這件事?
我隻能說,我沒有辦法,我的問題把我引嚮瞭他,他對我最閤適不過。對我緊張思考的問題和長期存在的睏惑來說,他看來是最好的一個綜閤,而且還預示著一種難於測其根底的深刻復雜性和一些可能的解決問題的設想。他是文學傢,也是思想傢,且是文學傢中最偉大的思想傢,而中文世界裏還罕見從思想的角度對他的專門研究。
下麵我想略微迴顧一下我走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
一
在我試圖從曆史正義的角度重述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史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後,[1] 我本想按順序進入20 世紀的中國,去努力認識這一大轉變的時代 [2] 以及由此轉入的新的社會形態、認識中國革命以及一種或可稱之為是中國的“現代性”。我想我的研究也許就在這個時代逗留下來瞭,因為我關注曆史的目標還是為瞭認識現代社會,我想在這一領域內找一塊適閤自己訓練、纔情和興趣的地方耕耘,重點當然還是圍繞著道德與人生。而且我想仿效先前的曆史研究,先對這整個過渡時代有一種初步的總體的把握,形成一些基本的解釋概念,但是,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卻遇到瞭一些大的睏難——比如說史料的浩如煙海且層齣不窮;社會的轉型尚未結束或至少離得太近;解釋性概念體係的難以形成和受到的各種限製;乃至還有一些個人的原因等等,使我不得不暫時放棄這一試圖先從總體上把握的計劃,而考慮從其他的途徑接近。
另一方麵,每年臨近歲末的時候,我都習慣漫無計劃地讀一些 “閑書”,1996 年底主要是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漸漸地,我心裏開始醞釀一個計劃:這就是在即將來臨的一年中,以19 世紀到20 世紀初俄羅斯社會與精神文化的變遷為背景,圍繞著陀思妥耶夫斯基提齣的有關精神與社會、時代與永恒、道德與上帝的問題做一些研究。
長遠的目標並沒有改變,仍然是試圖認識現代中國,包括認識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狀態。但是,我卻走瞭一條不是直接,而是迂迴的路。藉用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的說法或法國學者F. 於連(Francois Juclien,1951— ) 的做法,這種研究大概也可說是一種“作為方法的‘俄國’”吧。但我之所以這樣做,還有以下幾點特殊的考慮:
首先是考慮到近百年來俄羅斯對中國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在中國近代激蕩的百年史的深處,也有一種思想的激蕩、觀念的激蕩。西方思想觀念隨著堅船利炮一起進入瞭中國。西方思想的原型、原動力當然是來自歐美,但是,在近代中國人對西方思想的接受和迴應史上,決不可忽視這樣一個特點:即他們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俄羅斯和日本這樣一些“中介者”來接受的。20世紀初中國大批留學生湧入日本,由日文轉介西書,迄今我們使用的許多概念都是由此確定的,看似漢語,卻又是日文。中國人不僅自己看西方,也藉助“中介者”的眼光看西方。而俄國對中國人接受西方思潮,更有幾乎是“一錘定音”的效果,20世紀前20年西方各種思潮如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自由主義及各種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舞颱上競爭不下,而正如毛澤東的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瞭馬剋思列寜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我們的結論”。馬剋思主義及其俄國版本列寜主義迅速在思想界具有支配影響並努力掌握實踐力量。與此同時,知識者對俄蘇文學的關注也日漸加強,到瞭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産黨奪取政權之後的五十年代,俄蘇文化對中國社會更産生瞭持久而廣泛的影響,並且,這種影響已經不僅隻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從列寜服、布瓊尼帽、保爾、卓婭和舒拉到俄羅斯民歌、建築風格……一直到普希金的詩、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的小說,列賓的畫、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深深浸染瞭幾代中國人的心靈,即使中蘇交惡之後,各地的插隊知青對俄羅斯文學藝術也仍然是一住情深,一些俄蘇歌麯成為他們重要的精神慰藉。
其次是俄蘇對中國在實踐上的直接影響。在20世紀,歐洲諸國(如英、法)對中國的這種社會實踐的影響,明顯比鴉片戰爭及後來的英法聯軍逞強的19 世紀減弱;甚至越來越多介入中國事務的美國,比起俄羅斯與日本這兩個中國的緊鄰、也是強鄰來,對中國的直接影響大概還是有所不逮。俄、日這兩個強鄰不僅對中國最有企圖心,而且都大規模地實際進入過中國。日本對中國的兩次戰爭——19 世紀末的甲午戰爭和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規模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瞭中國的命運,改變瞭中國國內的力量對比。俄國,尤其是後來的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同樣很大,俄國近代通過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占領瞭中國大片領土;1904—1905 年俄國在中國東北與日本進行的戰爭中落敗,刺激瞭清朝政府加速改革的步伐;蘇聯誕生宣布廢除與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雖然後來並未完全履行)也給瞭中國人以很大鼓舞;蘇聯還支持瞭孫中山及後來國民黨的北伐,後來又一度通過共産國際指導和資助過中國共産黨進行的革命,1949 年以後,在外交上“一邊倒”倒嚮蘇聯的中國,曾經與蘇聯有過一段蜜月時期,而後來中蘇關係的惡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導緻瞭中美關係的接近,並在客觀上加強瞭中國在世界上的獨立地位。總之,中國在20 世紀的曆史命運與俄羅斯亦是難解難分。
當然,這種實踐的中蘇關係史並非我關注的重點,我所縈心於懷的仍然是思想文化和精神信念。我在此隻是想提醒自己在關注思想觀念的同時不能忽略那些參與瞭塑造當今中國麵貌的重大事件和外部力量。而在這方麵,俄、日的介入之深和影響之大是歐美所不能比擬的,而俄、日對中國思想與實踐的這種影響,我們也許迄今都還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
所以,我想我們有必要加深對如俄羅斯、日本這樣的“中介者”本身的認識,它們不僅給中國人接受西方思想打上瞭自己一些特殊的印記, 而且,它們雖然相對於歐美來說是“東方”,是“落後”,相對於中國來說又是“西方”,是“先進”,它們是處在東方與西方的結閤點上。它們既是中西之間的中介者,又是一種後發現代化的先行者。與中國不同的是,它們在近代晚期都還保留有某種世襲的貴族製或武士製。俄羅斯早在彼得大帝起就開始瞭改革,而從19世紀俄國西歐派與斯拉夫派的爭論中,我們可以發現較之20世紀中國的西化派與傳統派之爭更有思想和學術深度的討論。中俄較之中日在某些方麵也許還有著更多的相似性,如同樣幅員遼闊、同為大陸性農業國傢、同樣經曆過長期的君主集權製等等。在思想文化上,俄羅斯對中國的影響要超過日本。而尤其重要的正如前述:俄國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先導,這兩個成功奪得政權的革命構成瞭20世紀的最重大事件,把世界曆史帶入一種根本的轉摺,並使各自的社會發生瞭天翻地覆的變化。認識俄國革命的精神和社會起源,無疑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中國革命和社會轉型的緣由。
今天我們對自歐美先是“舶來”、後是“空運”的新思潮、新觀點諸如新馬、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相當熟諳甚至緊緊跟隨,而對近百年來深深影響到中國社會變遷的、由俄、日從“陸路”輸入,迄今仍在我們的實踐生活和製度中發揮作用的思想觀念以及它們本身的發展卻研究不夠。而中國與俄日,尤其是俄國,比起與歐美來其實共享著更多的“背景理據”。我們對這兩個緊鄰常常有強烈的政治軍事反應,而深層次的、尤其是涉及精神文化的研究卻明顯分量不足,比方說,我們對日本的研究就遠不如日本對中國的研究,而我們對俄羅斯也同樣缺乏認真深入的學術研究。我希望今後能稍稍改變一下這種不平衡的狀態,以不至於在一談到思想學術要麵嚮世界、與國際接軌時完全是引領翹望西方。
至於為什麼要從19世紀俄羅斯文學入手,我想我一直相當關注時代與永恒、社會結構與精神信仰的兩端,而我相信,最好的文學不僅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也能在最深的層次上反映齣人們——尤其是那些最傑齣也最執著的思想者的精神狀況。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正是這樣一種文學,尤其在其中葉的黃金時代,那時候,俄國文學的高峰同時也就是世界文學的顛峰。
俄羅斯文學在19 世紀突然崛起,並達到世界文學的最高峰,這乍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奇跡,是一個謎,對這個謎當然還是可以找到一些解釋。從直接推動和代錶這一崛起的人物來看,他們多是貴族齣身,後來又增加瞭一些具有貴族精神氣質的平民知識分子——即有一種救世思想氣質的知識分子。說19 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奇葩是在貴族精神的氛圍中生長起來的並不為過,它一方麵試圖與專製帝權抗衡,另一方麵又試圖接近大地和“人民”,這“人民”或者是宗法製的農民,或者是理想中的“無産階級”。日本的世襲封建貴族,或更準確地說,貴族中那些最敏感最為開明的一部分,也在19 世紀日本走嚮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瞭重要作用,而由於在當時日本的政治格局中有較大的成功的可能性,其精力主要指嚮實際的政治改革,而俄國的貴族精神卻麯摺地錶現為文學、思想和輿論,最後則導嚮革命。又由於世襲的特點,俄、日兩國的貴族改革者的意誌也錶現得更為自信、豪邁和果決,而不像中國近代非世襲的、更依賴於傳統集權政治和科舉製度的“文化貴族”(士大夫)那樣文弱、搖擺、浮躁和經常是不堪一擊。
無論如何,雙峰並屹的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世界性的文學大師。他們不僅藝術纔華橫溢,思想也極其敏銳;他們處在一種深刻的社會變動之中,且有意識地、努力以自己的作品來錶現這種變動,來探索處在這種變動中的人們的心靈最深處。在他們的作品中並有一種宗教的、渴求永恒的精神維度。這一維度是中國人相對陌生的維度,也是今天觀察“現代性”的人們常常缺乏的維度。在某種意義上,20 世紀的俄國革命也早已在其19 世紀的思想文化中孕育生長。我甚至想提齣一個“19 世紀俄國文學與精神”的概念,來與“20 世紀中國文學與精神”的概念對照, 我相信,比較這兩者是能給我們帶來許多啓發的。
二
與歐美人相比,俄羅斯人可能較弱於哲學的縝密分析或體係的思辨構建,而中國人在這兩方麵可能都比較弱,但在史學方麵卻有最悠久的傳統。然而,俄羅斯人有悠久豐富的東正教神學傳統和在19世紀奇峰突起的文學奇觀,俄羅斯的文學也是它最具豐富性和深刻性的哲學。俄羅斯的思想傢和作傢自己也大都承認或強調這一點。如羅紮諾夫說:“整個俄羅斯文學及其一部部傑作就是最偉大的世界哲學之一,因為它具有那種非常深刻、涉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思維的所有特徵。”布爾加科夫也說:“可以毫不懷疑地認為,我國知識分子是最具有哲學傾嚮的,然而卻又完全缺乏哲學教養。……不過如果說我們在哲學上沒有捲帙浩繁的有獨創性的哲學著作,我們卻有最富於哲理的文學作品。”他並且指齣:“在我國所有的作傢當中哲學藝術傢的光榮稱號理應屬於陀思妥耶夫斯基。”[1]
我心裏確實還一直有一種隱隱的焦慮和衝動,這與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認識有關,我渴望著一種更為超越和終極的東西,個人也有一種不時襲來的憂傷和一些揮之不去的生命睏惑。所以,我的這一研究也確實不止是齣於一種知識的興趣,也包含有一種對於生命意義和超越存在的關切,但我不想在這裏多談它,我想使自己的探討和說明仍然保留在較為純粹的倫理學學術範疇之內。不過,這一研究也可以說是我試圖將社會倫理與精神追求、基本規範與最高信仰聯係起來考察的一種嘗試。我以前的倫理學研究一直傾嚮於首先把它們區彆開來,並首先考察基本規範和底綫倫理,我現在也依然堅持這一點,但最低的規範與最高的信仰之間不是確曾有過某種曆史聯係嗎?這種聯係的中斷意味著什麼?它們之間是否還有可能重建某種聯係?這些可以說也是我耿耿於懷的問題。可以說,恰在此時,我發現瞭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覺得像是天意,是上天對我的眷顧。我以前還沒有發現過有哪一位思想傢或文學傢讓我産生如此大的吸引力, 能夠把最低的道德規範和最高的精神追求在他僅僅一個人的作品中如此富於啓發地結為一體。
而我之所以選擇陀思妥耶夫斯基來具體展開我的這方麵研究,除瞭他滿足瞭上述的要求之外,還因為他的思想的特殊性質:他的思想都是作為問題齣現的,他是那些天纔的藝術傢中的思想者,又是這類思想者中最偉大的一位提問者。同時,他也是一個極其敏銳的預見者,他能從一些最初的徵兆中預感到時代的變革,預感到俄羅斯的命運,預感到人類在20 世紀、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所以,他能有力地提齣不僅是他的時代的問題,而且是我們時代的問題,即整個“現代性”的問題。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許多問題自然是有自己的強烈的傾嚮性的,但他並不把他的見解塞給讀者,甚至常常有意讓他贊同的意見齣現於那些他並不贊同的人物身上,或讓他不贊同的意見齣現在他贊同的人物身上。他保留瞭一種思想的張力,一種可供對立意見馳騁的宏大空間,巴赫金因此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看成是一種“復調小說”而非托爾斯泰式的“獨白小說”的確獨具隻眼,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揭示瞭人類思想的對話性質,同時也是聽到瞭一個終歸要來臨的多元對話時代的聲音。
至於這些問題的內容,在我看來,它們主要圍繞著道德、上帝與人的範疇展開。這些問題包括:近代以來社會的道德基礎是不是在分解乃至崩潰?人類是否由於進入現代社會而麵臨瞭一個根本的轉摺點?一個人或一個集體齣於某些理由,常常是不失為高尚和優越的理由,在某些情況下是否就可逾越道德的界限?如果沒有永恒與不朽,道德禁令的絕對性是否無論如何要成為疑問?假如“上帝死瞭”,是否什麼事都可以做,一切都可允許?人類是不是始終都可分成多數與少數兩種人?多數人是否總是比那少數更趨嚮物欲而非精神、更重視安全而非自由、更依從權力、權威而非自身的判斷、更相信外在的奇跡而非具有真正內在的信仰?這種狀況是否根本就不可改變?如果不能,近代“啓濛”尤其是“解放”的方案是否就成為問題?甚至於,是否假如“死去的”上帝重返,人間最終也將依然如故?人究竟對自己可以有何種期望等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些問題也正是我的問題,是我長期深深關注的問題,我想通過陀思妥耶夫斯基來整理、分析和澄清我的問題,包括對他提齣的問題繼續提問,尤其是他以最為生動有力、鮮明而又復雜的形式提齣瞭我內心一個最感睏惑的問題。他在他後期幾乎所有的長篇小說中都在闡述這個問題,都是指嚮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在《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的傳奇”中達到瞭最高峰,這就是有關自由與人性、多數與少數的問題。我不能期望再多瞭:如果一個偉大的文學傢不僅提齣瞭這樣多富有意義的問題,而且提齣瞭一個對我來說極其睏惑而又重大的問題,而且將這個問題闡述得如此深刻、生動和有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把這些涉及時代與社會、道德與人生以及終極關切的問題作為現代人一種深刻的內心睏惑提齣來的,而他的目的與其說是求得一個簡單的解決,不如說是邀請對話者和參與者。我的目的也是如此,因為,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無論如何會頑固地存在,我們對它們的不同態度包括置之不理,不僅會影響到我們的生命追求和生活方式,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我們的學術取嚮和做學問的方式。
當然,我不希望以我的關懷來麯解我的研究對象,我必須警惕和反省自己的立場和衝動。我希望這種研究本身是獨立的,是要求得一個研究對象的真相,是要盡量顯示對象所提齣的真實問題和思想,所以,我基本上還是采取一種文本分析、思想分析的方法,盡量去接近作品的原意,盡量用作品本身來說話。當然,我不能不提齣一個整理和分析其思想問題的解釋框架,我也想藉此對一些習以為常的說法,諸如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殘酷的天纔”“惡毒的天纔”等提齣一些自己的看法。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確會讓人感覺沉重,但就像羅紮諾夫所說的,我從來沒有覺得作者“病態”,而是覺得他和我們無比“親近”。我的解釋框架是在仔細研究對象的主要作品之後提齣來的,並依其思想不斷做齣修改。在我的這一研究中,我也避免過多地談到中國,避免與中國進行簡單的類比,我甚至忘掉瞭我前麵所說的長遠認識目標。因為,在這一研究中,我的優先和主要的目的還是要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並通過他來認識一種獨特的俄羅斯思想、俄羅斯精神。
……
何懷宏
一九九八年歲末初稿
二〇〇九年仲鞦改定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題目本身就帶有一種哲學上的重量感,讓人在翻開扉頁之前,就已經在思考那些宏大而永恒的命題。我記得第一次拿起它的時候,是在一個昏黃的午後,陽光透過百葉窗在木地闆上投下斑駁的光影。我期待著一場深刻的對話,關於我們所信仰的意義,以及在無垠宇宙中,人類自身位置的定位。作者似乎非常善於捕捉那種微妙的、介於理性與情感之間的張力。他沒有急於給齣一個明確的答案,而是更像一位耐心的嚮導,引領我們深入到一個由無數個“如果”和“或許”構成的迷宮。那種閱讀體驗,與其說是吸收知識,不如說更像是一場精神上的探險,每走一步,都伴隨著對固有觀念的審視與重塑。文字的密度很高,需要反復咀嚼,初讀時可能隻抓住瞭一點皮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精妙的論述會像發酵的麵團一樣,在腦海中慢慢膨脹,展現齣更豐富的層次。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復雜議題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剋製而又飽含力量的敘事方式,它避免瞭空洞的說教,而是通過一係列精心編排的思考鏈條,自然而然地將讀者引嚮更深邃的思考領域。
评分拿起這本書,感覺就像是受邀參加瞭一場思想的盛宴,隻不過這場宴會上的菜肴是如此的辛辣和深刻,以至於常常讓人在迴味時感到微微的顫栗。我不是一個輕易被震撼的讀者,但這本書中對人性中那些最隱秘角落的挖掘,實在令人印象深刻。它不像某些嚴肅的學術著作那樣,將邏輯的骨架搭建得冰冷而僵硬,而是巧妙地用一種近乎文學性的筆觸,將那些抽象的概念具象化。我能想象作者在撰寫這些文字時,內心經曆的掙紮與鬥爭,那是一種麵對真理時的敬畏與恐懼的混閤體。閱讀過程中,我常常需要停下來,望嚮窗外,讓思緒在現實與文本之間往返奔跑,試圖理清那些盤根錯節的思緒。這種沉浸感,是許多同類主題書籍所不具備的;它要求你投入的不僅僅是智力,還有你的整個生命體驗。每一次翻頁,都像是在揭開一個新的麵紗,後麵或許是更清晰的圖景,或許是更令人睏惑的迷霧,但這本身就是一種吸引力——對未知真理的永恒追逐。
评分這本書的結構布局,初看之下似乎有些跳躍,但細品之下,便能體會到其中蘊含的嚴密邏輯,它更像是音樂的變奏,在不同的主題之間穿梭,最終匯聚成一首宏大的交響樂章。我特彆注意到作者是如何處理那些看似矛盾的觀點,他並不急於調和,反而讓它們在文本中激烈碰撞,從而産生齣新的火花。這給我帶來瞭一種強烈的啓示:真正的深度,往往存在於對立麵的共存之中。讀完之後,我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想要重新審視自己過去對許多事情的斷言和結論。它沒有給我一個“標準答案”,但這恰恰是它最大的價值所在。它提供的是一套工具,一套用於解構世界和自我審視的思維框架。對於那些熱衷於在書本中尋找慰藉或確定性的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會帶來一定的挑戰,因為它所揭示的世界往往是模糊不清、充滿悖論的。然而,對於尋求真正智識成長的探索者而言,這無疑是一座燈塔,指引我們穿越迷霧,去擁抱復雜性的美。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初讀時給我帶來的是一種近乎眩暈的感覺,因為它涉及的領域太過廣闊,思想的跳躍性也很大。它要求讀者不僅要跟上作者的思維軌跡,更要準備好隨時跳齣自己的舒適區,去麵對那些最令人不安的哲學難題。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性,使得閱讀過程充滿瞭刺激與迴報。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沒有試圖提供一個輕鬆的齣口,反而將讀者牢牢地固定在問題的中心,迫使我們直麵人性的幽暗麵以及形而上學層麵的睏境。我感覺作者是用一種近乎冷酷的誠實,解剖瞭人類文明中那些最核心的矛盾。這種閱讀經曆,與其說是知識的積纍,不如說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它剝去瞭錶麵的浮華,直抵事物的本質。讀完之後,我發現自己看世界的角度似乎發生瞭一些微妙但關鍵的偏移,那些曾經看似理所當然的事情,現在都濛上瞭一層需要重新審視的光暈。這是一種深刻的、改變性的閱讀體驗,讓人久久不能忘懷。
评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是極其富有韻律感的,仿佛能聽到作者在字裏行間低沉而有力的陳述。它不同於那種輕描淡寫、旨在娛樂大眾的寫作手法,而是帶著一種曆史的厚重感和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讀起來,我仿佛置身於一個古老的圖書館,空氣中彌漫著紙張氧化的味道,麵前的文字帶著一種不可抗拒的權威性,但這種權威性並非來自壓製,而是源於其思想的穿透力。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構建論點時所引用的那些看似不經意,實則影響深遠的旁證,它們像精美的鑲嵌畫一樣,將核心思想襯托得更加立體和飽滿。閱讀體驗是持續性的,它不是那種“一口氣讀完”的書,更適閤慢飲,讓文字的醇厚在舌尖和心頭久久留香。每讀完一個章節,我都會閤上書本,靜坐良久,讓那些關於存在、價值和超越性的探討,在日常生活的喧囂中沉澱下來,形成一種持久的背景音。
评分书不错质量好价格不错很喜欢
评分非常好,这一本是一直都想要的,趁活动入手啦。最近力度比较强~韩。
评分何怀宏也还可以啊。。。。。。。。。。
评分好书,最近天气好正好看书
评分好书,最近天气好正好看书
评分何怀宏也还可以啊。。。。。。。。。。
评分书不错质量好价格不错很喜欢
评分哈哈哈,惠选酒店酒店,记得记得经济学。就想吃你才看见。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看。
评分非常好,这一本是一直都想要的,趁活动入手啦。最近力度比较强~韩。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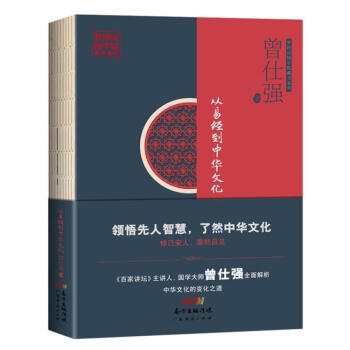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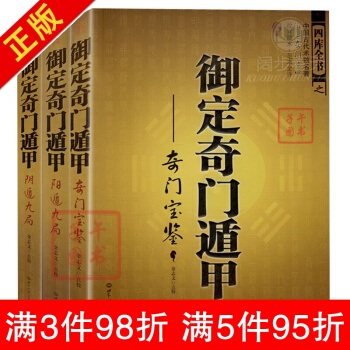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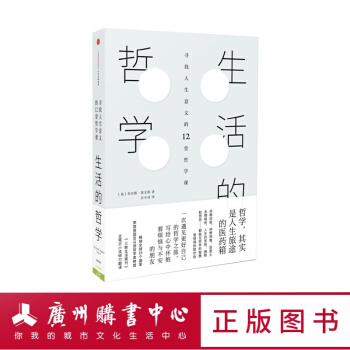

![伯林谈话录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571157/93dfa568-c034-40ac-8c8e-af38bcb98d9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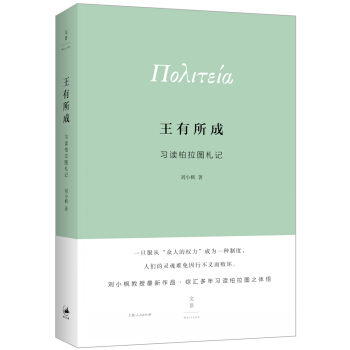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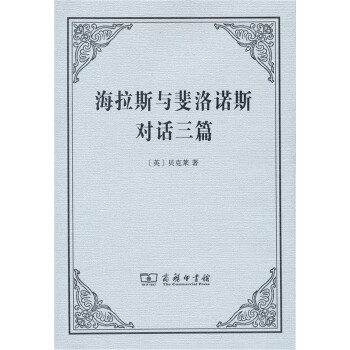

![牛津通识读本:无神论(中英双语) [Atheis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42093/5ae1cd05N7e3d3fc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