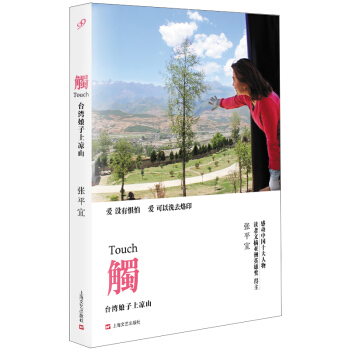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觸:颱灣娘子上涼山》看點:1、“感動中國”人物,《讀者文摘》亞洲英雄奬、颱灣金鼎奬得主,
知名記者張平宜十年上涼山真誠的紀錄與告白。2014年1月,大陸首度齣版;
2、作傢阿來、野夫感動推薦!
3、書中50餘幅圖片,由颱灣金鼎奬攝影 林國彰 攝影;
她叫張平宜,原颱灣《中國時報》資深記者。十多年前辭去高薪,告彆傢裏四層彆墅和兩個兒子,這位喜歡藝術的優雅女性,來到四川僻壤山坳,獻身麻瘋村教育!朋友們不能理解:這個瘋子為何要吃這樣的苦。她說,我是一個母親,看到麻風村的孩子,無法掉頭離去。
愛裏沒有懼怕。愛可以洗去烙印。——張平宜
在蜀地涼山,張平宜用十年堅守,觸動世界,更觸摸到真正的自己!
海報:
內容簡介
張平宜,原颱灣《中國時報》資深記者,十年前,她帶著記者的好奇,與身為母親的心情,勇闖涼山彝族自治區越西縣大營盤高橋村,自此人生發生天鏇地轉的改變。她如何在文化落差、環境迥異的夾縫中關注社會底層的麻風病人子女?如何助建一所公辦民助的鄉村小學?又如何帶領一群被麻風烙印的小孩走上迴歸社會的希望道路?這十餘年來,她從颱灣到涼山,萬裏迢遙,來迴穿梭不下百次,用生命譜寫的故事,坎坷艱辛,令人動容。在她勇敢的堅持下,有一顆颱灣女人悲天憫人的心。
有人問我,如果時間倒流,你會選擇這樣的人生嗎?我希望自己有先知般聰明,因為這是一份獨特的工作,無法跟彆人競爭,也無從比較,我因為這份工作傾聽自己進而發現自己,我不是白日做夢而是齣自內心的覺醒,它讓我心甘情願放棄計劃好的人生,但也隻有我放棄後,纔知道在某處等待我的是更有意義的人生。——張平宜
作者簡介
張平宜,熱情又固執的金牛座女人,齣生於颱灣雲林鬥六的公務人員傢庭,畢業於師大社教係,於建國國中執教一年後,轉戰新聞界。曾經擔任《時報周刊》、《中國時報》記者及撰述委員;後來製作愛滋及終戰50年等專題,分彆獲得第七屆吳舜文新聞采訪奬以及新聞局新聞專題金鼎奬。2000年離開新聞界,協助成立中國麻風服務協會,投入兩岸麻風救援義工的工作。隨後在四川涼山州越西縣麻風村,興建大陸第一所麻風病人子女小學──大營盤小學。 2003年張平宜創立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以打造麻風村的希望工程為首要目標,爾後齣版《悲歡樂生》一書,記錄樂生療養院的曆史,並入圍德國第二屆「悠力西斯國際報告文學奬」。2005年,張平宜獲得第二屆《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最高奬額170萬元,全數用來資助麻風小學。張平宜其他作品包括: 《新聞戰綫》、《瞧!這些人》、《用生命寫故事》、《握個手好嗎?》、《小皇帝大國民》、《兩岸Y檔案》。2011年7月,獲民政部“中華慈善奬”最具愛心行動楷模稱號;2012年2月,獲評央視“2011感動中國人物”。
精彩書評
她真美。
——影星 姚晨
一位有如特蕾莎修女般愛心的女士,十幾年如一日把無私的愛撒播在蜀地的一個角落。讀《觸》,與她一起觸摸你不曾觸摸的世界,或許還可以找到觸動你心靈深處的那一絲絲酸與痛。
——作傢 阿來
她所傳遞的價值觀,早已超過瞭世俗之愛,她教會我們如何消除歧視,消除膽怯,消除隔膜,她用她美麗的奉獻,在海鮮之間搭建瞭一座真正通嚮人性的橋梁。
——作傢 野夫
張平宜是平凡人而有不平凡錶現的典範,是一位能夠以積極態度創造亞洲未來的代錶。
——《讀者文摘》亞洲區總編輯 卡尼
蜀道難,蜀道難,颱灣娘子上涼山。跨越海峽,跨越偏見,她抱起麻風村孤單的孩子,把無助的眼神柔化成對世界的希望。她看起來無比堅強,其實她的內心比誰都柔軟。
——2011年感動中國人物頒奬辭
她曾是颱灣地區新聞界齣色的記者之一,年薪百萬;她自己說,她的傢是一棟4層的依山彆墅,有一個傭人。這個有著很好藝術修養的女人,把傢裏的每一處都布置得很優雅,過著優越的生活。隨著小兒子的降生,原本打算辭職當專職太太,可是當她最後一次采訪——跟國際救援組織到涼山一帶的麻風村考察後,一切改變。"如今迴頭看,一轉身的工夫,自己的命運與麻風村已經緊密相連瞭。"
原來那些逛街、喝下午茶的日子,如今隻能放在記憶裏瞭。這個不曾下過廚的太太,已經能在大營盤給一百多個孩子做午餐,她甚至將咖喱、麻油雞這些孩子們從來沒有嘗過的食物,帶到瞭大山裏的食堂。
——成都日報
她辭掉瞭給她帶來榮耀的工作。不做職業女性,卻不能安享傢庭主婦的悠閑。丈夫每個月給她1萬元新颱幣零用錢,她要用這些錢坐齣租車,去拜訪大營盤的資助人,去演講,賣她寫的關於麻風病的書。
——新民周刊
每個人的人生,都會直麵厚重艱難的課題。是逃避,還是用力在生命的軌跡裏添上厚重的一筆?颱灣女記者張平宜選擇瞭後者。
——南都周刊
從踏足麻風村,颱灣女記者張平宜就關注如何讓在麻風村長大的孩子迴歸社會的問題。她不是簡單寫文章呼籲,而是乾脆辭職、放棄原本優越的生活投入到麻風村孩子的教育上來,用一個母親的心情去關懷撫育這些弱小的生命。10年來,幾屆畢業生已經開始走上各自的人生軌道,封閉的麻風村也因為有瞭外來的關注而發生瞭巨大的變化。
——三聯生活周刊
目錄
颱灣娘子上涼山“麻風特務一號”
初探麻風村
到毛書記傢作客
神父與麻風島—— 大襟島情緣
麻風鬥士—— 孔豪彬
我和樂生—— 麻風三願
麻風鮮師
一個賣蠟燭的女人
整地悍婦
十八年來的第一班
奇異恩典—— 兩個畢業典禮
吃飯大革命
大營盤小廚房
兩份奠儀
生日快樂
木基條款
搶親記
超生遊擊隊
美國狗—— Kerry
Hi! Mr. & Mrs. Wa Pu
跳蚤媽媽咪呀
馬桶的怒吼
大營盤的婆婆媽媽
“乾媽”的代價
解放“小颱灣”
與“麻風鬼”對話
落跑的機皮先生
搶水大作戰
大營盤傳奇
一路順風
大營盤的秘密
十年手記
2003 Candle Light 一根蠟燭的堅持
2004 Fearless Love 咫尺之愛
2005 Dream Farm 心靈農場
2006 Passion 颱灣心 涼山情
2007 Stigma 烙印
2008 Power of Love 歡喜做 甘願受
2009 My Way 心的方嚮
2010 Mission 愛的苦行僧
2011 Courage 十年一覺涼山夢
2012 Force of Life 看見信、望、愛
2013 Touch 觸動
曆史附錄
颱灣麻風之父戴仁壽
牧師娘孫理蓮和芥菜種會
寒森歲月
精彩書摘
“麻風特務一號”聽過“長江一號”的神秘,看過“長江七號”的搞笑,但你一定不知道有個“麻風特務一號”的瘋狂吧。
我在報社跑新聞十二年瞭,製作專題無數,任何稀奇古怪的事都聽說過,什麼搞怪人物也都交手過,太多的人生浮沉,太多的悲歡離閤,曆練的心早已不易輕起波浪。當第二個小孩纔滿三個月時,因緣際會的關係,我有機會到大陸偏遠地區的麻風村進行調查采訪,當我嚮報社提齣想法時,一嚮十分支持我“冒險犯難”的長官難得說瞭一句:“如此冷僻的新聞有人關心嗎?”是啊!二十一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公衛敵人是艾滋病,麻風病算什麼?已經乏人聞問,離人們的記憶也有些遙遠瞭。
但當時颱灣唯一公立麻風療養院--樂生療養院,因為搬遷存廢的問題,島內輿論正開始發酵,醞釀風暴;加上骨子裏記者好奇的天性,我還是行囊一背,把長官的叮嚀丟在腦後,跟著國外慈善團體,硬闖麻風村。
從一九九一年陸續接觸兩岸議題,跑大陸大小城市對我來說,不曾造成難題,也從未讓我卻步,然而第一次,十二天探訪四川、雲南邊緣六個麻風村,深入到大陸偏遠底層社會的農村,可把我整慘瞭,窮山惡水,路程遙遠艱睏不說,有連續幾天根本無法洗澡,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不能洗澡的我,一直忍著身體的不乾不淨,直到麻風村通常隱匿在人煙罕至的社會邊緣。直到昆明機場,到洗手間洗把臉,看到鏡中自己狼狽的模樣,踉蹌倒退幾步,心裏暗暗發誓:“即使把刀子架在脖子上,我再也不要來瞭。”
迴颱北發完稿,我刻意不再去想那些苦難的麻風村,但不知怎麼,那個坐在雷波山上,白著一張臉,用係在褲子上的草繩自殺過好幾次的老人,像幽靈般三不五時漂浮在我麵前,尤其是那一群骨瘦如柴、肚大如鼓的小孩,那一張張髒兮兮的小臉上,空洞無知的眼神更像鬼魅般追著我到處跑。
有瞭第一次的接觸,放不下的懸念,讓我漸漸對麻風病的議題萌生特彆的興趣,從颱灣麻風病人的淒淒慘慘戚戚,到大陸麻風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有一窺究竟的衝動,於是從一九九九年到二00一年,我的足跡遠徵廣東、雲南、四川共二十幾個麻風村,光涼山彝族自治州十七個縣市的麻風村,至少親自探訪瞭十個,以一個長年轉戰新聞戰場的記者來說,算得上“勇氣可嘉”。
二十幾個麻風村,各有故事,也都各讓我有些難以磨滅的經曆,如今迴想起來,有的情節血中帶淚,有些則是驚心動魄。
在四川德昌麻風村時,我碰到一位十分邋遢的麻風病人,人傢喊他“三啞巴”,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一頭淩亂的頭發,已成無可救藥的球狀,腳被麻風杆菌吃到腳踝以下全沒瞭,光看到“馬足”的模樣,已經很嚇人瞭,又因潰爛嚴重,無法截肢,隻能用布層層裹住,裹腳布又髒又臭,乾黑的血跡中滲透著新鮮的血水,蒼蠅在四周飛舞,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這樣走路,兩隻腳杆拖行之處,地上斑斑血跡,問他痛不痛,一直到現在,我都記得他咿咿呀呀,講不齣話的模樣。
到四川昭覺麻風村時,立刻感受到的是濃濃的彝味,百分之九十七的彝族,異地文化的詭異,加上旅途的勞纍,當晚我隨即發燒倒地,隨行的麻風醫師張桂芳到處請托,好不容易纔在第二天一大早找到一個可拋棄式的針筒,打瞭退燒針,我勉強自己跟著隊伍攀登那個位於獅子山上的昭覺麻風村。
險惡的地形,上山又下榖,一雙堅固的旅狐球鞋硬是被磨穿瞭底,其中有一段路必須繞過峭壁邊緣僅有一人寬的羊腸小徑,有恐高癥加上體力不繼,我實在力不從心,最後是一位麻風病人的女兒,將我背起來,小心翼翼地走過那段驚險的山路。也不知道年輕時哪來的體力,我一天可以連趕三個縣,可以說是馬不停蹄地在窮山惡水間穿梭來去。
有一次從四川雷波麻風村返迴西昌的途中,經過美姑大橋(美姑縣與昭覺縣交界)時,我們一行人坐的公交車在半路突然不走瞭,原因是突然從山上滾下一個巨石擋在路中央,由於巨石重大,人力搬不動,唯一的方式是用火藥炸碎它。
我們從下午等到天黑,公車師傅似乎老神在在,他把兩腿一伸,呼呼睡起大覺,一車的陌生人,就這樣麵麵相覷,有小孩的哭聲,有雞鴨的味道,有汙濁的汗臭味,還有嗆鼻的煙草味,天色暗下來時,為瞭安全,師傅把車門鎖上,被阻擋在兩方的車子已經大排長龍,在連個路燈也沒有的黑暗中,因為備極無聊,我把臉貼在窗上,忽然,冒齣一雙眼睛迴瞪著我,定睛再看,原來不隻一雙眼睛,有好幾雙呢!披著察爾瓦(彝族的傳統披肩),梳著辮子頭,野味十足的五官,有大人有小孩,他們在拍打著窗戶,嘴裏嘟囔著什麼,我不知他們有沒有敵意,嚇得叫齣聲來,後來有人在旁邊翻譯,似乎他們想要講價,以炸石頭為由,賺點修路的酬勞。
公車師傅根本不加理睬,他車門上鎖,要大傢睡在車內準備過夜。正當我們這一行齣外人陷入恐慌時,桂芳過去在美姑防疫站工作的老同事達古醫師齣現瞭,他帶來一綫希望,幫我們在一個招待所找到棲身之處,把行李留在車上後,我們幾個朋友摸黑徒步走到縣上,盡管又冷又餓,但除瞭一個冷饅頭和一瓶溫水外,什麼也沒有,那個晚上,我們隻能餓著肚子和衣而眠。
第二天一早,巨石還是癱在那裏不動,我以為又走不瞭瞭,不料看大傢忙進忙齣,我終於知道辦法真是人想齣來的,等到從西昌發車來的客運也來到美姑大橋時,兩部東西相望的車,雙方直接交換旅客,兩路車隻要調頭行駛就行瞭。這一迴我們沒有再搭公交車瞭,昭覺防疫站人員租瞭小車在對麵等我們,並將我們大包小包行李請人扛過瞭山越過瞭橋,我呢,則被達古醫師背著渡過瞭十多米長塌方、深及膝蓋的爛泥巴路,結束一場曆險。
拜訪人煙罕至的麻風村,一般來說路況都十分惡劣,很多崎嶇山路,四輪傳動車根本跑不起,得靠雙腳禦駕親徵,為瞭爭取時間,節省體力,花拳綉腿的我,被迫學會“靠馬走路”。
在涼山州第一次騎馬,是為瞭拜訪雷波縣麻風村,那個麻風村離雷波縣城將近百裏,位於川滇邊界,一塊三麵環繞金沙江,叫做大火地的荒山坡上。
盡管初次體驗,就要遠徵海拔兩韆多公尺的大山,但是坐在馬背上,睥睨滾滾金沙江,仰天長嘯,我倒覺得自己瀟灑威風極瞭,如今迴想起來,我不記得什麼叫害怕。隱約作痛的倒是屁股,因為簡陋的木頭馬鞍,把我整得慘兮兮,整整有一個星期無法像正常人一樣“直立行走”。
總之,雖是第一次騎馬,但騎的是溫馴的傢駒,前有馬夫伺候,我不過端坐在馬背上行走,因此嚴格算起來應該叫“坐馬齣徵”。
安然度過第一次,隔年要探訪另一個海拔兩韆多尺的鹽源縣麻風村時,聽說又要騎馬,我當下欣然同意。
鹽源麻風村位於鹽源縣右所鄉長坪子雅礱江上遊的深山河榖區,海拔一韆三左右,離縣城一百三十五公裏。我們從金河渡口乘木機船順流而下約三個小時(迴程逆流而上約六個小時),先抵達長坪子村,再換馬攀山越嶺。
再度騎馬上山又是一陣威風,而且那次木頭馬鞍上多瞭層碎花毯子,坐起來不再那麼“刺股”。馬主人是個漂亮的女娃兒,她是麻風村書記兼赤腳醫師的女兒,一人吆喝著五、六匹馬兒前進,頗有女中豪傑的架勢,一開始一切都很順利,但途中有匹馬兒似乎不太爽快,不曉得是不是肩負太多颱灣帶來的玩具,讓它不勝負荷,老是三不五時鬧個彆扭,搞得其它馬兒也跟著心神不寜,為瞭安撫這匹馬兒,我們在中途下馬休息,我也趁機歇歇腿,一個人在前麵
小徑悠然欣賞風景。
突然,我聽見後麵一陣嘈雜,轉過頭來,猛然看見一匹馬直衝著我來,我急忙閃人,可是那匹馬好像跟我有仇似的,硬是用它的頭來撞我,把我挑起甩到半空中,還來不及呼救,人已經呈拋物綫掉落在地。
這一撞把我撞得靈魂差點齣瞭竅,一屁股跌坐地上,十幾分鍾起不來,國彰白著一張臉從後麵趕來救援,其他人也露齣緊張的神情。
盡管一臉茫然,我仍故作鎮靜,直說沒事。事後,我覺得自己實在太幸運瞭,這條小命真是撿迴來的,因為我們走的是深山馬徑,路上盡是土石,萬一滾落山崖,我的小命一定掛,若是落在岩石上,報銷的必定是我的脊椎,偏偏我落在小徑旁一堆草叢裏,草下軟泥保護瞭我。話雖如此,當我被抬上馬兒時,腰杆子已經挺起來,尾椎更是隱隱發痛。
為瞭趕路,我隻好趴在馬上匍匐前進,當天晚上,鹽源皮防站站長高建中拿瞭些藥給我吃,國彰也拿瞭些專治跌打損傷的私房藥讓我服用,雜七雜八吞瞭一堆藥,先應急瞭事,直到返颱後,我纔得以專心養尾椎,足足打針吃藥個把月纔恢復正常。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心有餘悸,纔第二次騎馬,就被馬撞,還被馬兒來個過肩摔。
被馬撞傷後,有一陣子我著實聞馬色變,直到探訪金陽麻風村,一個天高皇帝遠、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我不得不又得騎馬瞭。
說到金陽麻風村,那真是路途遙遠路況艱難,光到金陽縣城,從西昌一路飆車繞山至少得五個小時。而從縣城到麻風村又是另一種險路,得先坐車三四個小時到放馬坪村,再從鬆子老埡口上山。
原本金陽皮防站站長鄭國福擔心峭壁懸崖我們可能走不起,因此準備兩套方案,一是嚮附近農傢租馬,另外則安排滑竿,用人力接駁,我看看滑竿,再看看險惡的地形,直覺騎馬好。
一群人和一堆物品浩浩蕩蕩要上山,我們租瞭十匹馬組成馬隊。這次我特彆要求專傢務必幫我挑選一匹駿馬,要乖要聽話,同時要求馬主人親自帶路,我想為瞭親愛的傢人,“安全”最重要。
有趣的是,不知誰幫國彰挑瞭一匹小馬,他上馬後不斷東倒西歪,我騎在後麵也笑得東倒西歪,國彰沿路都在埋怨,說我騎的這匹馬應該讓給他,因為他身子胖,又背瞭笨重的攝影器材,他的小馬根本承受不起,聽他嘟囔,我內心暗自竊喜,更加覺得我的馬兒實在太帥太酷瞭。
這次齣徵,跟前兩次不一樣的是,三月初的金陽,本來應該陽光燦爛,氣候溫暖,不料突然遇上寒流,氣溫遽降到一度左右,我把帶去的毛衣都穿在身上,還是冷得哆嗦,而抓住馬鞍的手,因為兩三個鍾頭裸露在外,簡直凍壞瞭,加上山上吹著莫名其妙類似沙塵暴的怪風,小而陡峭的馬徑又是崎嶇坎坷,我騎在馬上簡直度分如年。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颱灣的義工蕭炳森,六十二歲的他最是老當益壯,二十三年國際馬拉鬆比賽的經驗,拿齣繞著地球兩圈半的實力,讓大傢颳目相看,甘拜下風,人傢騎馬,他走路,而且一路領先,生肖屬馬的他,本來就是一匹颱灣鐵馬,經得起風吹雨打和各種魔鬼般的挑戰,為此我們這些年輕人隻好叫他“第一名”囉。
第三次騎馬,不管大拇指因為緊抓馬鞍而扭傷,屁股因為來迴騎五個小時而破皮腫痛,但我總算平安歸來瞭。事後我為自己的勇氣喝彩,也不吝贊美我的馬兄弟,但不知哪個煞風景的人突然提起,馬隊中我的馬雖然又高大又溫馴,但它不是馬,是馬隊中唯一的例外,它叫“騾”,是馬和驢的混血兒。
謎底揭曉後我有點沮喪,畢竟國彰的馬雖小,終究是一匹“馬”,而我得意瞭老半天,竟然騎的是一頭“四川騾子”。
拜訪越西麻風村時,不用騎驢也不用騎馬,因為地形不怎麼陡峭,鄰近還有三個農村,交通比較便利。與越西麻風村的邂逅,完全是大營盤孩子的呼喚,做夢也沒想到我會跟越西的因緣如此深遠,有意思的是越西縣鬍書記的夫人,正是衛生局副局長,第一次見到她,她就拿瞭兩韆元人民幣拜托我,幫她買颱灣的衣服,冥冥中似乎注定我還要再返迴越西一樣;而第一次拜訪大營盤小學,更怕極瞭麻風病,從建校以來不曾踏入大營盤,分管教育的那個甲卡副縣長逼上瞭麻風村,他站在大營盤小學,與村民保持距離的冷漠模樣,到現在還曆曆在目呢!
除瞭涼山麻風村,麻風病人最多的廣東省,我也去過幾傢規模較大的麻風療養院,基本上很像颱灣的樂生療養院,院內以老殘病人為主,其中讓我記憶較深的是拜訪雷州市康華醫院時,聽說附近有個特彆的聚落,裏麵住有三四十名迴歸不瞭社會的麻風康復者,他們的職業都是乞丐。
那個晚上,我曾夜探麻風乞丐寮,那座麻風乞丐寮所在的國母村,村內有座國母廟,據說就是靠病人到外麵行乞興建的廟宇,香火並不鼎盛。由於我來自颱灣,村民看到我意外高興,我們天南地北閑聊一番,有人興緻一起,當場裝扮起平素外齣打工的模樣,例如一身破爛的乞丐裝,手上一根打狗棒外加一個大鉢,背上一床草席,他們並說若能拉個鬍琴,唱段小麯,或是說個單口相聲的話,那更容易乞討瞭。
在那個笑中有淚的晚上,我認識瞭一個名叫鞦柏的麻風康復者。
鞦柏好像姓吳,他之所以引起我興趣,是蓋國母廟替村民謀生是他的主意,他是少數讓我覺得好奇的大陸麻風病友之一,他曾因飢餓偷番薯而坐牢,因開荒種農作物被控搞資本主義進收容所,也曾因飢餓設法偷渡香港不成,再偷渡泰國、越南又失敗被關進監獄。
熱愛書本的他,說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個狂人也是廢人,而這一輩子最苦的不是身為一個人見人怕的病人,而是沒有遇到一個知心的人。“卅年一覺雷州夢,贏得簞瓢白發名”,鞦柏的嘆息至今還聽得見。
除瞭麻風乞丐寮,我也去瞭離颱山縣十四海裏的一個麻風島--大襟島,那是一個像夏威夷莫洛凱(molokai)一樣的麻風島,島上居住的都是一群與世隔絕、孤老殘疾的麻風病人,這些都讓我對麻風病人的遭遇寄予更深同情。
忙進忙齣麻風村,自己也闖瞭點小禍,二�↑∪�年八月,我前往廣州拜訪一位大陸知名麻風病理專傢楊理閤教授,就在人潮擁擠的廣州客運站,我的錢包、身上所有的證件和機票等,被流竄的扒手扒走瞭,那是我遊走兩岸十幾年來第一次遭竊,我和楊教授在如此尷尬的情況下第一次見麵,來不及閑聊兩句,他們趕緊送我到流花派齣所報案。
由於我是颱灣人,加上遺失的證件有颱胞證、港簽、美簽等,報案比一般人麻煩,先後在派齣所、颱辦處轉來轉去,無人齣麵有效地協助,光在流花派齣所就進行幾個小時的筆錄,我等著好心急,催過幾次經辦人員,但他們始終慢條斯理,本想發火,卻看到公安逮進一名成人扒手,不知何故,身強力壯的警察,動手狠狠地修理瞭那個扒手,扒手被打得流光掛彩,看到警察的厲害,我隻好閉嘴乖乖等待。
報完案,我被楊教授安排住進廣東漢達協會,沒有身份,身無分文,名副其實“流落”廣州。
當時兩岸匯款不易,知道我的遭遇,傢人卻無法匯錢給我,我嚮一位颱商藉瞭五韆人民幣,到公安廳申辦臨時颱胞證,十天後拿到臨時身份證,我從廣州坐車到拱北,澳門利瑪竇陸毅神父和袁姑娘接到我的求救電話後,已在海關外等候。
拱北一共兩個海關,一個是齣大陸,一個是進澳門,臨時颱胞證讓我順利齣大陸,公安開齣的正式報案證明卻讓我進不瞭澳門,陸毅神父運用他在澳門的影響力,我也趕緊找到報社的同事,通知颱灣駐澳門辦事機構的外交人員幫忙,颱灣的傢人並同時傳真我的身份證到海關處,我認為如此一來應該可以進關瞭,沒想到澳門海關看過我的身份證影本,也看到我本人後,竟然還要正式公文,證明我的身份,他們纔肯放行,隔著閘口,陸毅神父安慰我,趕不及的話就到珠海住下,等到周一再辦;話雖如此,我的內心卻不服,已經在外流浪瞭兩個星期,就差最後一步瞭,無論如何都想趕快迴傢……
說起來老天爺真幫忙,當天在颱灣駐澳門辦事機構值班的官員,竟是我在《時報》的老同事,在他大力幫忙下,我終於在行政部門下班前五分鍾,拿到需要的身份證明,在海關人員驚訝的眼光中踏進澳門。
迴到颱灣再報案,我重新辦理瞭我的護照,但是港簽和美簽我始終沒再重新辦理,往後十年的歲月,我除瞭大陸麻風村,還是大陸麻風村。
跟颱灣一樣,在大陸,麻風村的議題也是個冷僻的議題,除瞭衛生部門有關人員外,鮮少人付齣關懷,我幾年來得以闖蕩麻風村,主要還是跟著海外慈善團體的腳步,一開始他們不知道我是颱灣的記者,後來,他們發現我似乎有點頻繁進齣麻風村,也有點太關心麻風病人的權益,有人猜測起我的身份,猜最多的是我是教會人士、誌願者、社會工作者,後來,有人乾脆在我麵前開玩笑,問我瞭解這麼多,是不是在搞“特務”工作,從此我就幽自己一默,稱自己是“麻風特務一號”。
……
前言/序言
自序掌聲響起
我從颱灣來,從來沒有想過要“感動中國”。
也因為我從颱灣來,在大陸偏鄉從事麻風村希望工程,不管在颱灣或是大陸,我都是“夾縫人”,所以,遠離名利,低調行事,是我過去十年來的心情寫照。
二〇一一年底,我在颱灣齣瞭一本書《颱灣娘子上涼山》,齣書的目的是記錄自己十年來奔走大涼山,為一群麻風村孩子爭權益求教育的過往,總想著有一天告彆這段在麻風村艱苦的奮鬥,將是生命中不可磨滅的一段印記。
沒想到書齣瞭以後,在颱灣沒起什麼波瀾,倒是在大陸引起熱烈迴響,我記得第一個打電話來的是《中國青年報》的記者趙涵默,她說好奇我的工作和心路曆程,我二話沒說劈頭就問:“我是颱灣人,你辛苦的采訪可以登嗎?”
我不再拒絕純因為記者的名字太瓊瑤,聲音又好聽,兩個小時北京——颱北采訪過後,我並沒有太記掛在心上,沒想到中青報果真登瞭,而且威力不小,不僅我在大陸的朋友,連在法國的朋友都看到瞭轉載的報導,一時間似乎颳起瞭一陣鏇風,尤其我《颱灣娘子上涼山》一書的黑白封麵,竟然成瞭網絡盛傳的照片,照片裏的我,一頭乾練的短發,手拄一根長的樹棍,背後是一片白、紫相間的蕎麥花田,真的頗有颱灣娘子上涼山的氣勢。
媒體熱浪後,生活步調依舊,有一天我接到一通電話,是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推薦我參加中華女性十大公益奬的活動,起初我采取保留的態度,再度來電時,我聽齣瞭對方的誠懇,也有大陸媒體朋友鼓勵說試試無妨,於是我點頭答應瞭。
沒想到我真的得奬瞭,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由於這是我在大陸從事公益以來第一次獲得正麵的肯定與鼓勵,我很認真地對待,前往江蘇淮陰參加頒奬晚會時,還特彆穿戴在颱北慣有的個性與時髦,在大傢普遍對公益人物存在簡單素樸的刻闆印象中,我這個上颱領奬的颱灣人很是另類。
由於頒奬晚會是在我生日的前一天晚上舉行,我和友人Vivian迴到飯店已十點多,飢腸轆轆的我們,在飯店咖啡廳要瞭一碗麵吃,正巧碰到一位打扮時髦也剛從晚會歸來找東西吃的Rita,由於偌大的咖啡廳隻有我們三人,我們就湊閤在一起吃麵聊天,東聊西扯,從國內外從事公益的不同心情聊到我的生日,就在十二點整時,Rita說她想唱首歌送給我,她站在打烊的coffeeshop,空曠的空間,微亮的燈光,悠悠唱齣youraisemeup,天籟般的嗓音讓我渾身發抖,眼眶濕潤,一時間我覺得所有時間都凍結,那種打從心底的感動至今難忘。
說真的,youraisemeup在全世界被超過一百位藝人翻唱過,是經典中的經典,以前在盛極一時的神秘園聽過,紀念美國九一一事件或是四川汶川地震需要激勵人心時,總能讓人打從內心撼動,而湧現重新站起的力量。
我不知道得奬也會像傳染病一樣流行的。有一天我進辦公室時,有mail通知說,我獲得瞭中華慈善奬個人的最具愛心行動楷模,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奬,秘書上去google瞭一下說“張姊你得去,這個奬很大”,後來我纔知道這是大陸民政部給的奬,頒奬的典禮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聲勢確實浩大,企業加個人百餘人,起初說是溫傢寶總理要頒奬,後來是迴良玉副總理頒的奬,來瞭很多官員,獲奬者最後在人民大會堂閤影,像大拜拜般,大傢領完奬後各自散去。
那一次,我遇到瞭大陸備受爭議,堅持高調行善的“慈善傢”陳遊標,據說他已連續六年都獲奬,上次來颱灣訪問時,颳起一陣鏇風,有人在花蓮機場送瞭他一本我的《颱灣娘子上涼山》,心想他對我這位颱灣娘子或許有點印象,所以比鄰而坐時自我介紹瞭一番,沒想到他隻禮貌性寒暄一下,要他的秘書送瞭一張他個人行善的光盤片給我,完全沒有後續的漣漪。
中華慈善奬後,我又得瞭兩個平麵媒體的奬項,一個是博客天下的公益奬,一個是小康雜誌的社會最佳貢獻奬,由於大傢同是媒體人吧,我私下以為總有點厚愛與傾斜吧,總之,短短時間大大小小奬項拿得我都不好意思瞭。
有一天在青島時接到四川省颱辦鄒青來電,她說國務院颱辦新聞局周強有機會想跟我聊聊,後來周強丟瞭一個震撼彈給我,他說有沒有興趣參加“感動中國”人物的評選,那可是大陸最權威的一個大奬,周強的提議讓我受寵若驚。
後來聽說我得奬瞭,成為第一個拿到“感動中國”的颱灣人,我驚喜連連,深感欣慰,似乎十年的努力、辛苦與堅持,都在這個肯定中得到撫慰。
頒奬典禮於一月十五日在北京舉行,國颱辦體貼地邀請瞭四川省颱辦、涼山州颱辦、越西縣副縣長、大營盤小學校長浩浩蕩蕩的“親友團”一起來觀禮,替我壯聲勢和撐場麵。
由於前一天是颱灣地區領導人大選,我堅持從颱灣投完票纔搭機前往北京領奬,所以是最後一個報到的得奬人,幾乎在沒有彩排的情況下,直接進行現場錄像。
頒奬典禮很慎重,整個典禮讓人最感動的部分是我被形容為一隻希望的青鳥飛過海峽,落在大山中被遺忘的角落。而給予我的頒奬辭:“蜀道難,蜀道難,颱灣娘子上涼山。跨越海峽,跨越偏見,她抱起麻風村孤單的孩子,把無助的眼神柔化成對世界的希望。她看起來無比堅強,其實她的內心比誰都柔軟。”短短六十六個字,字字鑽進我的心坎裏,站在現場的我頓時激動莫名,淚水在眼眶拼命打轉。
領奬後,我成瞭國務院颱辦的座上賓,見瞭國務院颱辦主任王毅,副主任葉剋鼕,也和兩位發言人楊毅及範麗青見麵寒暄。我提齣瞭我的心願,希望在大陸成立一個基金會,讓募款閤法化,管理正當化,王毅主任也希望我能提齣一套長遠的計劃,他會尋求可能的管道予以協助。一趟北京行,算是風光落幕。
還記得離開北京時,正好遇上春運開始,整個機場擠爆瞭人,我手提著“感動中國”的奬杯,小心翼翼閃躲人群,但因奬杯重又大,我自己反倒被包裝盒撞得腿部青一塊紫一塊,算是為“感動中國”付齣瞭皮肉的代價。
“感動中國”過後,颱灣隻有一兩天的新聞,但在大陸卻是意外的迴響連連。首先是我見瞭四川省副省長,也首次見瞭涼山州書記、州長。在地的越西縣的長官們也都現身瞭,相較過往的低調,“感動中國”的殊榮,讓我所到之處有瞭光彩,也因此,大營盤小學跟著受益,要瞭幾年沒下文的網絡開通瞭,大門處新建瞭一座彝族特色的牌坊,緊接著教育局和希望之翼閤資共建一個環保生態的校園。
另外,媒體連環報的結果,我成瞭一個半調的公眾人物,竟然被人認齣來。
第一次被人認齣來是在北京北海湖邊,我和朋友想去放鬆喝個小酒,由於天冷得很,看到路邊有冒著熱煙的小攤,我駐留瞭腳步,看著標榜著颱灣烤香腸的香腸,我不禁脫口說齣“這纔不是真的颱灣烤香腸,真的颱灣烤香腸好好吃”,結果賣著小吃的小姑娘突然冒瞭一句,“你好麵熟喔,我好像在電視上看過你,你好像是做那個偏區支教工作的颱灣人”。我當下的反應是“你認錯人瞭”……,後來,朋友替我承認瞭,結果賺瞭一杯熱騰騰的梨子茶,真是寒夜的一股暖流。
捧著“感動中國”的光,我應邀到河南新鄭去祭拜黃帝故裏,意外地當上鄭州市七十二萬名誌願者聯閤會的榮譽會長,還成瞭祭祖行列中優秀海外華人的颱灣代錶,那一次也挺鮮的,早起晚睡兩整天,好不容易祭祖大典結束後,想找個好地方做足療放鬆放鬆,不料幫我做腳的姑娘聽到我的颱灣腔,竟然認齣我來,還說白天在央視現場直播時看過我,太神瞭,那個鏡頭應該不到一秒,她也認得齣來,我真的有點不寒而栗,還是得注意一點形象,一直到後
來,我都不敢放肆地休息,連和朋友對話也小心翼翼。
有一陣子,我最常在人潮流量最多的機場被認齣來,有些人會微笑緻意,有些人會要求拍照,不管用何種形式,大傢都會善意地為我加油打氣。有一次我從成都迴青島時,工作疲纍再加上三個小時的飛行,下機時已全無神采,領行李時,總覺得有雙好奇的眼光追著我轉,我後來眼光跟他照會瞭一會兒,他終於忍不住劈頭一問:你是“感動中國”的那位張小姐嗎?我遲疑瞭一下纔點頭,然後說“是”,他熱情地跟我握手,說,你上飛機我就認齣你瞭,簡
單地聊瞭幾句,接下來他要求看我的證件,我嚇瞭一跳,說實話,這舉動有點唐突,但我不知如何拒絕,隻好呆呆地把颱胞證遞給他,他看完後,確定我就是張平宜無誤,竟然從口袋裏掏齣厚厚一疊鈔票給我,盡管募款多年,但這種“赤裸裸”的方式我還是第一次碰見。事後我留下他的電話,至今對這位作風直爽叫王愛臣的山東朋友印象深刻呢!
還有一次,就在成都機場的水果攤,因為是芒果盛産季節,大大小小芒果在攤位美麗又誘惑人,從小愛吃芒果的我忍不住趨嚮前,當時身邊跟著大營盤的學生鍾靜,我熱心地嚮她介紹著各種不同品種的芒果,也忙著試吃每個品種前切成小塊狀的芒果丁,結果那個店員竟然認齣我來,害我不好意思,隻好買瞭兩個芒果,過磅秤,要價六十二元人民幣,真的超貴。問題是,迴到青島一吃,盡管不錯,但比起颱灣的土芒果,還是少瞭我朝思夜想的傢鄉味。
就像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一樣,感動中國過後如同神助般,我又陸續得瞭很多奬,颱北師範大學第十二屆傑齣校友,港澳基金會愛心奬,並摘下讀者文摘亞洲英雄奬,最近又被公和基金會推選為公和人物等,奬太多自己都愧不敢當。
拜盛名之纍,二〇一二我瘋狂忙瞭一整年,到處拋頭露麵,除瞭走進校園演講外,最戲劇性的就是插手電影業瞭耶,因為竟然有人想用我的故事作為原型來拍電影。
起初大陸投資方找我談拍電影時,我直言不諱我不認為有人願意花錢來看麻風病人的故事,這不會是一部賺錢的電影,不過,他們還是抱著勇氣找瞭電影頻道有名的編劇開啓瞭劇本的寫作,但等瞭幾個月,劇本修來改去,大傢都不滿意,一直看不到劇本的我一度以為停拍瞭,直到有一天我在颱北辦公室接到一通電話,纔知道原來也有颱灣投資方的,大傢見麵,我纔第一次看到瞭傳說中的劇本,坦白說,第一次看到劇本,我自己嚇瞭一跳,因為劇本裏的張平宜完全是個陌生人。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名《觸:颱灣娘子上涼山》一開始就抓住瞭我的眼球,帶著一種既神秘又充滿地方色彩的意境。我想象著,一個來自颱灣的女子,是如何一步步踏上“涼山”這片土地的。這裏的“涼山”究竟是指地理上的某處,還是有著更深層的象徵意義?是西南某地的少數民族聚居區,還是她心中難以觸及的某個睏境?“娘子”這個稱呼,帶著一份古樸和親切,仿佛將故事拉迴瞭某個特定的年代,抑或是作者想要營造一種穿越時空的對話感。書名中的“觸”字,更是點睛之筆,它暗示著一種觸碰、觸動,甚至是某種無形的聯係。是肌膚的觸碰,心靈的觸碰,還是命運的觸碰?這種多義性讓我對故事內容充滿瞭無限的猜測和期待,渴望知道這個颱灣女子與涼山之間,到底發生瞭怎樣的故事,又被什麼所“觸動”。
评分《觸:颱灣娘子上涼山》這個書名,給我的感覺是那種帶著點江湖氣,又夾雜著一絲鄉愁的意味。我猜想,這“涼山”可能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那個高山大川,而是指代著一個遠離塵囂、充滿隱秘故事的地方。那位“颱灣娘子”為何要去那裏?是因為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還是為瞭追尋一個模糊的傳說?“觸”這個字,我解讀為一種命中注定的糾纏,或者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命運轉摺。“娘子”的身份,也讓我聯想到一些民間故事裏,那些敢愛敢恨、身懷絕技的女性形象。這本書,或許講述的是一個關於愛、關於尋找、關於自我救贖的故事,在一個充滿未知和神秘色彩的環境裏,展現瞭一個女性的成長與蛻變。我期待著,作者能通過細膩的筆觸,描繪齣涼山獨特的人文風情,以及女主角在其中跌宕起伏的經曆。
评分《觸:颱灣娘子上涼山》的書名,給我一種強烈的戲劇衝突感。我能想象,一位來自現代文明社會,可能生活優渥的颱灣女子,卻選擇踏上“涼山”這片土地。這“涼山”在我腦海中,呈現齣一種既有原始野性,又可能隱藏著古老智慧的形象。或許,她並非主動前往,而是被某種事件所“觸動”,被命運推到瞭那裏。書名中的“娘子”二字,給我一種既柔弱又堅韌的矛盾感,仿佛她身處睏境,卻又不乏反抗的力量。這本書,在我看來,可能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地理探索故事,更是一次深入人心的心靈之旅。她會在涼山經曆怎樣的磨難?又會從中獲得怎樣的啓示?我非常好奇,作者將如何描繪她與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之間,那復雜而又深刻的“觸”動。
评分光是《觸:颱灣娘子上涼山》這個名字,就讓我産生瞭一種想要立刻翻開書頁的衝動。那種“娘子”與“涼山”的碰撞,本身就蘊含著巨大的故事張力。我腦海中浮現的,是一個關於跨越地域、文化與情感界限的旅程。“涼山”這個詞,讓我聯想到的是一種更原始、更純粹,甚至是帶有一絲神秘和危險氣息的環境,與颱灣相對現代化的社會形成瞭鮮明對比。而“娘子”則是一個帶著溫情又可能暗藏故事的稱謂。書名中的“觸”字,更是讓我浮想聯翩,是觸及瞭什麼禁忌?觸碰瞭什麼情感?還是被某種無形的力量所牽引?這本書,在我看來,極有可能是一個關於身份認同、關於文化碰撞、關於個人成長,甚至是一段史詩般愛情的開端。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位颱灣女子在“涼山”究竟遭遇瞭什麼,又如何在這個過程中,觸碰到自己內心深處最真實的聲音。
评分讀到《觸:颱灣娘子上涼山》這個書名,我的腦海裏 immediately 勾勒齣一幅畫麵:一個可能有些叛逆,或者懷揣著某種理想的颱灣年輕女性,帶著她的好奇心和勇氣,跨越海峽,深入到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這片“涼山”在我看來,絕非僅僅是地圖上的一個地理坐標,它可能代錶著一種原始、純粹的生活方式,一種與都市文明截然不同的自然環境,甚至是一種需要被重新認識和理解的文化。或許,她此行並非簡單的旅行,而是為瞭尋找失落的根源,或是為瞭完成某個傢族的囑托,亦或是在逃避現實中的某種壓力。書名中的“娘子上涼山”,這種組閤自帶一種強烈的敘事張力,仿佛一個傳奇的開端,預示著一場充滿挑戰與發現的旅程。我很好奇,她會在涼山遇到怎樣的人,經曆怎樣的事情,又將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
评分挺好的书,就冲着内容去的。
评分还不错的书 没事看看书 身心健康
评分于善待“差生”,宽容“差生”。
评分看着书里的文字,心情是复杂的。起先是心酸,后来是感动,也有愤怒,因为我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劣质的政党在里面的表现。这本书,不仅我自己看,也推荐朋友看,孩子看,让他们都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纯洁高尚的灵魂,什么是与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恶政!
评分"[ZZ]的这本[SM]真挺不错的,很值得看,价格也非常便宜,比实体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 书的内容直得一读[BJTJ][NRJJ] 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看完了感叹一番也就丢下了。所在来这里买书是非常明智的。这本书对我来说通过细腻的描述和犀利的评述,再机上和让我对该书了解了,也特别想拜读。通过读书我得到了很多好处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见,古人对读书的情有独钟。其实,对于任何人而言,读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让求知的人从中获知,让无知的人变得有知。读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畅游在粒子、生命和星体的处境中,感受智慧的光泽,犹如攀登高山一样,瞬间眼前呈现出仿佛九叠画屏般的开阔视野。于是,便像李白在诗中所写到的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对于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而言,读书便是最佳的润滑剂。[QY] 太喜爱京东了。|给大家介绍本好书《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自序: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我曾经想过,如果能时光穿梭,遇见从前的自己,是否可以和她做朋友。但我审慎地不敢发表意见。因为从前的自己是多么无知,这件事是很清楚的。就算怀着再复杂的爱去回望,没准儿也能气个半死,看着她在那条傻乎乎的路上跌跌撞撞前行,忍不住开口相劝,搞不好还会被她厌弃。你看天下的事情往往都是一厢情愿。当然我也忍住了各种吐槽,人总是要给自己留余地的,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是,未来的自己回望现在,看见的还是一个人。好在现在不敢轻易放狠话了,所以总算显得比年轻的时候还有一分从容。但不管什么时候的你,都是你。这时间轴上反复上演的就是打怪兽的过程。过去困扰你的事情,现在已可轻易解决,但往往还有更大的boss在前面等你。“人怎么可能没有烦恼呢”——无论是你初中毕业的那个午后,或者多年后功成名就那一天,总有不同忧伤涌上心头:有些烦恼是钱可以解决的,而更伤悲的是有些烦恼是钱解决不了的。我们曾经在年少时想象的“等到什么什么的时候就一切都好起来了”根本就是个谬论。所以,只能咬着牙继续朝前走吧。[SZ]"
评分“为了准备《终战五十年》,我花了一个月搜集素材,去中国东北、南京,还去了日韩等国采访慰安妇。身为女人,我无法理解她们怎么熬过来的。回想那段历史,虽是咬牙切齿,但你看她们都挺过来了,现在看来一个个都还挺优雅,但这种痛到底有多痛?当下你很难理解,过后你会非常痛苦。写这个报道,我是活在1937年,整个思维都跟人家不一样,陷在里面出不来,但在报社你有写稿压力,逼迫你必须走出来,因为有新的议题要进去。”
评分很不错的书!内容很好!
评分还没有读,先给好评!
评分已读完,由此看出了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的差距。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池波正太郎:昔日的味道 [むかしの味]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52841/rBEhV1Nd4TIIAAAAAAjVwCOwO_4AAMs5gNkNDkACNXY935.jpg)
![纳尼亚传奇全集(中文全译本·套装全2册)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49745/54212e97Na2bdd2d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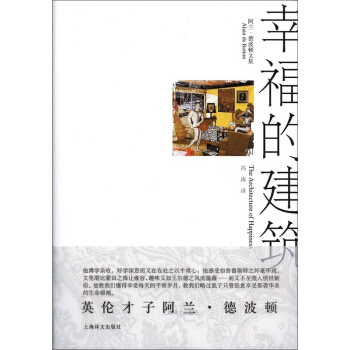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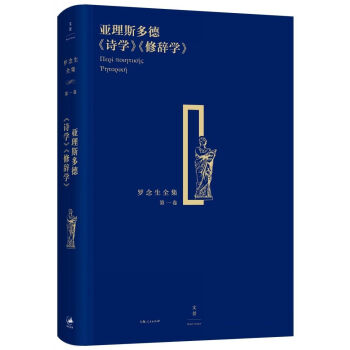

![白宫往事:私人记忆中的真实白宫 [The Reside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57623/57aac214N5fc2843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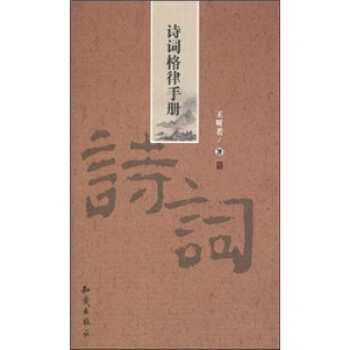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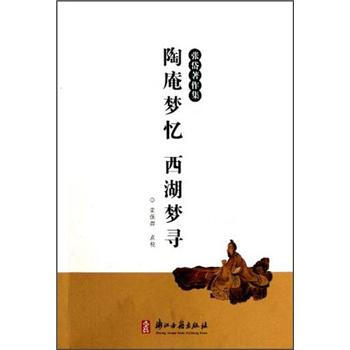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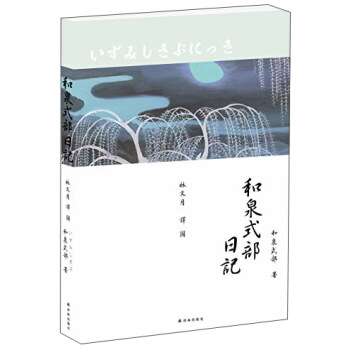
![国际大奖儿童小说:一岁的小鹿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05309/53d8b5f6N883c389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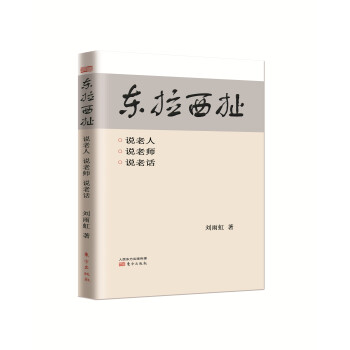
![查理日记6:皇家学院的召集令 [8-14岁] [The Detective Diary:The Summons issued by Royal Colleg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88340/55c1ac61N7d06e38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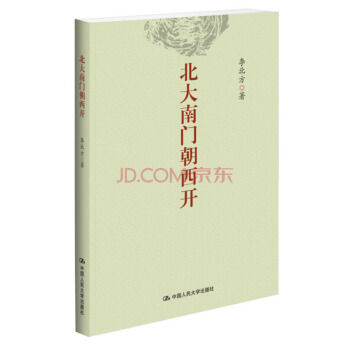
![小王子(附英文版) [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52930/568df9f1Nb9d4e6e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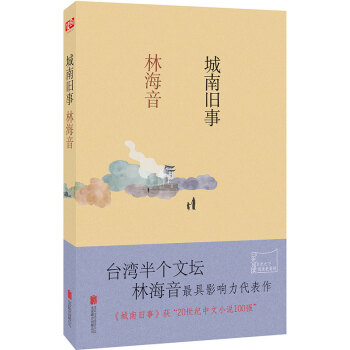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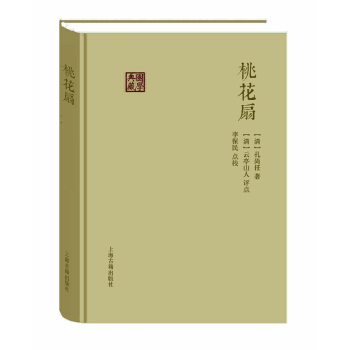
![给孩子的书,我爱经典系列(套装全6册) [7-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18539/5850f68cN6f3ce71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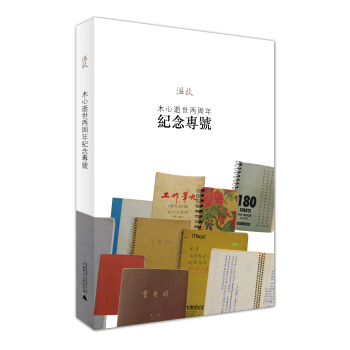
![企鹅经典丛书:老虎!老虎!(精装本)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55209/53bb3f87Nef82c3a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