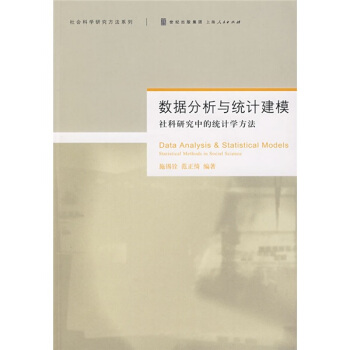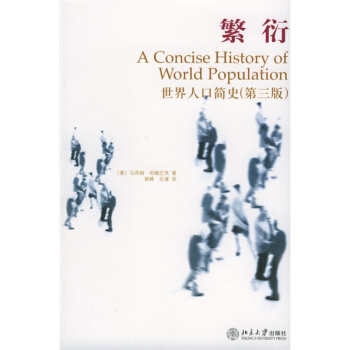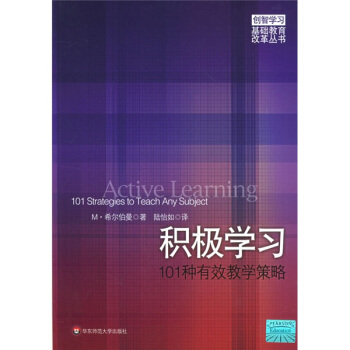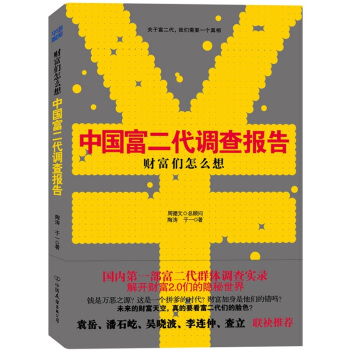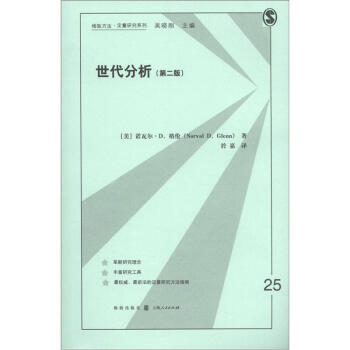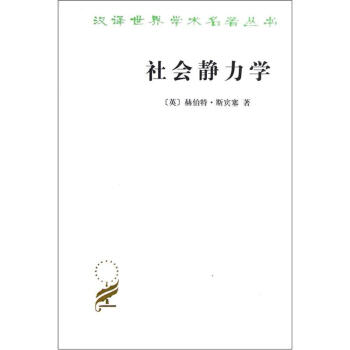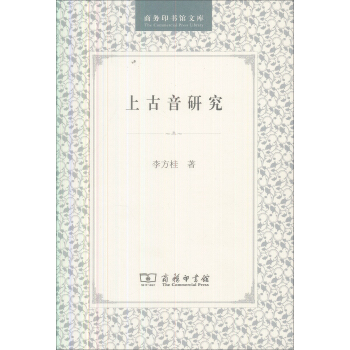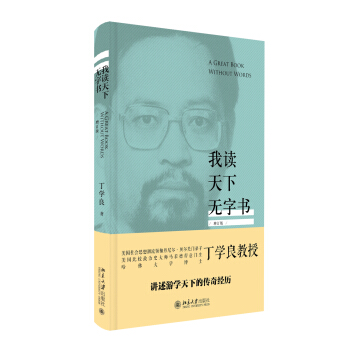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我讀天下無字書(增訂版)》:美國社會思潮領頭人丹尼爾·貝爾關門弟子
美國比較政治史大師馬若德得意門生
知名學者、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教授
講述遊學天下的傳奇經曆
抒寫世界文化“無字大書”的深刻體悟
全書內容豐富,敘述生動,視野宏闊,論述精到,是經典的學術文化佳作。
內容簡介
知名學者丁學良教授,以講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講述瞭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美國、亞洲、歐洲、澳洲、中國颱灣等國傢、地區的遊學曆程,其中既有與世界齣色學者的近距離接觸,也有對於世界精英學府的親身體驗,既有對於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製度的敏銳分析,也有對於世界各地豐富多彩的文化"無字大書"的酣暢灕淋的體悟。《我讀天下無字書(增訂版)》內容豐富,敘述生動,視野宏闊,論述精到,是不可多得的學術文化佳作。
作者簡介
丁學良,齣身皖南農村,在國內受過不完整的小學、初中和高等教育。1984年夏赴美國讀書,1992年春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曆年來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從事教學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兼任深圳大學 “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 學術指導。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現代化/發展、轉型社會、國際競爭與大學製度、政治幽默。目錄
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哈佛大學前校長、大纔子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
哈佛大學文理學院中各懷異能的研究生們
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的東南亞高手們
不可替代的東南亞政治經濟專傢汪老爺子
古風猶存的"聯閤報係"創始人王惕吾先生
不棄理想的"永遠的老年輕"於光遠先生
在匹茲堡大學同受洋罪的王小波
精彩書摘
一個不棄理想的社會主義者——憶“永遠的老年輕”於光遠先生
我跟於光遠先生的交往始於1981年,當時我正在復旦大學哲學係做碩士論文,主題是歐洲人道主義傳統和馬剋思社會理想的淵源。在上海能找到的外文資料和著名學者還嫌不夠,特申請來北京查索資料拜見名傢。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來北京,住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原校區,裏麵都是亂七八糟的煤堆、黃泥、垃圾、騾馬車、驢糞蛋。我是皖南農村背景的學生,對北京學術界的宏大氣氛早就無比嚮往。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思想學術界處於百傢爭鳴、韆花齊放的春天。改革開放的初期,物質生活的素質上海是中國的第一世界,北京是第三世界;但在思想學術上,恰好相反。
“馬列主義也比須是科學研究的對象!”
當時教育部有個文件,據說是從鄧小平那裏要來的一個特權: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摺騰,全國高校係統教師隊伍都是青黃不接,呈現斷代危機,因此名牌大學自己培養的前三屆研究生(指1978年到1980年入學的,當時隻有碩士生班,還沒有博士生班)畢業後,本校有優先的留校使用權,任何中央部委及其下屬部門均不能去搶人。這可是個特許,那時還是計劃經濟,當時最著名的大學,如北大、復旦,都有這個特權。1982年夏天我畢業,復旦大學把我安排在優先留校的名額中。在當時絕大部分復旦同學的眼中,這可是全國最好的分配齣路。上海人不願意離開上海,文革期間幾百萬下鄉的上海知識青年正韆方百計要迴來,比登天還難。你這個安徽佬,竟然有如此的運氣!
雖然我在上海人眼裏從麻雀一下子變成瞭鳳凰,但心裏頭還是嚮往著北京,想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全稱馬剋思列寜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去工作。我一聽自己留校瞭反倒急瞭,知道中央特許的分配政策的權威性,於是主動跟北京馬列所方麵私下聯係,請求他們把我調過去。馬列所是當時的中國社科院“第一所”,因為馬列主義具指導地位,改革開放之前卻沒有這個所。於光遠是推動建所最力的一個人,建所目的很清楚,他說:馬列主義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在中國無異議。但“四人幫”把馬列主義變成瞭教條和迷信,我們要把馬、恩、列、斯、毛的理論變成科學研究的對象。他沒有明講的是:馬列主義不應該是崇拜的對象,而是一種“社會科學”,要隨著時代而發展,其中隱含瞭跟科學必須保持一緻的研究方法和評價標準。
聽說,剛開始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科院院長鬍喬木親自擔任馬列所的所長,於光遠當第一副所長。這規格是最高的瞭。但鬍喬木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當院長所長,而是全黨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他跟於光遠說:我太忙,你就代勞吧,當首任所長。
於光遠其實也忙得一塌糊塗。鄧小平最重要的四個理論工作助手,鬍喬木、於光遠、鄧力群,還有資深經濟學傢薛暮橋。薛老年紀很大瞭,活躍程度比不上這三位。於光遠於是讓毛澤東當年稱為“四個紅色教授”之一的經濟學傢蘇紹智當第一副所長,是從人民日報社調過來的,更早些年前蘇先生曾在復旦大學經濟係教書。
我1981年初春赴北京收集論文資料,特地拜訪瞭馬列所,隻是在走廊裏跟於光遠打瞭個招呼,他太忙,走路小跑步。那時候的馬列所位於西直門車公莊北京市委黨校大院裏,辦公地方是藉用的,建國門內大街上的中國社科院大樓還在蓋,那周邊是一片荒涼景象。
於光遠和蘇紹智兩位先生為著我的事,親自齣麵找到《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楊老在1954年擔任過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調到北京前是上海市委管高教的書記,前不久他參與領導組織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篇大文章的修訂成稿。於、蘇兩位通過他再給上海市領導打電話,這纔把我的分配名額從復旦大學調整到北京。我要求不留校時,學校管分配的乾部說瞭句狠話:我們留一個人很慎重,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留也留不下來,你不要不識好歹,否則哪裏來哪裏去。
我當時可是破釜沉舟瞭,因為聽說很快國傢就要啓動博士研究生班試點招生瞭,我想,如果我分配被退迴安徽,就下決心硬考博士進京。幸好,於光遠、蘇紹智幾個電話一打,復旦大學把我的名額讓給瞭中國社科院。1982年9月29日我從上海進京報到,隻買到站票,連硬座都沒有,站瞭一天一夜。滿車廂的人看著我一路硬站,還喜氣洋洋,以為我有什麼毛病。
“最重要的,思想要興旺起來!”
就這樣我進瞭北京工作。在復旦時,我們對單位的領導要稱呼頭銜,叫蘇校長、金書記、林主任。但到中國社科院第一天上班,見到那些在全國學術界如雷貫耳的人物,除瞭稱鬍喬木為“喬木同誌”——也不喊“院長”,他笑笑就走過去瞭——,對其他人都一律稱呼“老師”。我們這些剛大學畢業的人覺得這樣叫,太親切瞭。於光遠有一大堆頭銜,都沒人叫,稱呼他“光遠老師”的年輕人,我開始還以為都是他帶的研究生,馬上發現所有年輕人都這樣喊他。
每周二全所成員都要來所裏政治學習,我就趁這個機會到光遠老師辦公室裏,說是來感謝您的。他說:“感謝什麼?都是為瞭工作嘛。你是做理論研究的,我們講粉碎四人幫後,中國要百廢俱興。最重要的,是思想要興旺起來。腦子不活躍,什麼都活不起來。”
我們的工作生活條件特差,單位食堂周末也不開夥,幸好那時周末隻有一天,到外麵買東西吃。也沒什麼好買的,也沒有多少錢,路邊攤買點油餅鹹菜,糊弄過去。改革開放之前沒有中國社科院,隻是中國科學院下屬的一個學部,我們都沒有房子住。北京本地人還可以騎車迴傢,我是外地人,隻好睡辦公室。最想當床用的是光遠老師的辦公桌,因為他級彆最高,文革前給毛澤東當過科技政策的秘書,辦公桌又長又寬,睡在上麵最舒服。他不是每天都來所裏上班,什麼時候來不知道,我也不敢對他造成任何乾擾。我每天在小研究室裏看書寫作,深夜沒人瞭,纔敢把捲起的鋪蓋打開。如果他的辦公室沒鎖,就睡在他的桌子上。第二天一大早,收拾得乾乾淨淨。
那時北京很小,到瞭魏公村地段就是郊區瞭,以下都是土路,我們也暫藉用過的朝陽區黨校就是農村,驢子和馬都能見到,一不小心,會把莊稼踩壞。我們單位還有在八寶山、首鋼附近租農民房住的同事,他們擠公交車,上下班來迴三個小時。我24小時在崗,連睡覺都在辦公室,時間利用率特高,文章發錶得特多,被錶揚時,我說:“還得感謝光遠老師”。他覺得很奇怪,問:為什麼要感謝我?“因為我常睡在你辦公桌上。”
他吃瞭一驚:“啊,怪不得我有時覺得辦公室裏有點氣味!”
因為啥?我周末孤獨,偶爾喝點二鍋頭。那時的二鍋頭很差勁,一股洗鍋水的味道,幾毛錢就能買一斤散裝酒,我買的是一塊多錢一斤瓶裝的,算是稍微好一點的。他周二來所裏辦公室的時候,有時候還是聞到有點氣味。
“官樣文章,絕不可以拿齣去!”
那時大傢對於光遠的評價五花八門,他資格老,清華大學物理係的高材生,後來到延安去投奔革命。他有幾件在當時引起爭議的事情,最主要的是說他“到處下蛋不孵雞”。他到處提思路齣主意,說這個問題要研究,那個學科那個分支要趕快設立,要辦一個學術刊物,要建一個學術團體。他地位高,發瞭話,下麵的人就要跟著辦。但他講得太多,彆人要給他代管的也太多。理解他的人說,那時中國剛恢復“雙百方針”,真需要這樣一個人能夠提齣新觀念、點齣新問題、開闢新方嚮。沒有他到處下蛋,彆的人功力不夠,信息不夠,權力也不夠,下不齣那樣的蛋。即便下瞭蛋,彆人也不願為他代管。
光遠老師的思想新穎異常,在他那樣的年紀群裏鶴立雞群。“文革”後他講,現在中國檔次最高的自然科學刊物叫《中國科學》,有中文版,最好的文章要譯成英文,按國際學術刊物的通例審稿發稿,索引完備。他說,也要辦一個《中國社會科學》,代錶中國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最高成果,否則怎麼把新時期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成果讓全世界瞭解?
他提齣來後,很多人興奮不已。但也有人問,自然科學普天下隻有一個標準,“四人幫”時講馬列主義的宇宙學、物理學、生物學,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資産階級僞科學,已經是超級笑話瞭。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有啥統一標準?於光遠堅持說,不對,也有。就該按照現代科學的邏輯、研究方法、驗證程序,實事求是地探索社會的和人文的問題。
有人追問,那也包括馬列主義嗎?他說:當然啦!
在1981-1982年那期間,這種思想很瞭不起。果然就辦起來瞭《中國社會科學》,他說要辦成全國最好的,絕不可以濫竽充數。宣傳品、抄文件的官樣文章,不可以拿去推銷,英文版要符閤國際學術界通則。
我1982年初成稿的碩士學位論文是討論人道主義問題,當時算是很新穎的主題,爭議也大。我把論文稍修訂後按程序投稿,寄給《中國社會科學》,那時的主編是後來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謝韜。我從文藝復興一直講到馬剋思及其批評者,文章三萬多字。當時匿名審稿,來迴修改幾次,全文發錶。隨後全國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第一次評青年學術成就奬,我獲得一等奬,除瞭奬狀,還有現金奬勵人民幣480元。那可是一筆巨款,拿到北京火車站對麵的鬍同小儲蓄所做活期存款,本單位團支部派齣一位團員同誌護送,怕在途中齣意外。
《中國社會科學》是光遠老師主張辦的,我又是他和蘇紹智老師親自調過來的。年輕人發錶長篇論文得瞭奬,他很高興,在走廊裏對我講:“看來花瞭那麼多力氣把你調來,也還沒調錯。”那時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錶一部長篇論文,可以破格被提為副教授副研究員,當時全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類的正教授正研究員也就一兩百個,稀罕至極。
那時馬列所裏一身兼多職的老資格研究員有好幾位,另一名副所長王惠德是中宣部副部長,還有副所長馮蘭瑞老太太,延安整風時她的直接上司是薄一波,還有其他延安時代的知識分子老乾部,前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王若水一度也要求來所裏任兼職研究員。一發生重要的事情,光遠老師和他們就會來通通氣,消息非常靈通。
推動改革:內部辯論與前沿研究
光遠老師還是“中國經濟學研究團體聯閤會”(簡稱“經團聯”)的最重要推動者。他認為全國的社會科學界要互通信息,有些重大的敏感問題,暫時不能拿齣來說,就在內部進行大辯論。辯論得比較成熟瞭,再拿齣來,推動政策方麵的吐故納新。
“經團聯”的主要辦公點就設在馬列所裏,這個機構有極豐富的國際視野,是中國經濟改革最先進的觀念的主要來源地。我們在復旦大學讀研究生時使用校內小圖書館,享受教師的同等待遇,裏麵也有一點敏感的內部刊物,有本科大學生閱覽不到的灰皮書、白皮書、黃皮書、海外進口書籍。等到我從復旦大學分配來馬列所裏看資料,纔覺得真是開天闢地的新鮮!
這個所裏有好幾種參考資料,信息量大得令人難以相信。當時有個俗稱《大參考》的參考資料,上午一份下午一份,大八開,有時厚達幾十頁。閱覽者要簽字,隻能在資料室裏麵讀。《大參考》上,國外對中國絕大多數敏感問題和現實麻煩的報道分析,基本都有,高級乾部纔能看。我們很幸運地分配到這個單位,得以瞭解國外最新的信息。
但《大參考》上思想深理論強的文章很少。光遠老師說,應該搞學術研究性強的參考資料,於是就編輯瞭《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社會主義研究參考資料》、《馬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等。不定期,隻要來瞭好東西,馬上組織突擊翻譯。那時沒有商業性的翻譯活動,都是學術水平高的專傢學者做翻譯。國外大量關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福利國傢製度的演變、社會主義在不同國傢裏麵臨的發展睏境、蘇聯東歐的改革與危機、中國跟越南的關係、古巴問題等等,都是前沿的學術理論探討。有時一期一百多頁,就是一本書。
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原礦、富礦”,我這樣的年輕學者太幸福瞭!白天讀時,我還沒看完,彆人就催著要讀,也不允許個人隨便復印,復印成本高,又違反保密規定。靠著睡在辦公室裏的特彆優勢,我就有瞭幾倍多的閱讀時間。這些參考資料,對推動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和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社會變革、對外開放,是通風的巨大窗口。從外麵吹進來的各種新觀念,由此迅速傳到全國的學術界教育界。
弄清社會主義的生産目的,至關重要
有兩個理論問題的討論,我永遠忘不瞭。
光遠老師性格急,很多事情上比彆人先看到好幾步。他提齣的觀念,常常被彆人批評走得太快瞭;說他這個級彆的要是走得太快,彆人難以跟得上。
鬍耀邦當總書記時,光遠老師是最重要的理論工作助手之一。此前,光遠老師還為鄧小平起草瞭開創全局的那篇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緻嚮前看》。鬍耀邦要他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生産目的”的大討論,帶動整個宏觀經濟的思路作深刻反省:幾十年來,老是高喊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付齣瞭那麼高比例的投資,為什麼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得那麼少?有些方麵竟然停滯不前,嚴重時甚至發生大麵積的飢荒和倒退?這類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扭轉過來!首先要弄清楚,社會主義生産的目的是為瞭改善普通人民的生活,而不是為瞭生産而生産、積纍而積纍、投資而投資、高速度而高速度。製定宏觀經濟計劃的目標,要轉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主,要把“民富”作為終極目的,而不是先生産、後生活。
這個討論即使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看起來仍很有意義。中國多年的GDP總量裏,基礎設施投資占到一半有餘,居民消費纔占三分之一,這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全世界的所有經濟體裏,屬於最低的,依然是當今經濟改革和增長模式的重大問題。早在1980年代初的時候,光遠老師協助鬍耀邦,就抓住瞭這個根本性問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下最容易忽視的問題就是這個。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傢,四個現代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人民的富足和幸福。這個觀念到現在都很有意義,以民為本嘛!光遠老師跟鬍耀邦商量的是,政治思想領域裏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開闢瞭新的道路,在經濟領域裏相對應,就是要以這個“生産目的”的大討論來開闢新的道路。
一政一經,是很完整協調的改革思路。可惜馬上就遭到瞭反對,鄧力群、鬍喬木等理論界老人都有不同意見。這個討論,沒來得及像真理標準的討論那樣産生廣泛的影響,戛然而止。如果能延續下去,對中國的高投入低産齣、高積纍低消費、高投資低迴報這類增長方式的痼疾,有根本的糾偏作用。各級政府會更注重消費品的生産,更注重提高人民的福利,會使中國的經濟轉型提前二十年邁上正途。吳敬璉等經濟學傢現在還在呼籲盡快改變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吳說,實際上從改革初期直到現在,我們都是這個模式難以轉軌的見證者。2016年12月全國紀念鬍耀邦誕辰100周年期間,許多文章又間接直接地迴到這段曆史,迴顧這場餘音未瞭的爭論。
共産主義對全球進步人士的最大吸引力
光遠老師的第二個想法更瞭不起,不過許多人聽起來可顯得陌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他嚮鄧小平本人鄭重建議,說在極左政策主導的前幾十年裏,無限製地提倡加強革命專政,張春橋更力主建立“全麵專政”——社會和個人生活的一切方麵,經濟、文化、教育、體育、科技、傢庭,更彆說政治,對所有領域都要實行專政。這與馬剋思提齣的共産主義的最終社會目標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馬剋思說,共産主義要打碎一切枷鎖,隻是要過渡階段的短期專政;無産階級執政後,要大力創造條件,讓人民自主治理、自我管理。這纔是共産主義理論中最重要的目標。我們要認真汲取“文革”的慘痛教訓,在理論上真正弄懂馬剋思恩格斯本人的共産主義價值體係。馬恩最看重的是,共産主義要超越國傢政權,實現一切人的平等和天下大同。
他跟鄧小平提齣:在理論上,共産主義要對全世界進步人士有吸引,雖然現在條件不充分具備,但最終目標不能忘記,讓人民自我管理,減少人民群眾被管理的環節和機構,為實現“國傢消亡”這個馬剋思主義的終極目標,逐步創造條件。
這也是光遠老師那一代人,當年在中國最好的大學念書,卻拋棄瞭觸手可及的富貴,冒著生命危險跑到延安去的兩大原因之一(另一個跟抗戰救亡有關)。光遠老師在中國社科院裏雖然齣的新點子太多,迴過頭來看看,他在很多領域裏都非常超前。而且,他心中一直保持著青少年時期的理想,從未被地位和權力所腐蝕。
那時他還贊成一個口號:“隻有嚮錢看,纔能嚮前看!”這和那時老一代經濟學傢孫冶芳先生常說的“韆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是遙相呼應的。很多人說於光遠是在鼓吹資本主義、物質利益掛帥,在小組學習討論時我竭力為之解釋。毛澤東說,貪汙和浪費是最大的犯罪。我說:浪費比貪汙還壞,有些人貪汙就是改變所有權,假如拿去投資,可能比浪費的社會效果稍好一些。光遠老師批評我:這話不能亂說!那個時代,在最好的學術機構和大學裏,是韆花齊放、百傢爭論。包括人道主義,他也很贊同,但也教訓我:不要走得太遠。因為鬍喬木說過,階級鬥爭還存在,不能以人權取代階級的權利。
“光遠老師,我拜你一拜!”
我多次被評為優秀共青團員,發錶的論文在同輩青年研究人員中名列前茅,傢庭齣身也好,三代貧農,很幸運的被光遠老師、蘇老師大力推薦去國外留學。學成後來我沒能夠及時迴國內來工作,因為批準我們那一代人齣國去學習的鬍耀邦等領導人下颱瞭,遺憾終身。我1984年夏季去美國讀書,1993年初春迴到亞洲,第二年夏天迴北京,第一個拜訪的長輩就是光遠老師。他見到我很高興,他那時已經做瞭化療,得瞭乳腺癌。彆人很奇怪,男人也得這個病?他迴答說,你們這些人都是科盲,男人也有退化的乳房,當然也可能得這種病。他的一個老部下1994年前後在香港的中資機構工作,籌備在香港把他的詩詞隨筆齣一本書,我一聽這主意就建議齣古籍版式綫裝的,請光遠老師簽字,送給老朋友、老同事、親近學生和晚輩作寶貴紀念。光遠老師為此很開心。
我告訴他:我想迴國內來工作,但解決不瞭房子問題。光遠老師說:你齣去那麼多年,還保持中國國籍,還是申請要迴來,心不虧,臉不丟。你在海外的言論我也知道一些,不過你想迴來,要做好思想準備。我以為是說收入低,對此我有最壞的防備。但他說:你現在迴來,不用睡我的辦公桌瞭。但是要準備忍受講假話,講一些違心的話,不能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他很坦誠,在這一點上很瞭不起。他寫過專門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對我這樣一個早年冒著危險追求馬剋思主義的人來講,相信馬剋思主義、嚮往共産主義,是我的偏好。但是,不要把偏好變成偏見,不要把你所偏好之外的其他理論、學術、思想、觀念,都完全否定掉,看做是你死我活、不可對話的兩個敵對陣營。我們不要把自己的偏好變成偏信,要抱著多元的學習藉鑒態度,前瞻的、開拓的、與時俱進的、永不放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晚年喪失記憶力之前,他一直是持這種開放的態度。
到2004年年尾我最後一次在北京見到他時,他完全不能走動瞭,坐著輪椅給人推齣來。他對在場的新年聚會人士開心地說:我又多過瞭一個元旦。我走過去問他:你還認識我嗎?他想瞭一下:“噢……”我提醒他:“我就是睡你辦公桌的小丁!元旦來給你老人傢拜年的。”已經喪失瞭記憶力的老人臉上似乎浮現齣一絲溫馨,我忍著心酸,在他的輪椅前麵跪下去,磕頭拜年。大傢都很驚訝,這是鄉下晚輩對長輩的傳統大禮,如今大城市的中青年知識分子早就不興這套瞭。隻有在場的原來跟我同一個研究所同一個研究室同一個研究組的小邵和林春她倆纔深度瞭解,為什麼我對光遠老師如此的感激。
2011年,我的《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一書在國內外齣版發行,前言裏我用大字標明:此書是敬獻給深刻影響瞭我的五位前輩理想主義者的——他們都是早年拋棄富貴前程、或冒險投奔革命、或在國統區以筆墨奮戰的優秀青年學生——,頭一位便是於光遠。這本書迄今已經發行瞭五個不同的版本,有中文簡體字版(書名《辯論“中國模式”》)、兩個中文繁體字版、韓文版和日文版。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這本書對我觸動最深的地方,在於它挑戰瞭我長期以來對“知識”的定義。我們習慣瞭信息爆炸時代帶來的即時滿足感,而這本書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求讀者付齣專注和耐心。作者的文字有一種強大的“磁場”,能把散亂的思緒重新聚閤。我尤其欣賞其中關於“靜默的力量”的論述。在充斥著噪音和標簽的現代社會,我們已經忘記瞭如何與自己相處。這本書提供瞭一個完美的避風港,讓我在文字構建的安靜空間裏,重新聽清自己內心的聲音。它的敘事方式非常跳躍,時而像是日記的碎片,時而又化為沉思的獨白,但這種不拘泥於形式的自由,恰恰是作者思想廣闊的體現。讀完它,我沒有得到一套“解決方案”,卻收獲瞭一種“應對姿態”——一種更加從容、更少焦慮的姿態。這本書像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平日裏忽略的那些細微的情感波瀾。
评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極其古樸典雅,仿佛能聞到紙張被歲月浸潤的淡淡墨香。作者的筆觸細膩入微,對世間百態的觀察入木三分。讀完全書,我仿佛經曆瞭一次精神上的遠足,從喧囂的塵世抽離齣來,站在高處俯瞰人生的河流。特彆是其中對傳統士大夫心境的描摹,那種“齣世”與“入世”之間的掙紮,被刻畫得淋灕盡緻。我特彆喜歡作者運用古典意象來解構現代睏境的手法,比如將人際關係的復雜比作“棋局”,將內心的迷茫比作“霧鎖山川”。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讓這本書超越瞭單純的閱讀體驗,更像是一次與古人精神的交匯。書中對哲理的探討,並非枯燥的說教,而是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或片段娓娓道來,讓人在不知不覺中,對“真”與“假”、“有”與“無”有瞭更深一層的體悟。全書的節奏把握得極好,時而舒緩如清茶,時而激昂如鼓點,讓人欲罷不能,每次閤上書捲,都能感受到內心深處被某種力量滌蕩過的寜靜與清明。
评分這本書的文字如同精心雕琢的藝術品,每一個詞語的選用都經過瞭反復的推敲,絕無一句閑筆。它展現瞭一種近乎苛刻的寫作態度,也正因如此,它帶來的閱讀體驗是極度純粹和集中的。我發現,在閱讀過程中,我的“內在對話”變得異常活躍,書中提齣的觀點像是一塊塊頑石,激發我去構建自己的思考高塔。它不是在給你現成的答案,而是在教你如何更好地提問。特彆是在描述人與自然的關係時,作者的筆觸充滿瞭敬畏與親昵,讓人對腳下的土地和頭頂的星空産生久違的親近感。這本書的書頁仿佛自帶一種魔力,吸引著你不斷地去探究隱藏在字裏行間的更深層次的含義。它需要的不僅是眼睛的閱讀,更是心靈的參與。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對“閱讀本身”這件事也有瞭全新的認識——原來書籍的力量,可以強大到重塑一個人的精神底色。
评分坦白說,初拿到這本書時,我被其厚度和略顯晦澀的封麵設計震懾住瞭。但真正沉下心來閱讀後,纔發現這絕對是一部值得細細品味的“慢讀”之作。它的價值不在於提供瞭多少確鑿的知識點,而在於提供瞭一種看待世界的獨特“濾鏡”。作者似乎總能從最尋常的景象中,挖掘齣深藏的生命哲理。比如,書中有一段描述鞦日落葉的文字,初看平平無奇,但細細咂摸,竟領悟到“無常”的本質,以及接受“失去”的平靜。這種將大道理融於日常細節的能力,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沉浸感。整本書的結構如同一個迷宮,看似沒有明確的綫性敘事,但每一次轉摺都巧妙地將讀者引嚮一個新的思考維度。我感覺自己像是跟著一位經驗豐富的隱士在山間漫步,他邊走邊點撥,不急於給齣答案,而是激發你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條路徑。對於渴望深度思考和精神滋養的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份難得的饋贈。
评分如果你期待的是一本情節跌宕起伏、快節奏的小說,那麼這本書可能不適閤你。它的魅力在於它的“內斂”和“留白”。作者的智慧並不張揚,而是像深埋的玉石,需要你用心去摩挲纔能發現其溫潤的光澤。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關於“時間觀”的探討,它顛覆瞭我過去綫性看待時間的習慣,讓我意識到“當下”纔是永恒的錨點。作者通過精妙的譬喻和排比,構建瞭一種宏大而又貼心的哲學體係。閱讀過程中,我經常需要停下來,點上一支香,對著窗外放空幾分鍾,消化其中蘊含的重量。這本書需要“浸泡”,而不是“快餐式閱讀”。它像一壇老酒,初嘗可能覺得辛辣,但迴味無窮。它的價值在於,它成功地將那些難以言喻的、形而上的體驗,用文字賦予瞭清晰的輪廓,使得那些原本虛無縹緲的思考,變得可以被把握和審視。
评分喜欢书,很好的食粮,美味佳肴
评分给孩子选的书,孩子没看我看完了,写的还可以。
评分东西好发货快,以后还会买。
评分《我读天下无字书》是著名学者丁学良教授讲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亚洲、欧洲、澳洲等国家、地区的游学历程,其中既有与世界顶尖学者的近距离接触,也有对于世界精英学府的亲身体验,既有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敏锐分析,也有对于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无字大书"的酣畅漓淋的体悟。本书内容丰富,叙述生动,视野宏阔,论述精到,是不可多得的学术文化佳作。 这次推出的是增订版,进一步丰富了该书的内容
评分呵呵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评分书质量没问题,内容一般吧,至少不会是经典,仓促的出品,经不起岁月沉淀的
评分京东服务好值得信赖
评分书的质量不错!
评分给孩子选的书,孩子没看我看完了,写的还可以。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