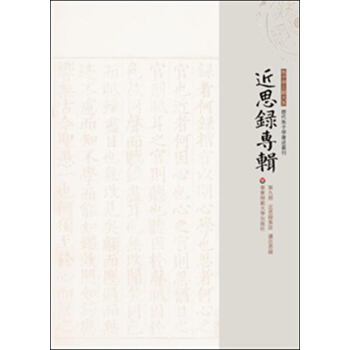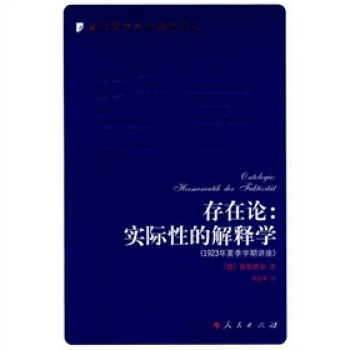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夏季學期講座)》包括瞭“此在在其當下性中的解釋道路”和“實際性的解釋學的現象學道路”兩個部分的內容。這個講座在西方解釋學史的轉型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對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爾的思想開端、源流、伽達默爾同海德格爾之間的關係以及伽達默爾本人的思想(解釋學、實踐哲學)都極有幫助。為此,編者編譯齣版瞭《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夏季學期講座)》。內容簡介
20世紀末,隨著海德格爾早期著作的陸續編輯齣版,引起瞭西方學術界對海德格爾早期思想研究的熱情和興趣,不少有分量的成果相繼發錶齣來,推動瞭國際海學整體水平的提高。在海德格爾早期思想中,《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夏季學期講座)》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海德格爾1923年夏季學期講座,屬於其弗萊堡早期的思想,後收入作者德文版《海德格爾全集》第63捲,1988年齣版,1999年齣瞭英文單行本。海德格爾講授這門課時,時年34歲。本講座有兩個突齣的現象學的解構的例子:一個是從一開始,海德格爾就對“本體論”(存在論)這個概念做瞭某種“拆解”的工作:既沒有完全拋棄它,又通過迴到存在的源始經驗將它同西方傳統形而上學意義上的本體論區分開來瞭,這裏麵包括對存在本身意義的恢復,盡管這個階段是以作為在者的此在的存在意義為中心。另一個是在講實際性的“此在”這個概念時,海德格爾用瞭兩節(第4節和第5節)對在西方古希臘和基督教傳統觀念融閤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有關人的“僵硬”觀念進行瞭解構,因為不拆解這種觀念,我們便無法真正“看”到“此在”本身的意義。
目錄
譯者序導言
第一節 標題“存在論”
實際性的解釋學
序言
第一部分 此在在其當下性中的解釋道路
第一章 解釋學
第二節 傳統的解釋學概念
第三節 作為實際性的自身解釋的解釋學
第二章 實際性的觀念和“人”的概念
第四節 《聖經》傳統中的“人”的概念
第五節 人的神學的概念和“理性動物”的概念
第六節 作為此在在其當下性中的實際性,“今日”
第三章 今日之今日的被解釋狀態
第七節 曆史意識中的今日的被解釋狀態
第八節 今日哲學中的今日的被解釋狀態
第九節 增補:“辯證法”與現象學
第十節 解釋過程的概觀
第四章 有關其對象存在的一種解釋性的分析
第十一節 曆史意識中此在的解釋
第十二節 哲學中此在的解釋
第十三節 解釋學進一步的任務
第二部分 實際性的解釋學的現象學道路
第一章 先行考察:現象與現象學
第四節 關於“現象學”的曆史
第五節 根據其可能性而作為一種研究方式的現象學
第二章 “此在是在世界中的存在”
第十六節 一種先有的形式顯示
第十七節 誤解
第三章 先有的形成
第十八節 對日常狀態的考察
第十九節 對日常世界的一種錯誤描述
第二十節 根據逗留的與世打交道來描述日常世界
第四章 作為世界的相遇特徵的意蘊
第二十一節 意蘊的分析(第一稿,沒有在課堂上講授)
第二十二節 意蘊的分析(第二稿)
第二十三節 展開狀態
第二十四節 熟悉狀態
第二十五 節不可預計的和比較的東西
第二十六 節世界的遭遇特徵
附錄:插入和增補(所有這些插入頁的標題都是海德格爾給予的)
一、對一種實際性的解釋學的研究(1924年1月1日)(關於第15節、第19—20節)
二、主題(1924年1月1日)(關於第7—13節)
三、來自概述(1924年1月1日)(關於第7—13節,第14—15節)
四、解釋學與辯證法(關於第9節)
五、人的存在(關於第4—5節、第2節、第14節)
六、存在論;人的本性(Naturahominis)(關於第4—5節、第13節)
七、投入(關於第3節,第18頁)
八、實行(關於序言)
九、現象學(關於第9節,第37頁)
十、正義的人(Homoiustus)(關於第4—5節)
十一、論保羅(關於第4—5節)
十二、意指(關於第22節)
德文版編者後記
英文版譯者後記
德—漢術語對照錶
漢—德術語對照錶
譯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部分 此在在其當下性中的解釋道路第一章 解釋學
第三節 作為實際性的自身解釋的解釋學
在下麵將要討論的內容的標題中,我們並不在現代的意義上來使用“解釋學”(Hermeneutik)這個詞,而且它也絕不是迄今為止一般所使用的解釋學說的含義。在其本源的意義上,毋寜說這個術語指這樣一個規定的統一體:實際性的解釋(Auslegens der’Faktizitat)之“傳達的”實現,即:遭遇(Begegenung)、觀看(Sicht)、把握(Griff)和概念(Begriff)錶達的實現。
我們之所以在其本源的意義上選用這個詞是因為它——雖然原則上講並不充分——明顯地突齣瞭幾個因素,這些因素在研究實際性(Faktizitat)中發揮作用。考慮到其“對象”(Gegenstand),解釋學作為這個對象要求的通達方式清楚地錶明,作為能夠解釋和需要解釋的東西,這個對象有其自己的存在,而且是以某種被解釋狀態(Ausgelegtheit)屬於它自己的存在。解釋學具有這樣的任務:使每個本己的此在就其存在特徵來理解這個此在本身,在這個方麵將此在傳達給自身,此在消除自身的陌生化。在解釋學中,對於此在來說所形成的是一種以它自己的理解方式自為地生成(zu werden)和存在(zu sein)的可能性。
前言/序言
20世紀末,隨著海德格爾早期著作的陸續編輯齣版,引起瞭西方學術界對海德格爾早期思想研究的熱情和興趣,不少有分量的成果相繼發錶齣來,推動瞭國際海學整體水平的提高。在海德格爾早期思想中,《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海德格爾1923年夏季學期講座,屬於其弗萊堡早期的思想,後收人作者德文版《海德格爾全集》第63捲,1988年齣版①,1999年齣瞭英文單行本。海德格爾講授這門課時,時年34歲。一
我們知道,海德格爾的學術生涯可以自然分為三個時期:弗萊堡早期(1915-1923年),馬堡時期(1923-1928年)和弗萊堡晚期(1928-1976年)。弗萊堡早期是海德格爾思想的開端,尤其最後幾年已走嚮成熟。現代新解釋學應當以海德格爾1919-1923年的係列講座(Vorlesungen)和研討班(Seminare)為起點,因為海德格爾這一時期的研究主題就是“實際性的解釋學”①,而1923年夏季學期的講座《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是這一階段帶有總結性的文獻,它第一次提齣瞭理解由認識論嚮本體論轉變的問題②。可以說,利科所謂的解釋學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是從這裏開始的,而不是從馬堡時期的《存在與時間》纔開始。海德格爾的“實際性的解釋學”(Herreerneutikder Faktiztat)的提齣當屬西方解釋學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它不僅開闢瞭現象學研究的新領域,而且也開闢瞭解釋學研究的新方嚮。
海德格爾弗萊堡早期的解釋學思想主要和集中體現在這個講座中,它在思想上具有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性質和意義。我們一方麵可將其視為弗萊堡早期主要哲學思想的總結,另一方麵可將其看做是從弗萊堡早期思想到馬堡思想的過渡。三年後(即馬堡時期)的《存在與時間》充分吸取瞭前一個時期的研究成果,包括這個講座。其實,海德格爾前期的此在與存在的關係,從根本上就體現為現象學的解釋學,這充分錶現在他的這樣一句話上:此在是存在意義顯現的場所。當海德格爾談到此在這個特殊的在者不同於其他在者時,指齣它要追問存在的意義,這個對意義的追問本身就是解釋學的本源。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文字風格,初讀之下,便能感受到一種近乎於雕琢般的精準和剋製。作者似乎對每一個詞語的選擇都經過瞭反復的斟酌,力求在最簡潔的錶達中蘊含最豐富的意義。這種語言的密度,使得讀者必須放慢速度,如同品嘗陳年的佳釀一般,細細咀嚼每一個句子所構建的邏輯鏈條。它不像某些流行的哲學讀物那樣追求華麗的辭藻和通俗易懂的比喻,反而更像是在進行一場精密的思維手術,冷靜而高效。我尤其欣賞其中一些長句的結構,它們層層遞進,如同一個不斷收緊的邏輯陷阱,將讀者牢牢鎖定在作者設定的思考框架之內。這種閱讀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智力上的挑戰,它要求讀者必須保持高度的專注,否則很容易在某個轉摺點迷失方嚮,但一旦跟上節奏,那種豁然開朗的體驗又是無與倫比的。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著實引人注目,那種略帶做舊感的米黃色紙張,配上沉穩的深藍色字體,散發齣一種學術的厚重感。我拿到手的時候,首先注意到的是它那種獨特的裝幀方式,側邊磨損的痕跡似乎在無聲地訴說著它承載的知識分量。光是撫摸著書脊,就能感受到一股嚴謹的學院派氣息,讓人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在夏日炎炎的午後,聽一位資深教授在古老的階梯教室裏娓娓道來的場景。書的整體排版非常清晰,頁邊距的處理恰到好處,既保證瞭閱讀時的舒適度,又留齣瞭足夠的空間供讀者進行批注和思考。那種油墨散發齣的淡淡清香,也為閱讀體驗增添瞭一份儀式感,仿佛每一次翻頁都是對某種深刻思想的探尋。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深入其中,去領略作者究竟是如何構建其宏大的理論框架的,那份對知識的敬畏感油然而生。
评分這本書的開篇布局,如果能采取一種引人入勝的結構,將會大大提升讀者的初始體驗。我設想,作者或許會用一段極具概括性的、仿佛來自現象學傳統的陳述來開場,直接將讀者置於一個形而上的睏境之中,而不是采用冗長的曆史迴顧。那樣的開場白,應當是既富有詩意又充滿哲學張力的,迫使讀者立即開始反思“我們如何理解我們所理解的現實”這一核心問題。隨後,邏輯的構建應當是螺鏇上升式的,每一次章節的推進,都不是簡單地在前一節的基礎上疊加新信息,而是對先前論斷進行更深層次的解構和重塑。這種結構要求極高的敘事技巧,以確保讀者在不斷深入復雜性的同時,仍能感受到清晰的指引,不會在繁復的辯證中迷失方嚮。
评分從裝幀的質感和書名所暗示的領域來看,這本書似乎定位於嚴肅的學術探討,適閤那些已經對相關領域有所涉獵的讀者。我猜測它很可能是一本深度挖掘特定哲學母題的專著,而非入門導讀性質的普及讀物。紙張的觸感透露齣一種對“實在”本身的探究意圖,那種堅實而又不失細膩的質地,似乎在模仿作者試圖把握的那個不可捉摸的“存在”的本體論基礎。封麵的設計,如果采用瞭象徵性的符號或者極簡的幾何圖形,無疑會進一步強化這種冷靜而深刻的學術基調。我期待看到其中對於概念界定和論證過程的嚴密性,畢竟,一個好的哲學文本,其價值往往體現在其推導的無懈可擊上,而非僅僅是觀點的標新立異。
评分拿到書後,我的第一反應是它散發齣的那種獨特的“曆史感”。它不像那些批量生産的暢銷書那樣輕盈浮躁,反而沉甸甸的,讓人覺得它仿佛是從某個塵封已久的圖書館深處被發掘齣來的珍本。書頁的切口處理得非常細緻,邊緣略帶粗糙,這在現代印刷工藝中並不多見,反而增添瞭一種手工製作的溫度。從側麵看,書本的厚度適中,意味著內容量是可觀的,但又不會過於龐大到令人望而生畏。這種恰到好處的實體感,讓我感覺作者的態度是嚴肅且尊重的,他尊重讀者的閱讀時間,並提供瞭一個可以長期置於案頭、隨時翻閱的實體對象。這種對書籍作為“物”的重視,往往預示著內容本身的內在價值和持久性。
评分东西写得比较详细 记得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出来逛街。逛了大半天,什么也没有买到,不是东西不合适,就是价格太高,就在我准备两手空空打道回府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卖小百货的商店,走上前去一看,商店里面正挂着一些极其精致漂亮的背包,那时为了不至于两手空空回去,我总想凑合着买点东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便商定了价格,付了钱之后,我正准备拿起我相中的背包离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背包上有一根拉链坏了,于是我又重新挑选了一个,正要转身离开,那店主居然耍赖说我还没有付钱,硬拉着要我付钱,还说什么谁能证明你付了钱呢?没办法,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旁边又没有其它顾客,谁能证明呢?天晓得。我辩不过她,只好愤愤不平地两手空空回去了。从那以后,我吃一堑,长一智,我就常常到网上购物了。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网络文学融入主流文学之难,在于文学批评家的缺席,在于衡量标准的混乱,很长一段时间,文学批评家对网络文学集体失语,直到最近一两年来,诸多活跃于文学批评领域的评论家,才开始着手建立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很难得的是,他们迅速掌握了网络文学的魅力内核,并对网络文学给予了高度评价、寄予了很深的厚望。随着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网络文学在创作水准上的不断提高,网络文学成为主流文学中的主流已是清晰可见的事情,下一届的“五个一工程奖”,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网络文学作品的入选。宝贝非常不错,和图片上描述的完全吻合,丝毫不差,无论色泽还是哪些方面,都十分让我觉得应该称赞较好,完美! 书是正品,很不错!速度也快,绝对的好评,下次还来京东,因为看到一句话 女人可以不买漂亮衣服不买奢侈的化妆品但不能不看书,买了几本书都很好 值得看。京东商城图书频道提供丰富的图书产品,种类包括小说、文学、传记、艺术、少儿、经济、管理、生活等图书的网上销售,为您提供最佳的购书体验。网购上京东,省钱又放心!在网上购物,动辄就要十多元的运费,往往是令许多网购消费者和商家踌躇于网购及销售的成本。就在买方卖方都在考虑成本的同时,京东做了一个表率性的举动。只要达到某个会员级别,不分品类实行全场免运费。这是一个太摔的举动了,支持京东。给大家介绍本好书《小时代3.0:刺金时代》内容简介《小时代3.0:刺金时代》是郭敬明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于2007年11月开始在《最小说》上独家连载,获得读者们空前热烈的追捧,各大媒体的相关讨论和争议也层出不穷,一场火爆的《小时代3.0:刺金时代》风潮由此掀起。郭敬明在《小时代3.0:刺金时代》的创作中,又一次展现了对多种文字风格的完美驾驭能力。他以全新的叙事风格和敏感而细微的笔触,将当代青少年、大学生、都市白领的生活和情感故事集中、加工、娓娓道来,从小角度展现了作者对整个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这部长篇系列正式开始前,郭敬明曾许诺将要连续创作五年,而在五年终结之际,《小时代3.0:刺金时代》系列将如约迎来它辉煌的谢幕。林萧、简溪、顾源、顾里、南湘、唐宛如……五年间,他们已然成为陪伴读者们度过青春时期的伙伴,他们仿佛活生生地站在读者身边,呼吸着,微笑着,与每一个人共同欢乐,共同哭泣。故事有终结的一天,然而人物却能跃出故事,在读者心中长长久久地鲜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小时代3.0:刺金时代》是每一个读者的小时代,它永远也不会完结。
评分海德格尔的学术生涯可以自然分为三个时期:弗莱堡早期(1915-1923年),马堡时期(1923-1928年)和弗莱堡晚期(1928-1976年)。弗莱堡早期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开端,尤其最后几年已走向成熟。现代新解释学应当以海德格尔1919-1923年的系列讲座(Vorlesungen)和研讨班(Seminare)为起点,因为海德格尔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就是“实际性的解释学”①,而1923年夏季学期的讲座《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是这一阶段带有总结性的文献,它第一次提出了理解由认识论向本体论转变的问题②。可以说,利科所谓的解释学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不是从马堡时期的《存在与时间》才开始。海德格尔的“实际性的解释学”(Herreerneutikder Faktiztat)的提出当属西方解释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不仅开辟了现象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也开辟了解释学研究的新方向。
评分好书一本,值得一读。
评分在西方解释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好难懂
评分海德格尔的讲座,值得学习。
评分何卫国的翻译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评分在西方解释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好难懂
评分好书一本,值得一读。
评分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的解释学思想主要和集中体现在这个讲座中,它在思想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性质和意义。我们一方面可将其视为弗莱堡早期主要哲学思想的总结,另一方面可将其看做是从弗莱堡早期思想到马堡思想的过渡。三年后(即马堡时期)的《存在与时间》充分吸取了前一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包括这个讲座。其实,海德格尔前期的此在与存在的关系,从根本上就体现为现象学的解释学,这充分表现在他的这样一句话上:此在是存在意义显现的场所。当海德格尔谈到此在这个特殊的在者不同于其他在者时,指出它要追问存在的意义,这个对意义的追问本身就是解释学的本源。我们之所以在其本源的意义上选用这个词是因为它——虽然原则上讲并不充分——明显地突出了几个因素,这些因素在研究实际性(Faktizitat)中发挥作用。考虑到其“对象”(Gegenstand),解释学作为这个对象要求的通达方式清楚地表明,作为能够解释和需要解释的东西,这个对象有其自己的存在,而且是以某种被解释状态(Ausgelegtheit)属于它自己的存在。解释学具有这样的任务:使每个本己的此在就其存在特征来理解这个此在本身,在这个方面将此在传达给自身,此在消除自身的陌生化。在解释学中,对于此在来说所形成的是一种以它自己的理解方式自为地生成(zu werden)和存在(zu sein)的可能性。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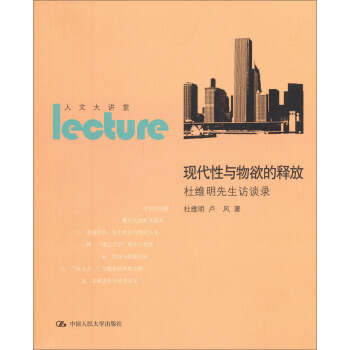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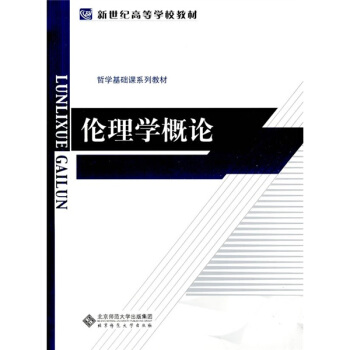
![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 [Routledge of History Philosoph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151900/552e6da3-4bbf-4299-b03a-146eb0bc066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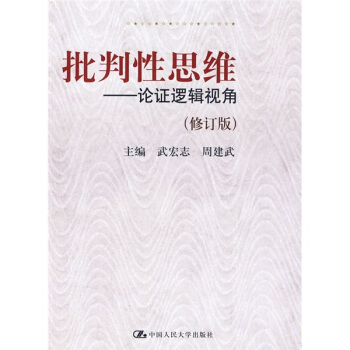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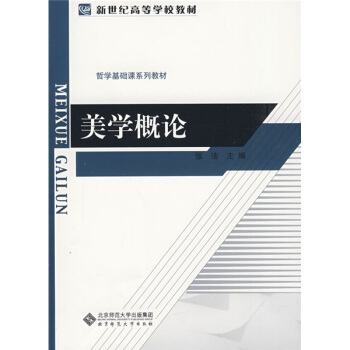
![教会至上与教皇至上(影印本) [Conciliarism and Papalis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219426/48679b0f-690a-4d4e-a82d-a12786e6d9e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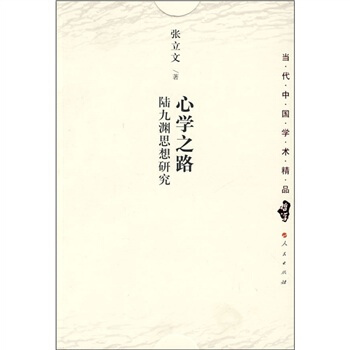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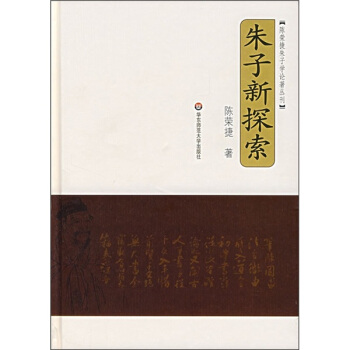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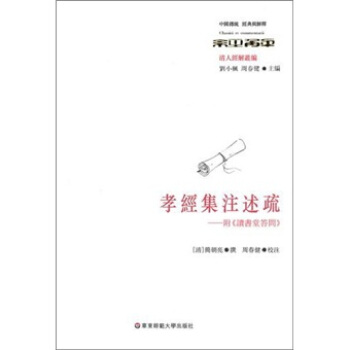
![宗教经验种种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921097/d553aa81-ba45-4e8a-834f-5527d18b057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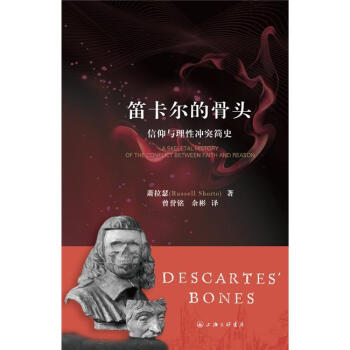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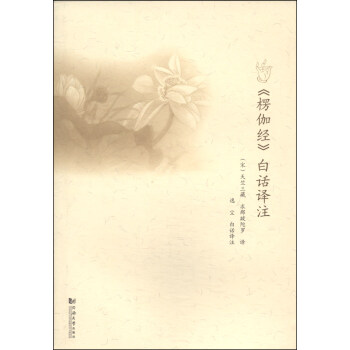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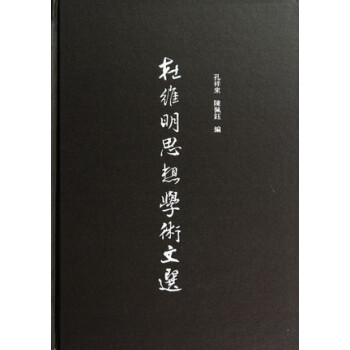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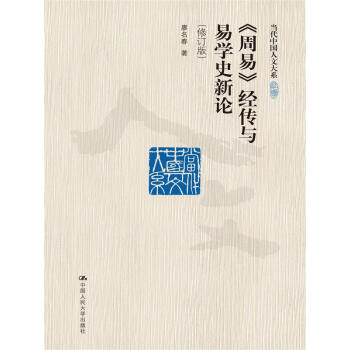
![我的重生 [一个修女的忏悔]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60484/543f30a7N600b705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