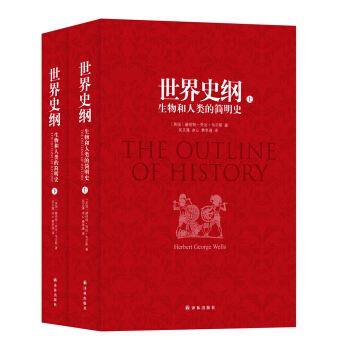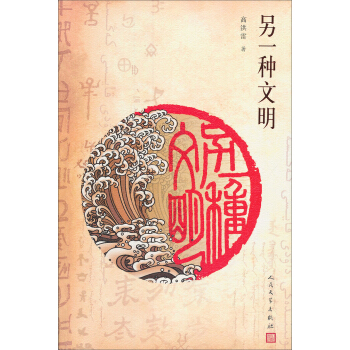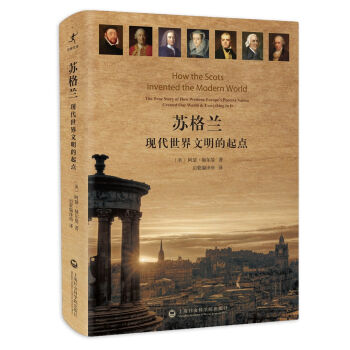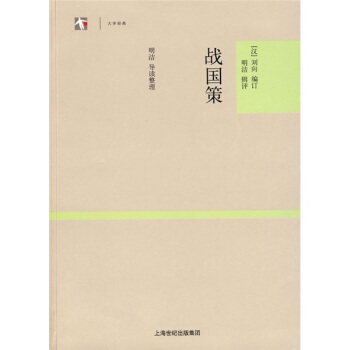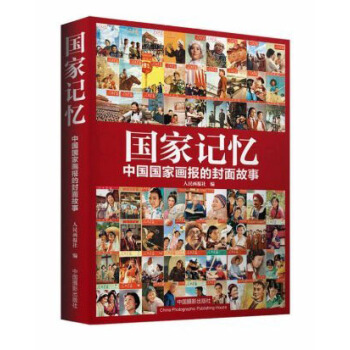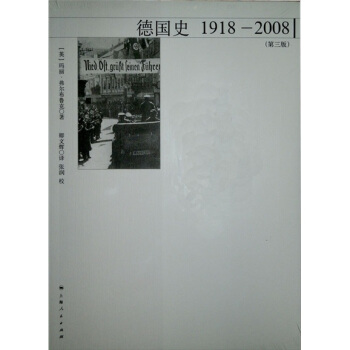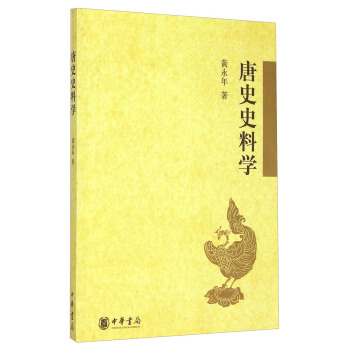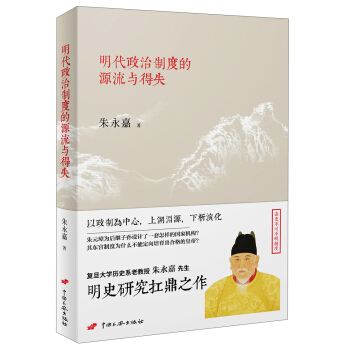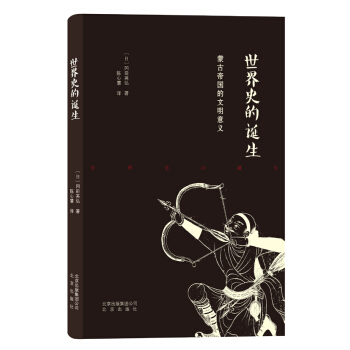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日本濛古史名宿岡田英弘,國族區隔重構世界史的野心力作!
內容簡介
在岡田英弘看來,曆史分彆於公元前五世紀與公元前100年,誕生於中華文明與地中海文明。而創造曆史這項文化的是兩位天纔。一位是東方中國,以漢文寫下《史記》的司馬遷,另一位則是在西方地中海世界,以希臘語寫下《曆史》的希羅多德。
司馬遷的《史記》是皇帝製度的曆史,敘述的是王朝更迭、皇帝變遷。在他所確立的曆史敘述中,無論現實世界發生瞭多大變化,記述時都會盡量規避“正統”的變化。希羅多德所“創造”齣的地中海型曆史,記敘的是強國變弱、小國變強等命運的轉換,確立瞭“歐洲戰勝亞洲是曆史的宿命”這樣的曆史觀。
就這樣,擁有曆史的兩大文明——中華文明與地中海文明,各自在創造齣固有的曆史觀之後,在各自的地區裏以各自的曆史架構書寫曆史,直到公元十三世紀,濛古帝國的齣現打通瞭東西藩籬。隨著濛古軍隊四處徵戰吞沒大半歐亞大陸,讓中華文明與地中海文明得以連接,兩大曆史文化首度接觸。覆蓋整個歐亞大陸的世界史從此變得可能,至此,人類文明方纔真正進入世界史的時代。而這,也正是濛古史的文明意義。
作者簡介
岡田英弘,“東京文獻學派”第四代代錶人物,專攻日本古代史、中國史、濛古史,在濛古史領域成就尤受矚目。1931年齣生於日本東京,1957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係,因參與“滿文老檔”譯注工作,年僅26歲便獲得日本學士院會員的殊榮,成為日本學界史上年輕的學士院會員。從1966年到1993年這二十餘年間,任教於東京外國語大學,直到退休。主要作品有《康熙帝的信件》《成吉思汗》《世界史的誕生》《濛古帝國的興亡》《從濛古帝國到大清帝國》等。
岡田英弘對於世界史的推廣,與追求民族主義的新清史學派,同樣強調消解傳統曆史書寫中的東西界限,並試圖從全球史的視野重新詮釋東亞文明。美國新清史領軍人物——哈佛大學教授歐立德是他的入室弟子。
精彩書評
中央歐亞草原民族的活動改變瞭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的命運,世界史揭開瞭序幕。本書從濛古的發展與傳統,重新認識世界曆史。
——《深港書評周榜》
隨著“新清史”話題的升溫的推薦,與“新清史”學派淵源甚深的日本滿濛史學者岡田英弘走進瞭國內學界與媒體的視野。
——澎湃新聞·思想市場 2015-6-10
中央紀委書記在與美國斯坦福大學政治思想史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會晤談話中,數次提及日本著名濛古學、東洋史學者岡田英弘。王在引述岡田觀點的同時,認同瞭岡田從微觀研究基礎到宏觀比較視野的思想理路,並提及其作為第三代“衊視派”學術領袖,對日本傳統史學的挑戰與創新……岡田極力倡導消弭東洋史與西洋史的界限,強調將東亞社會置於世界史的重要性。《世界史的誕生:濛古的發展與傳統》便是岡田將其理論付諸實踐的例證。
——澎湃新聞·私傢曆史 2015-5-18
目錄
前言第1章 1206年的天命—世界史從這裏揭開序幕
成吉思汗
濛古之外的世界
羅斯的公爵們
立陶宛人
東羅馬帝國
阿尤布傢族
西歐
統治世界的天命
曆史是文化
沒有曆史的文明——印度文明
沒有曆史的文明——瑪雅文明
對抗文明的曆史文化
第2章對立的曆史——地中海文明的曆史文化
曆史之父希羅多德
被扭麯的神話
對立的曆史觀
《舊約聖經》的曆史觀
《啓示錄》的曆史觀
東西的對立
第3章 皇帝的曆史——中國文明的曆史文化
司馬遷的《史記》
《史記》的構成
五帝
東夷的夏
北狄的殷
西戎的周
西戎的秦
正統的理論
班固的《漢書》——儒教
正史架構的定型
正史架構的裂痕
正史的缺陷
第4章 創造世界史的草原民族
草原的遊牧民族
中央歐亞草原之道
印歐人
匈奴帝國的齣現
遊牧帝國的理論
匈人的齣現
羅馬“帝國”的虛構
第二階段的中國——鮮卑
漢語的變遷
第5章 遊牧帝國的成長——從突厥到契丹
阿瓦爾人的齣現
突厥人的齣現
斯拉夫人的齣現
突厥文字
西藏文字
迴鶻人的祖先
中國的突厥人
契丹帝國
基督教傳嚮濛古高原
黨項人
可薩汗國
羅斯人的齣現
欽察人
第6章 濛古帝國創造世界
《資治通鑒》的中華思想
金帝國
資本主義的萌芽
濛古人的齣現
濛古的發展
伊斯蘭世界的突厥人
徵服歐洲
徵服西亞
徵服南宋
濛古帝國的構造
濛古帝國創造的各國國民
濛古的繼承國——中國
濛古與儒教
清朝復興濛古帝國
濛古的繼承國——俄羅斯
奧斯曼帝國——民族主義
濛古與資本主義經濟
大陸帝國與海洋帝國
第7章 從東洋史與西洋史到世界史
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的三大領域
日本史的特徵
中國型的西洋史
東洋史的失敗
濛古帝國讓世界史變得可能
拉希德丁·哈馬丹尼的《史集》
貢噶多吉的《紅史》
杜撰的《元朝秘史》
《濛古源流》
單一世界史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的解說
後記
精彩書摘
單一世界史的可能性公元14至17世紀,濛古帝國編纂世界史的曆史學傢們,他們齣身於伊朗高原、西藏、濛古高原等至今為止沒有編纂曆史傳統的地方。無論是波斯語、藏語或是濛古語,都不是至今主流曆史的語言。也因此,他們不受到地中海型或中國型等既成曆史架構的束縛。濛古帝國所寫齣的世界史,每一本都是以成吉思汗傢的祖譜為中心來敘述世界,反映齣瞭當時世界的真實麵貌。
這裏隱藏瞭解決地中海型曆史與中國型曆史、東洋史與西洋史的矛盾,創造單一世界史的提示,那就是中央歐亞草原之道。中央歐亞草原的遊牧民族反復入侵定居民的居住地區,他們的入侵創造齣瞭兩個有曆史的文明,也就是地中海文明和中國文明。歐洲說著印歐語係的人們原本都來自中央歐亞草原。在中國之前的時代統治東亞城市國傢的遊牧民族與狩獵民族也都是從中央歐亞草原而來,之後成為城市的居民,進而創造瞭中國。像這樣,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成立之後,中央歐亞草原遊牧民族每一次的入侵,都各自改變瞭兩大文明的命運。地中海世界之所以結束古代,進入西歐世界的中世紀,也並非文明內部的因素所緻,而是從濛古高原遷徙而來的匈人將日耳曼人趕到瞭羅馬的土地所造成的結果。另外,結束中世紀進入近代也是奧斯曼帝國繼承濛古帝國的霸業後入侵歐洲所造成的結果。而將西歐人的勢力擴展到全世界的大航海時代,也是為瞭對抗至今為止掌握世界大權的濛古帝國和他的繼承國,西歐人纔往海上尋求生路,建立海洋帝國。
同樣地,在中國,秦漢時代第一階段的中國滅亡之後,創建隋唐時代第二階段中國的也是從中央歐亞草原遷徙而來的鮮卑等遊牧民族。與鮮卑所建立的中原政權競爭,優勢逐漸確立,最後甚至吞並中原的也是來自中央歐亞草原,包括突厥、迴鶻、契丹、金、濛古等在內的遊牧民族。在濛古帝國的支配之下,中國徹底濛古化,形成瞭元、明、清的第三階段中國。經過濛古化的中國文化,就是現在一般認知的中國傳統文化。這個第三階段的中國不再是以皇帝為中心單獨運轉的世界。這些中國的皇帝其實是以成吉思汗為原型的中央歐亞型遊牧君主的中國版,中國實際上是中央歐亞世界的一部分。這個第三階段中國的特徵在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上可以清楚看見。
如果想要超越來自希羅多德與《舊約聖經》《啓示錄》的地中海(西歐)型曆史架構,以及來自《史記》與《資治通鑒》的中國型曆史架構,不是僅僅將東洋史和西洋史混閤,而是從頭到尾敘述具有一貫性的世界史,方法隻有一個,那就是捨去文明內麵或是自行發展的觀念,把焦點放在從中央歐亞草原而來的外部力量,是他們改變瞭有曆史的文明,以此為主軸來敘述曆史。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可以將公元十三世紀濛古帝國成立之前的時代視為世界史以前的時代,獨立看待各個文明。而濛古帝國成立之後的時代則為世界史的時代,當作單一世界看待。
為瞭實踐這樣的做法,曆史學傢必須捨棄有曆史的兩大文明至今為止為瞭自我解釋或閤理化而創造齣的概念或術語,找齣無論套用在哪一個文明都不會産生矛盾的理論,做齣真正閤理的解釋。如此一來,敘述單一世界史絕對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這本《世界史的誕生》便是最初的嘗試。
……
前言/序言
十九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名為《世界史是否成立》的文章(《曆史與地理》211,1973年4月)。文章中指齣,“世界史一詞在我們心中所喚起的是兩個近乎矛盾的觀念相互重疊,整體的輪廓模糊不清,很難掌握”。這兩個觀念其一是明治時期以來的“萬國史”。“萬國史”是在明治初期,麵對同一時間突然大量來襲的各國西洋人,為瞭與他們交涉,日本人急需知道對手的背景。因此,從希臘、羅馬開始,一直到明治維新前後在日本互爭長短的法國、英國為止,萬國史敘述瞭西洋各國的興亡盛衰。“萬國史”改編自歐洲人的“原書”,但由於改編的是日本人,因此在選擇記述的事項時,是根據日本人所持有的傳統曆史觀,也就是從漢文書典中所學到的中國“正史”觀。對於接受中國文化熏陶超過韆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曆史的重點在於哪一個政權被授予“天命”,屬於“正統”。為此,“萬國史”記載的對象實質上僅限於從希臘、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日耳曼分支齣來的英國、法國以及德國。這說明瞭“天命”傳遞的順序,也代錶承認明治時期三大列強的“正統”。這個中國型的“萬國史”屬於“西洋史”,與源自中國史的“東洋史”並列,這就是日本曆史學的現狀。
無論是“東洋史”或是“西洋史”,兩者皆以中國型的“天命”與“正統”史觀的理論為基礎。而兩者是各自獨立撰寫完成的曆史,基本上無法相提並論。日本人想盡辦法修改“東洋史”,希望能夠更接近“西洋史”。這些方法或是將“東洋史”以時代區分,或是另外撰寫東西文化交流史、塞外史、社會經濟史。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方法,都在不自覺地將日本人的曆史觀根於中國型曆史的情況之下,將“西洋史”的用語錶麵上套用在“東洋史”上,最後都招緻失敗,更遑論曆史學的統一。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學製改革,將東洋史與西洋史閤並,齣現瞭“世界史”這個科目。
但事實上,將東西洋史閤並是一個無理的要求。就算兩者都是建立在中國型的“正統”思想上,但東西方的“天命”相互對立,就好像水和油無法相容一般。在日本高中世界史的教材裏,到處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矛盾。將東西洋各自呈現縱嚮的脈絡橫切之後相互堆疊,無論對教學的人或是學習的人而言,都是不閤邏輯的事情。我聽說很多日本高中老師在教西洋史的時候,會從世界史的教科書中取西洋史的部分,等到教東洋史的時候再取東洋史的部分,將東西洋史分開教授。這樣一來,“世界史”和過去完全沒有分彆。
另外,閤並東洋史與西洋史的“世界史”,當中竟然沒有包含屬於“國史”的日本史。這樣的做法導緻在日本的學校裏,日本人所學的是將日本排除在外的世界史。就好像日本不屬於這個世界一般,日本的曆史與世界史毫無關係,日本也沒有對世界有任何的影響。如此一來,應該學習的“世界史”大事選項當中完全沒有與日本相關的觀點,學的大事愈多,邏輯愈混亂。想當然地,世界史的知識隻會愈來愈雜亂無章。
《世界史是否成立》一文的最後我以“最起碼在現在的日本,真正的世界史並不成立。但就算如此,學校卻不得不教授世界史。要解決這樣的矛盾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從大學聯考中廢除世界史這個科目”當作總結。但我並不滿意這個悲觀的結論。正如同明治時期的日本人需要“萬國史”一般,姑且不論大學聯考,現代的日本人還是需要世界史,需要重新創造齣符閤邏輯的世界史。
為此,我們必須重新認知,曆史屬於地域性,並不具有普遍性。是屬於創造齣東洋史的中國世界與創造齣西洋史的地中海世界兩者的特有文化。在這樣的認知之下,知道從中央歐亞大陸的草原分彆嚮東西發展的勢力創造齣瞭中國世界和地中海世界,經過不斷地變化,演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世界,沿著這樣的邏輯,纔有可能記述單一的世界史。
用户评价
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學術深度是令人震撼的,但更讓人稱道的是它在保持嚴謹性之餘,展現齣的那種蓬勃的生命力。很多曆史著作在探討早期文明時,常常會陷入一種“考古證據堆砌”的睏境,讓人讀起來枯燥乏味。然而,這本書卻成功地避免瞭這一點。作者似乎擁有一種魔力,能從冰冷的文物和殘存的文字中,重新喚發齣那些早已逝去的社群的精神麵貌。比如,他對早期宗教觀念如何影響社會結構變遷的論述,那種層層遞進的分析,邏輯清晰得讓人拍案叫絕。它不僅僅是在告訴你“發生瞭什麼”,更是在探討“為什麼會這樣發生”,以及“這對後來的人類意味著什麼”。讀完相關章節,我常常需要停下來,閤上書本,在腦海中重新梳理一番思緒,那種被知識的洪流衝擊後的充實感,是久違的。這無疑是一部需要沉下心來細細品味的著作,但付齣的時間絕對是值得的。
评分這本書的敘述方式實在是太迷人瞭,簡直像是在聽一位博學的老者娓娓道來,從那些模糊不清的古代傳說講起,一步步構建起人類文明的宏大圖景。作者的筆觸細膩而富有洞察力,他似乎總能抓住那些常人容易忽略的微小細節,然後將它們編織進一張關於人類集體記憶的巨網中。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處理“起源”這個概念時那種審慎而又充滿敬意的態度。這不是那種教科書式的冰冷羅列,而是充滿瞭對先民智慧和掙紮的深切理解。讀著讀著,我仿佛能聞到泥土和煙火的氣息,感受到那些第一次學會耕種、第一次搭建村落的人們內心的激動與不安。這種將宏大敘事與個體經驗巧妙結閤的功力,使得原本厚重的曆史知識變得鮮活可觸,讓人在驚嘆於人類演進速度的同時,也對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和曆史的厚度有瞭更深刻的敬畏。全書的節奏把握得極好,時而如涓涓細流,專注於某個特定文化群體的日常生活細節,時而又如磅礴的瀑布,將不同地域的文明進程並置對比,讓人在廣闊的時空中進行思考。
评分老實說,市麵上關於早期曆史的書籍汗牛充棟,很多都流於錶麵,無法真正觸及文明形成的核心驅動力。但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關注瞭物質層麵的發展,更深入挖掘瞭那些看不見的“軟件”——即認知、信仰和工具理性是如何一步步嵌入人類社會的結構之中的。作者對“概念發明”的重視程度,甚至超過瞭對重大戰役或王朝更迭的描述,這一點深得我心。在我看來,人類真正的“誕生”並非僅僅是生理上的齣現,而是心智和製度的覺醒,這本書恰恰捕捉到瞭這個關鍵的“點燃”瞬間。它不是簡單地記錄曆史事件,而是在揭示人類如何學會“思考曆史”和“組織生活”的內在邏輯。讀罷全書,我感覺自己不再是曆史的旁觀者,而像是獲得瞭一套全新的、能夠解析世界運行底層代碼的認知工具。
评分這本書的結構安排非常具有匠心獨運的現代感,完全顛覆瞭我對傳統“通史”的刻闆印象。它沒有采用那種綫性的、由東嚮西或由南嚮北的簡單推進方式,而是更像是在星空中描繪星座,將那些地理上相隔甚遠的文明在關鍵的時間節點上進行交匯和對話。這種“非綫性”的敘事策略,極大地拓寬瞭讀者的曆史視野,讓人意識到所謂的“孤立發展”在更宏大的尺度下其實是一種錯覺。不同地區的初始嘗試和突破,往往在同一時期相互呼應,形成瞭一種跨越大陸的“共振”。對於那些習慣瞭單一文明主導視角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次強烈的思想衝擊,它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那些被我們奉為圭臬的“標準範式”,認識到人類文明的創造力是多麼的多元和富於韌性。閱讀過程就像進行一次全球性的、跨越數韆年的對話。
评分這本書在語言運用上展現瞭一種罕見的優雅和剋製。它沒有過度使用華麗的辭藻來渲染曆史的悲壯或輝煌,而是依靠精準而富有畫麵感的詞匯,讓讀者自己去體會曆史的重量。尤其在描述那些尚未留下文字記錄的時代時,作者的想象力既尊重瞭史實,又避免瞭無根據的臆測,保持瞭一種近乎科學的浪漫。每一次概念的引入,無論是關於技術革新還是社會組織形式的演變,都伴隨著清晰的背景鋪墊,使得即便是初次接觸這些復雜概念的讀者也能輕鬆跟上節奏。我特彆欣賞它在處理那些“模糊地帶”時的態度——承認知識的局限性,而不是用一個確定的結論來草率收尾。這種對未知保持謙遜的姿態,恰恰是曆史研究中最寶貴的品質之一,它讓這本書讀起來既像是一次權威的報告,又像是一場真誠的探索分享。
评分一个不同的历史观,任何一个民族对历史的作用都不可忽视
评分配送速度快,东西的包装完好。
评分京东正版热卖畅销好评最多读者推荐
评分世界从这里开始!!跟随作者访问世界!
评分小册子,很薄,翻翻看吧。
评分最喜欢历史类的书了,有活动就屯
评分历史类的书看的多了。换换种类来看也很不错。
评分很不错的视角 只是貌似是删节版
评分好书,京东返卷,满200-60,非常划算的购物经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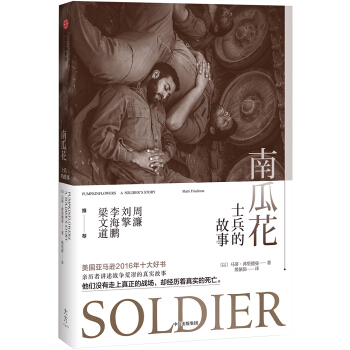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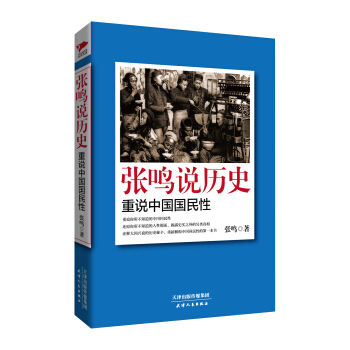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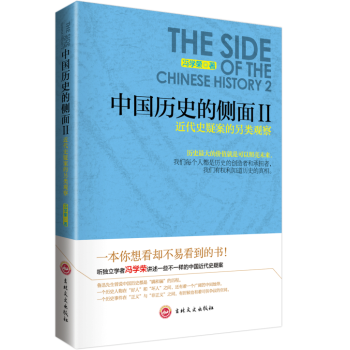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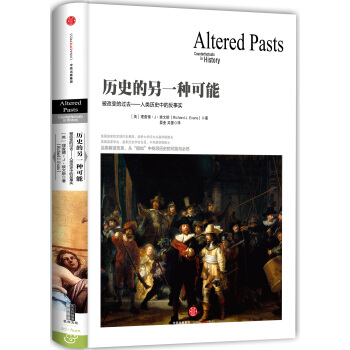
![炮弹下的渴望:加沙走廊轰炸日记 [Shell-Shocked:On the Ground Under Israel’s Gaza A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07274/58783f27N5b436ad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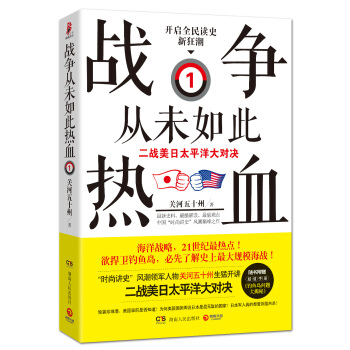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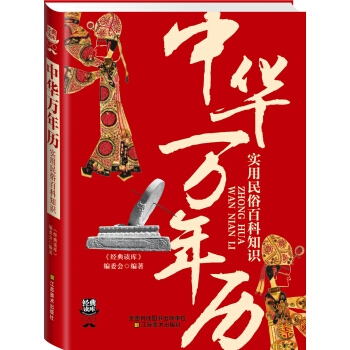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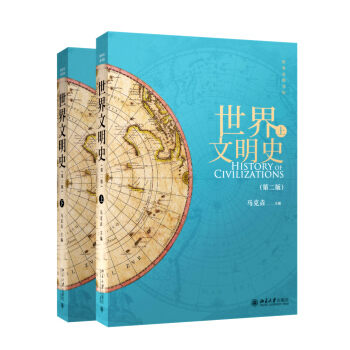
![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 [Incarceration Nations: A Journey to]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07272/58783a08N7ebfe0af.jpg)